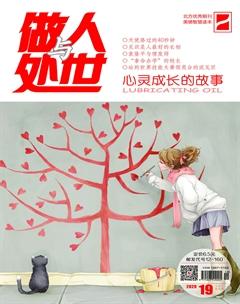大师的自信
吴敏文
梁启超不仅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人物之一,而且是国学大师、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梁先生在清华大学上课,第一句话是:“兄弟我是没什么学问的。”然后,稍顿一下,等大家安静下来,又慢悠悠地补上一句:“兄弟我还是有些学问的。”前一句表示谦虚,后一句带着自信,欲扬先抑,颇见性格。
课堂授课的“梁氏开头法”声名远播,它充分展示出以自谦为基础的自信,以自信为落脚点的自谦。自谦与自信相辅相成;不仅形式上独具特色,而且逻辑上无懈可击。试想,学问浩如烟海,不管是谁,无论怎样博学,又怎能够说自己学问够了?所以,即使是博学如梁启超也要承认“兄弟我是没什么学问的”。然而,如果你仅仅是“没什么学问”,你又来教什么书呢?这可是堂堂的清华园啊!所以,后一句“兄弟我还是有些学问的”至关重要。事实上,梁启超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著作等身,完全担得起“还是有些学问的”这个评价与称谓的。简短一个开场白,道出一个深刻的人生道理:第一,你要刻苦认真学习,以获得尽可能多的知识、学问;第二,有一点知识、学问没什么了不起,要知道学海无涯,你所掌握的知识、学问非常有限,所以,要时时自警、自谦。
第二位梁先生,即梁漱溟不仅学问深厚,而且积极参与实践。新中国成立后,梁漱溟是长期担任全国政协常委的资深无党派民主人士。在接受全国政协秘书汪东林同志的访谈时,梁漱溟讲述了他早年开始社会实践活动的起因:“1916年夏天,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张耀曾先生下野,我本是他的机要秘书,亦去职南游,经苏州、杭州到湖南。时值在衡山的北洋军阀旧部王汝贤等率部溃走长沙,沿途军纪败坏,大肆抢掠。正巧我与溃兵同时进京,一路所见,触目惊心。我有感于内乱战祸之烈,撰写了《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一文,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制止内战,让民众休养生息。”
梁漱溟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一生以改造社会、贡献国家为使命。“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意即我辈(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不出来干预和制止社会乱象,社会何以得和平?民众何能得安生?梁漱溟这等自信,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后来,梁漱溟创建“乡村建设”理论,并选择山东邹平积极推进建设实践。全面抗战開始后,他赴香港办报宣传抗战。太平洋战争后日本进攻香港,在日本飞机投弹轰炸香港时,大家都躲进防空洞避免被炸,只有梁漱溟照常在办公室办公,不躲不避。他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说:“上天赋予我改造国家的责任,如今事业未成,上天不会让我就这样被炸死的。”这极致的自信,其实是一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与浩然正气。
陈垣是大师级学者、教育家,特别是在宗教史方面,堪称首屈一指。陈垣家中有3部佛教的《大藏经》和一部道教的《道藏经》,他与同事、好友开玩笑时说:“唐三藏(即唐僧)不稀奇,我有四藏。”为了查证历史年月,陈垣花200银元从日本购得一部《三正综览》的副本,以此为基础,自己进行了长时间编排演算和验证。对于其中的清朝部分,陈垣借助清朝的皇历逐年逐月逐日校对,成为万无一失的珍本。遇到别的著作有与此不同的说法,陈垣说:“这个我有十足的把握,可以以我的说法为确。人不能什么都自负,但这件事我可以自负,我也有把握自负。”
陈垣所谓“有把握的自负”,本质上是一种建立在扎实研究功底上的自信。“有把握的自负”,重点是“有把握”,而不是自负。怎样才能做到有把握呢?陈垣做学问非常严谨,强调史学研究者在搜集和使用史料时,来不得半点马虎:一是要使用第一手材料,二是对材料的搜集要竭泽而渔。竭泽而渔即要努力把已经有的研究成果和材料搜罗殆尽,然后通读全部材料,细心深入研究,才可做到心中有数。
所以,谦虚固然是一种美德,但建立在“有把握”基础上的“自负”,亦是一种自信的表达。这样的自信实至名归。
(责任编辑/刘大伟 张金余)
——兼论自谦语的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