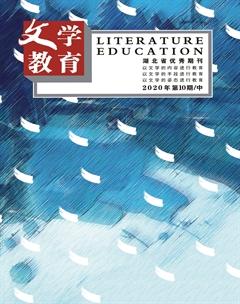奥索菲桑:在传统文化中新生的第二代戏剧家
内容摘要:费米·奥索菲桑是尼日利亚当代著名的作家、戏剧家、诗人,同时还是戏剧导演、文学理论家和大学教授。作为著名的“第二代戏剧家”,奥索菲桑在他的戏剧创作中,对某些已确立的传统、规范和价值观进行了重新诠释和改变,他的戏剧不仅停留在社会批判层面,而且深入到社会问题中去挖掘和揭露问题的根源,让人们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1]。在非洲国家政体转型的关键时期,他以戏剧作为革命的工具,对不同时期的统治者操纵历史的方式做出回应。
关键词:非洲文学 费米·奥索菲桑 《艾苏和流浪歌手》
一.为“沉默”发声的民众代言人
后殖民主义的特殊背景,经过血的洗礼以及残酷的军人统治,加之自身的生长环境,使得以奥索菲桑为代表的“第二代戏剧家”们不得不以戏剧为载体,在激进主义中去批判政治、反抗现实,同时出身贫苦阶级的他也积极成为“沉默”的大众的发言人,反映边缘化的声音。
奥索菲桑(Femi Osofisan,1946-)出生于尼日利亚西部小镇,在他仅三个月大时,父亲就不幸去世。他在伊巴丹政府学院接受了中等教育,他于1967年和1968年到位于塞内加尔的达喀尔大学学习,1969年获得法语学士学位,1974年获得博士学位,他还在1971年至1973年期间就读于巴黎第三大学。
1973年,奥索菲桑结束大学讲师的生活并于次年获得戏剧博士学位后,就与年轻的激进知识分子一起研究马克思主义,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探索社会责任的缺失问题。奥索菲桑的主要剧作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创作的,有的是对当代政治问题的大胆描述。如《一群不安分的蝗虫》(A Restless Run of Locusts);有的是寓言类的戏剧,如《艾苏和流浪歌手》(Esu and the Vagabond Minstrels)和《曾经的四个强盗》(Once Upon Four Robbers),这一类创作是基于非洲说书人的讲故事传统。还有一些作品可以被称作历史剧,因为它们是基于约鲁巴人的历史事件,如《喧哗与歌声》(The Chattering and the Song);还有一些作品是他试图颠覆“第一代创作”主题的剧作,例如《没有更多的浪费品种》(No More the waste Breed)的主题的就来自索因卡的《强种》(Strong Breeds)中的主题。
最终,以奥索菲桑为代表的剧作家形成了一个新的非洲戏剧传统,剧作家的文本大都参考非洲戏剧的整个领域,在对传统的借鉴与超越中,他们的作品不仅仅反映了一代又一代非洲人政治上的挫败感,更要试图去找到一种新的扎根于非洲土地和文化渊源的写作传统。
二.《艾苏和流浪歌手》的文化语境和艺术特色
《艾苏和流浪歌手》是奥索菲桑广受欢迎的一部剧作,戏剧开头先介绍了故事发生的背景:因政府改革使五个音乐家沦落到流离失所,无从饱食的困境,走投无路下不得不跟随奥米莱特来到艾苏的家,并恳求艾苏帮助他们摆脱饥饿并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于是艾苏让流浪歌手们服下“愿望种子”,并以唱歌跳舞的形式帮助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事后便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得到相应的报酬)。
戏剧结尾,流浪歌手们实际上进入了艾苏的恶作剧中,当艾苏要实施他的惩罚时,约鲁巴神话中的大牧师(奥孙)和河神(奥伦米莱)在天花之神(奥巴拉耶)的帮助下,拆穿了艾苏的计谋,奥米莱特的疾病被治愈并获得了奖励。至此“戏中戏”的表演结束,演员脱下伪装,回归现实,并与观众一起演唱《艾苏是不存在的》。
《艾苏和流浪歌手》是一部具有高超的戏剧表现技巧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作品,主要表现在:
第一,巧妙的戏剧结构与开放的戏剧结尾
首先,《艾苏和流浪歌手》巧妙采用了“戏中戏”的戏剧结构。戏剧一开始部落首领邀请领唱阿迪为大家展示他们为下周比赛准备的参赛作品,由此“艾苏和流浪歌手”成为该剧的“同名戏中戏”,剧作沿着“艾苏和流浪歌手”这条内部线索逐渐拉开了序幕。
整部剧共有四幕:管弦乐队、序曲、鸦片、残留。其中第二、三以及第四幕中的前半部分均是“戲中戏”的相关内容[2]。这种故事嵌套的模式,可以让读者在戏剧排演的过程中逐渐深入剧情,并利用观众的社会心理与剧中人物的命运发生共鸣,直接参与到剧作中去,对剧中人物的行为进行思考,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使其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戏剧的一部分,极大增加了观众的参与度。
其次,开放的戏剧结尾。奥索菲桑为了表现不同的意见并对观众有所教化,经常设置问题化、开放化的戏剧结尾。
结尾处,艾苏将奥米莱特是否应该将麻风病还给那对男女的问题抛给观众。“……你们不要只是坐在那儿,来主持正义吧!说点什么!奥米莱特是应该把疾病归还呢,还是要保留它?大声说,我们需要你的答案来做决定!这位先生?这位女士?”[3]奥索菲桑巧妙的利用观众的看客心理,在剧作将要达到高潮,观众们迫切的想要知道最终的判决究竟是什么时,陡然一转,将戏剧接下来的发展方向交给观众来决定,这种权利的赋予,极大的提高了观众的参与感,进一步拉近了观众与演员与剧本的欣赏距离,观众在不自觉中加入戏剧的表演中,成为剧本的一部分。奥索菲桑利用开放式的结尾,给予观众充分的时间直面社会现实,在对戏剧的激烈讨论中直面自我,从而得出自己的价值判断与现实思考。
第二,“故事说书”的传统模式
“故事说书”[4]式的口头传统在西非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许多西非作家在自己的创作中都借鉴并运用了这一传统形式。对于奥索菲桑而言,他希望能够通过民间故事策略弥补以“对话为主”的西方戏剧的“不足”[5]。在作家的戏剧创作当中,“魔力剧”最能体现西非的口头传统。
《艾苏和流浪歌手》作为奥索菲桑最有影响力的一部“魔力剧”,戏剧中超自然力量因素的存在体现了尼日利亚对于传统的“返魅”[6],同时《艾苏和流浪歌手》也是迄今尼日利亚连续演出时间最长的一部“魔力剧”,谈到这部剧的受欢迎程度,奥索菲桑认为,采用了传统的“故事说书”模式,是这部戏剧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谈到戏剧的形式,你知道,我总是非常关心戏剧的形式问题。一些批评家甚至认为形式对我来说至高无上,我对于形式问题给予了过度的重视。的确,我总是将传统生活中人们的娱乐形式(如故事说书、我们熟知的月光故事等等)铭记于心,也总是试图将之搬上现代舞台,找回它们曾带给我们的那种交流关系。剧院,是观众和民间语言的绝佳平台[7]。因此,对传统“故事说书”形式的借鉴,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读者与剧本的距离,便于读者参与其中,与人物情节进行对话,让观众产生一种“戏剧演出等同于故事说书”的情感联结,在情感纽带与传统心理的共同刺激下,增添了戏剧的亲和力,便于剧作家与读者之间更为顺畅的交流,从而使读者更易于接受剧作。总之,这种“故事说书”形式的运用是作者戏剧创作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三,隐喻与音乐剧形式的结合
动物故事在西非故事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受此影响,奧索费桑在许多戏剧作品中也多借用动物形象来暗指某些观点,《艾苏和流浪歌手》也不例外,如女流浪歌手吉金的唱词“贸易之路,为狮子敞开着;金钱之路,对兔子来说很狭窄;”[8]作者在这里用狮子和兔子的意象来暗指现实生活中贫富阶级的巨大差距。
奥索菲桑的戏剧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而隐喻对奥索弗桑来说则是一种强大而又具有深刻意义的文学工具,它可以讽刺和惩罚社会上的压迫性结构,启迪和揭露大众的真实情况,从而激发他们团结起来,争取自由和彻底解放。因此,隐喻被剧作家充分地运用,以加强在他的戏剧中普遍存在的反抗主题。
音乐和舞蹈是西非戏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这些特别设置的音乐、言辞、动作、节奏、舞台关系将人们的各种感官都调动起来,营造出富有色彩和诗意的舞台空间。具体到奥索菲桑的作品,几乎没有任何一部戏剧作品能缺少舞蹈与音乐的配合,这种特点在《艾苏和流浪歌手》一剧中也十分突出。这部作品分别由管弦乐队、序曲、鸦片、残留四幕构成,每一幕戏剧情节的发展与结束分别由一首歌来推动与收束。而戏剧的五个流浪歌手,则通过唱跳的形式来使用艾苏赋予他们的魔力。歌曲既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关键,同时独特的表演形式可以使观众随时都可以加入歌曲和舞蹈当中,成为这场音乐盛会的一部分。在这里,作者充分考虑了观众的需求,采用近似于音乐剧的形式,能够极大的调动观众的观剧热情,最大限度地提高观众的参与度。
三.《艾苏和流浪歌手》的思想内涵与文化寓意
《艾苏和流浪歌手》中塑造了两类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一类是善良无私的形象,主要代表人物是奥米莱特,其次还有奥孙、奥伦米莱以及奥巴拉耶;第二类是贪婪自私的形象,代表人物有吉金、辛辛、雷德欧、埃普·奥伊博和艾苏。
这两类人物之间的对话交流,人物命运的不同选择,将各自所属的特质完全的展露在观众面前,通过二者的表演对话及命运发展,观众不仅可以将自己代入特定的情景选择自己归属的一方,同时也可以对人物(或自己)的选择做出相应的反思。这种反思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现实与理想的距离
“戏中戲”里面的音乐家们因为政府改革,社会动荡而成为了一无所有的流浪汉,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摆脱流浪,免于饥饿,可却在基本欲望实现的过程中处处碰壁,不得已陷入了艾苏的恶作剧中。同时,他们对帮助对象的不同选择,也隐含了作者深沉的现实忧虑与理想的道德期待。
首先是善良的奥米莱特,他选择帮助被怀孕所累的妇人以及患麻风病的男女,前者贫困潦倒不能对他的帮助给予任何回报,而后者不仅得不到回报甚至还使奥米莱特失去了自己的健康。可尽管如此,奥米莱特仍然不后悔自己的决定,他将自己的私欲抛诸脑后,选择放弃换取财富的机会乃至今后生活的一线生机,将自己步步推到绝境,却为贫弱的妇女与患病的男女赢得了生的希望,在奥米莱特身上寄托着作者对社会道德现状可以得到净化的殷切期许。
相反,其他的流浪歌手们,有的爱慕财富选择帮助非法牟利的商人、违背合作道德的经理,有的贪慕虚荣选择帮助因反抗传统迷信而逃亡的王子,流浪歌手们每一次的“善意”下,都充满着各种目的性,他们漠视道德的教化,只注重现实金钱的获取,只看重现实生存的价值。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理想与现实之间是很难到达平衡的,现实中存在诸多干扰理想的因素,因此,大多数人不得不败给现实的残酷,而无力去编织理想的梦境。在剧中,奥米莱特是作家理想道德的化身,尽管他的精神是高尚的,但却不得不面对难以生存下去的窘境,但是现实生活中究竟有几个人是能真正放弃“小我”,升华“大我”?相比之下,其他的歌手们则显得如此贪婪、自私,丑恶不堪,但我们在批判他们的同时却不能不换位去理解他们的选择,因为他们确实无力反抗现实,这种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使得他们丢弃了自我,这是对人类生存现状的残酷暴露,是对现实本真的还原。
第二,金钱与道德的选择
剧作中的流浪歌手们在生活的牢笼中不断挣扎着,在这里,对于“生”的渴求已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目标,这种境况下,对物质财富的追求远大于对道德精神的追求。在剧中,除了奥米莱特拒绝了物质金钱的诱惑,将道德作为衡量价值的标尺外,其余四人均陷入了物质金钱的沼泽,善恶是非不分,将道德推向了深渊。他们或帮助以非法手段牟利的商人;或为了换取大量的财富帮助陌生人找寻丢失已久的许可证;或出于虚荣,救助了因反抗传统、破除迷信而逃亡的王子,他们将金钱视为人生的必要追求,一味地追求财富利益带来的巨大快感,以至冷眼旁观贫困的怀孕妇女以及威胁自己生命安全的麻风病人,人性的冷漠在他们这里可见一斑。
当然,我们无法对于五位流浪歌手们的选择做出简单的判断,因为,如果从道德层面上来看:四位流浪歌手抛去道德,忽视人性的精神追求,这显然不符合我们所追求的道德标准,但从实际出发来看,现实动荡,政治混乱,流浪歌手们没有生存的基本保障,只有物质财富才可以给他们带来安全感,现实使他们不得不沦为金钱的奴隶。因此,人性冷漠的背后,导致其发生的内在机制才是更值得我们去反思的。
第三,魔法与希望的交替
作为奥索菲桑最受欢迎的一部“魔力剧”,《艾苏和流浪歌手》中充满了奇幻的魔法世界,约鲁巴神话价值体系中超自然力量因素的存在更是平添了戏剧的神秘性。但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魔法终究是不存在的,戏剧的结尾,魔法消失、神明退场,演员与观众合唱《艾苏是不存在的》。但魔法的消失并不代表希望的消失,作家在剧中提出了有现实针对性的“疗法”,正如剧中的唱道:“让我们建设社会,因为我们可以。”“只有像这样坚决的声音才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9]这是魔法退去后,人们的选择,是动乱现实中的人民的觉悟。这也是作者奥索菲桑呼吁人们积极去寻找的东西。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艾苏和流浪歌手》是一部关于政治批评与现实讽刺的戏剧,其中充斥着人类各种不文明的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作家依旧对故乡的人们充满信心,对这片神奇的家园的重构充满信心。虽然作品隐喻贪婪、自私与堕落,显示了人们内心的焦虑与不安,但作品中的黑暗并不能泯灭作家对光明未来的企盼,哪怕这片土地已血迹斑斑,但作家依然以同情爱怜的心去抚恤他的伤疤,“因为我们可以建设社会”,这就是作家对现实发出的强有力的呼喊,是作者深入社会问题本源后提出的“疗法”,也是奥索菲桑致力于用文学服务社会,服务人类的体现。
四.结语
奥索菲桑作为尼日利亚“第二代戏剧家”的主要代表,被认为是继诺贝尔文学获得者沃莱索卡因之后,尼日利亚最重要的戏剧家。[10]奥索菲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强调剧作家的社会责任。他试图通过多种方式使戏剧反映尼日利亚社会的问题,并使他的戏剧成为探讨这些社会问题的平台[11]。对奥索菲桑来说,他面对的不再是民族独立后的兴奋,而是对殖民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的反思。因此,他的作品包含了更多的社会政治因素。他将本土表演方式与西方殖民艺术技巧相结合,呈现出一种非洲文化和西方文化交织的混杂生态,使戏剧充分发挥教育民众,启迪民智的功用;同时,身处国家转型的时代,奥索菲桑自觉地承担起“文学服务社会”的责任,作品中充斥着社会批评和政治干预的特色,将戏剧作为批判社会政治的有力武器,积极推动社会秩序的有力变革。总之,奥索菲桑的作品是多种元素,多种现实碰撞出来的结晶,读他的作品我们可以慢慢窥见非洲历史的演变,体味驳杂的文学元素,因此,在面对非洲独立后更加复杂的社会现实时,奥索菲桑作品中所蕴含的复杂深刻的思想内涵是值得我们慢慢品评钻研的。
参考文献
[1]Tess Akaeke Onwueme. Visions of Myth in Nigerian Drama: Femi Osofisan Versus Wole Soyinka[J].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La Revue canadienne des études africaines, 1991, 25(1): 58-69. DOI:10.1080/00083968. 1991.10803878.
[2][10]赵聪.文化冲突与政治关怀——论尼日利亚作家费米·奥索菲桑戏剧创作的文化品格[D].北京师范大学,2011.
[3][8][9]费·奥索菲桑[尼日利亚],赵聪(译).艾苏和流浪歌手[J].世界文学,2012,(2):211-292.
[4][5][7]程莹.“故事就像风”:试论奥索菲桑戏剧中的西非故事说书传统[D].北京:北京大学,2012,p.407-425.
[6]程瑩.“我们的传统是非常现代的传统”:解读非洲文本的另类方式[J].中国图书评论,2017(04):81-88.
[11]GARETH GRIFFITHS. Femi Osofisan 1946-[J].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非洲文学史》【项目批号:17FWW001】
(作者介绍:于欣群,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外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