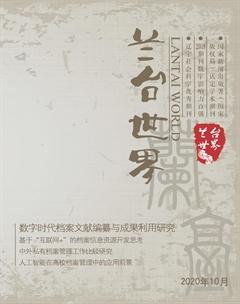档案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功能定位和实现路径研究
摘 要 本文立足于以档案效用助推意识形态工作,探析了档案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功能定位和实现路径。首先剖析了档案自身可与意识形态工作需求适配的鮮明特质,接着阐释了档案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功能定位,如意识认同功能、意识聚合功能、意识导向功能及意识表达功能,最后从工作导向、资源开发、宣传建设、服务品质等方面提出实现功能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 档案 意识形态工作 功能定位
中图分类号 G273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20-07-13
★作者简介:孙洋洋,求是杂志社办公室助理馆员,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档案管理,中国社科院博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bstract With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ideological work via the use of archiv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unctional positioning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archives in ideological work. First, the clear characteristics that archives can be adapted to the needs of ideological work are put forward. Then the functions of archives in ideological work are illustrated, such as ideology identification, ideology aggregation, ideology guide and ideology expression. Finally, effective ways to realize the functions are proposed from the aspects of work orientation, resources development, publicity construction, and service quality.
Keyword archives; ideological work; function positioning
当前,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信息科技日新月异,国内国际关系不断变革,意识形态工作领域的形势也更加复杂多变,态势也更加紧张严峻,为此,党和国家不断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论断、新举措,以充分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档案事业承担着“为党管党、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神圣职责,应以“对历史负责、为现实服务、替未来着想”为宗旨,充分挖掘档案资源的价值,探索档案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的契合点,积极彰显档案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的积极意义。
一、档案与意识形态工作需求适配的特质
档案之所以能够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发挥作用,从根本上来讲,是其本身所具有的鲜明特质与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在需求在一定层面上相吻合,形成了档案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的契合点。其特质主要体现为下几方面。
1.原始记录性。吴宝康先生在《档案学概论》中指出,“档案是历史的原始记录,或说是原始的历史记录,这是档案的本质属性”,且“档案以兼具原始性与记录性于一体的突出特点区别于其他资料”[1]3。档案伴生于人类的行为实践活动,是对历史事实真实客观的记录且具备保存价值。这种观点一直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笔者在此不作赘述,仅就此特质与其他特质的关系略作阐释:原始记录性也即档案的内部规定性,是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标志,也因其“非排它性”成为表现或延伸出其他属性的轴心,如基于属性表征论的“真实、客观性”,基于现实效用论的“备以查考性”和“历史再现性”,基于内容剖析论的“有机联系性”和“可追溯性”,以及基于交集论的“多属性统一性”,都需要在“原始记录性”这一本质属性的前提下进行理解、界定和阐释。
2.历史性。由于档案是对“过去时”的记录,因此其“历史性”与“原始记录性”可谓档案的一体两面。参考王英玮教授的阐释,历史性可理解为档案内容的本源性、形成者的真实性以及档案形成过程的历时性[2]21-23。换言之,即当时的实践主体在特定的历史活动背景之下,使用相应的记录符号或工具对现象、事物或实践行为进行了有意识的记录并保存下来,形成了历史载体。档案的历史性又具备两个重要特点:一是档案自身具有的未加工的原生性,使得其历史性更为朴素和真实,往往可作为历史资鉴的重要凭证;二是档案卷宗所具有的有机联系性,使得其历史性更为连续和系统化。
3.社会性。正如马克思所言,人是历史的剧作者,也是历史的剧中人。我们在对档案这一历史的原始记录的属性进行探讨时,自然不能忽略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人。人之于档案,不仅是记录的客体,也是记录的主体,人与人的普遍联系构成社会,档案也同样具有社会性。一是体现在档案记录了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社会实践活动,是社会实践的信息载体形式;二是体现在档案形成于人们有意识地推动社会实践活动,本身就蕴涵了人类主体的行为意向、价值基础和实践理念,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存在内在契合的关系。
4.文化性。从档案本身来讲,作为人类历史活动的原始记录,在纵向上贯穿历史脉络,在横向上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科技等方面,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发展成果的历史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回溯历史文化的着眼点,也是发展未来文化的资源库。《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2020年6月20日修订版)第二章第十条指出,中央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各类档案馆是集中管理档案的文化事业机构,负责收集、整理、保管和提供利用各自分管范围内的档案。由此可知,档案机构及事业本身具有一定的文化属性,与文化事业存在明显交集,是推动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动力。
二、档案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功能定位
1.基于文化观的意识认同功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是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体现。文化的力量是民族生存和强大的根本力量[3]243。传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加强文化认同进而增强意识认同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内容。档案作为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记录载体,作为中华民族为了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见证者,蕴含着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等深层次意识。例如,透过档案观摩到的党史、新中国史以及改革开放史,感受到的“沂蒙精神”“西柏坡精神”“延安精神”,体会到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马家浜文化”等,都充分展现了中华文明融会多元文化的特质,有利于促进中国人民从中华文化中吸收价值观、道德观以及民族观的内涵,不断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
2.基于成果观的意识聚合功能。成果观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的“价值关系论”,将档案理解为人类社会各组织和社会成员通过有意识的创造性劳动,逐步积累和保存下来的维系和促进人类历史文明延续和发展的物质和精神文化财富[4]2。从这一角度来讲,档案因其历史性和社会性而具有先天性的意识聚合功能。以家庭为单位來看,家庭档案是记载家庭事物和实践活动的载体,有着鲜明的时代色彩,是代际之间理解和传承的重要纽带,有利于沟通情感、和睦家庭、涵养家风。以城市为单位来看,档案是体现和延续一个城市历史文脉的载体,是城市魅力的关键所在,有利于人们以地理区域为划分,认知、理解和认同本土风俗、文化和情感根基。以民族为单位来看,档案是不同民族历史信息、血脉和联结的载体,承载着民族的历史沧桑和岁月痕迹,蕴含着民族文化风格和传统风貌,是加强民族团结意识的重要基点。
3.基于规则观的意识导向功能。“规则观”是以管理学思维为导向的,重在强调档案的工具价值,认为档案是社会组织出于自身管理活动的需要而形成的文化载体,因而可在组织内部的管理活动中发挥作用[5]100。为此,档案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同样具备一定的管理功能,主要体现在意识导向方面。一方面,档案是中华民族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的重要源泉,能够跨越时空与具有当代价值的精神对接,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另一方面,档案作为历史的原始记录,具有不可比拟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能够有力阐明相关历史渊源、基本走向和演进脉络,有利于有效应对当今的各种歪曲历史、误读国情的不利社会思潮,如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从而引导人们旗帜鲜明地抵制错误思潮、坚定树立科学观念。
4.基于传播观的意识表达功能。当前意识形态建设迫切需要增强话语权,增强对外交流的公信力、创造力和感召力,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课题。用档案说话,就是用事实说话,用历史说话。以档案资源为基础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具有独特的意识表达功能。首先,具备了民族特色,能够从客观、真实的角度展现中华民族的历史和传统;其次,破除了国界障碍,政治交往有国界,而文明交流互鉴是没有国界的,档案这一重要的人类文明载体有利于跨越地域和国界屏障来传播中国声音;再者,加强了情感表达,具备客观实在性的档案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能够在讲述中国故事时从感官上给人以直接、全面、立体的感受,从而增强话语阐释和意识表达效果。
三、档案服务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实现路径
1.明确立场,把握档案工作导向。方向和立场是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本性因素,要充分发挥档案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作用,使得二者相得益彰,就要先明确档案工作服务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原则立场和价值导向。意识形态建设关乎国家安全、民族安全和人民幸福,因此档案工作也要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明确其与意识形态建设、政治思想教育、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国家软实力的内在关联,以“在位”的姿态服务于党和国家大局,服务于人民的需要。如为了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加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宣传教育,中央档案馆积极开办专题档案展览,加强档案编研并摄制了一系列纪录片[6]112。以《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为例,它是由中央档案馆整理、中华书局编辑发行的,共收录842名战犯的笔供,涉及笔供档案近63000页,基本上无删节、无修改地呈现了侵华战犯的亲笔供述,严格尊重了档案的原始性和权威性,可以说是再现日军侵华历史、揭露日军掠华罪状的有力凭证,也是强化民众爱国主义情感和和平愿望的生动教材,不仅有力回击了历史虚无主义、维护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也有效增强了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
2.加强开发,挖掘档案资源价值。档案作为人类文明伟大进程的记录者,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历史载体,是展现中华文明、还原中国历史、传达中国话语的宝贵资源,因此我们应全面加强对档案的开发利用,充分挖掘档案的深层价值,并将其融入我国的意识形态建设中。从内容建设角度来讲,可以通过对历史文化档案的开发,引导人们从历史事迹中体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观念,通过对红色档案的开发引导人们从革命史实中体会为实现民族复兴不懈奋斗的理想信念,通过对法治档案资源的开发引导人们体会公正法治爱国诚信的价值理念[7]。从开发路径上来讲,应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创新档案资源开发举措,一方面要采用学术性开发的形式,加强与科研机构的合作,挖掘档案资源的学术价值,积极推出相关研究成果,为意识形态建设提供知识性、信息性的支持;另一方面要采用市场化开发的形式,积极与当下的社会形态和经济需求融合,使档案承载的深厚内容以接地气的方式融入公众意识,加强档案与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互动。
3.创新宣传,丰富档案宣传内涵。要以“守土有责”的原则占领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权和主导权,就要创新方式方法做好宣传思想工作,档案宣传工作也不例外。新时代,档案宣传工作应当顺应社会发展趋势,适应大众心态,创新宣传手段。首先,档案宣传工作应加强与媒体平台的合作,联合打造传播精品,为自己配备“扩音器”。如北京电视台于2009年2月开播的纪实栏目《档案》,以档案作为内容主体,回放案件和事件发生实录,生动展现了人生百态和社会现象,满足了观众视觉冲击感和对于事实的渴求感;其次,档案宣传应积极与信息科技相融合,应用公众喜闻乐见的信息接收方式。当下,档案领域的微信公众号已较为普遍,笔者关注较多的“档案那些事儿”“档案春秋”“中国档案报”已积累了一大批受众,并且展现出时度效较强的特点。下一步,档案宣传可在H5、VR技术的应用、音视频的制作以及微博、博客等平台的入驻方面进一步推进,从而多渠道、全方位加强档案宣传效果,从而参与到网络意识形态建设中来。
4.聚焦服务,提升档案服务品质。从本质上来讲,意识形态工作是关于“人”的工作,重在凝心聚力、成风化人,出发点和落脚点都要着眼于人。从这点来讲,档案工作要服务于意识形态建设,也应该把服务于人作为工作重点,不断拉近档案资源与大众的距离。首先,档案工作部门和人员应该加强服务意识,在做好档案保存和管理工作的同时,加大对提供利用的关注度,从思想、态度和行为上增强服务意识;其次,档案资源的开发要积极适应人民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对于文化资源的需要,匹配人民群众的层次性和差异性,注重对高校师生的教育和引领,进而在凝聚共识方面充分发力;再者,档案服务的内容应及时跟进社会发展节奏,不仅仅局限于查档供档方面,而是以主动的姿态走进社会、贴近大众,如开发一系列以档案为基础的文创产品,将档案转化为时尚活泼的实体形式进入市场,以崭新的风貌融入大众生活[8]14。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内容,积极实现档案在其中所具备的功能便是服务于党和国家发展大局的体现,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体现,为此,如何充分挖掘和实现相应功能是需要我们在研究和实践中不断探索的课题。笔者认为,在相关的研究中,应把握三个基本点:一是不可偏离档案的本体特质这一立足点;二是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顺应和跟进时代发展潮流;三是要坚持问题导向,着眼于意识形态工作中的疑点难点重点开展研究,从而产生有实际价值和应时效用的积极成果。
参考文献
[1]吴宝康.档案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3.
[2]王英玮.关于档案本质属性的思考[J].档案学通讯,2001(2):21-23.
[3]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243.
[4]王英玮.档案文化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2.
[5]胡鸿杰.维度与境界:管理随想录[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15:100.
[6]柴丽.档案宣传实现党性与人民性统一的路径分析[J].档案学研究,2019(2):112.
[7]杜童欣.論档案在强化制度认同中的功能与路径[J/OL].山西档案.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4.1162.G2.20200115.1037.002.html.
[8]熊文景,徐拥军.论档案文化的意识形态整合功能[J].山西档案,2018(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