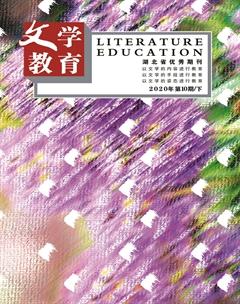论柏拉图《理想国》中的“逻各斯”与“秘索思”
内容摘要:“逻各斯”(logos)与“秘索思”(mythos)是西方文化中的一对核心概念。从“秘索思”与“逻各斯”这一维度对《理想国》进行考察,可知《理想国》旨在宣扬“逻各斯”,实则隐含着丰富的“秘索思”思想。由《理想国》延伸至艺术,“逻各斯”与“秘索思”的启示同样值得关注。
关键词:柏拉图 《理想国》 “逻各斯” “秘索思”
一.“逻各斯”与“秘索思”
作为西方文化的核心概念,“秘索思”通常被视为想象的、虚构的,“逻各斯”则是研析的、实证的[1]。德国古典学家威廉·奈斯特尔的《从秘索思到逻各斯》研究了“秘索思”与“逻各斯”这对概念。奈斯特尔认为,公元前五、六世纪,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先贤的努力使得哲学逐渐取代宗教,逻辑取代寓言,“逻各斯”取代“秘索思”并创造出有序的理性世界。[2]布鲁斯·林肯对奈斯特尔的上述观点提出了质疑,并从希腊早期文本出发进行了溯源。
在《性别话语:“神话”与“逻各斯”的早期历史》中,林肯指出“秘索思”与原始、粗俗、本真等特征相关。如在《伊利亚特》开篇场景中,阿伽门农就对祭司克里西斯宣扬了要霸占其女儿的神话。通过粗俗与暴力的“秘索思”宣言,阿伽门农成功向对手发出了挑战。理查德·马丁对《伊利亚特》中的“秘索思”及相关动词的使用状况进行了统计,指出“秘索思”的出场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和有权势的男性发出命令有关。[2]至于“逻各斯”,指向的则是与“秘索思”相对的部分,如柔软、间接、狡猾、理性等,通常以“logoi”的形式出现。在《奥德赛》中,“逻各斯”指卡利普索用来哄骗奥德修斯的甜言蜜语。同样,在《赫西奥德》中,潘多拉也被描述成诱人的“logoi”。通过文本分析,林肯得出了“秘索思”与“逻各斯”指向不同的话语——好斗的男性与誘人的女性的结论[2]。
显然,林肯是从性别话语出发对“逻各斯”与“秘索思”进行解读。如林肯所言,史诗中的贵族男性通常使用“秘索思”作为武器震慑敌人,但到民主时期或已行不通。公元前五、六世纪以后,希腊陆续受到埃及的几何学和巴比伦的数学及天文学影响,由精妙语言组成的逻辑严密的“逻各斯”成为哲学的得力武器,而“秘索思”随之成为虚假、蒙昧的代名词。[3]
为“逻各斯”与“秘索思”下确切定义是困难的。二者关系并非绝对的二元对立,而是于交织对立中不断演进。早期“逻各斯”兴起后,逐渐建立了一套规则,却又在中世纪被“秘索思”巧妙替换。中世纪宣扬神学,为分享“逻各斯”的权威光环,神学家们开始用“逻各斯”来宣扬神学,如早期基督教将“逻各斯”视为神的理性或智慧。“逻各斯”名义上占据了主导,实则只是潜伏在底层的“秘索思”所穿的外衣。文艺复兴爆发后,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的狂潮席卷而来,此后“逻各斯”又逐步占据了人文与科学的主阵营。近代以后,许多思想家又将视角转回了“秘索思”,企图从秘索思那里去汲取营养,探讨复杂的现代问题。如弗洛伊德从古老神话寻求材料,提出了俄狄浦斯情结;荣格思考集体无意识,追溯充满“秘索思”色彩的原始意象等。简言之,二者始终处于复杂的动态关系之中。
二.《理想国》中的“逻各斯”
《理想国》中“逻各斯”与柏拉图本人的知识背景有密切关系。柏拉图就曾求学于数学家德奥多罗,对赫拉克利特和毕达哥拉斯学派也十分了解,阿卡德米学园门前刻有“不懂几何学者勿入”字样的石碑即是例证。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就曾提及柏拉图对赫拉克利特教义的娴熟[4]。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多次论述数与计算对于技术、科学甚至城邦治理的重要作用。丰富的数理知识背景为柏拉图思想中“逻各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五、六世纪后,与逻辑推理、自然哲学密切相关的“逻各斯”受到西方学者的重视。“秘索思”则逐渐带上贬义,如人们“开始抱怨和批评荷马用诗和诗化解释一切的做法”,并“着意于试图从神话以外寻找解释宇宙和自然的途径”[3]。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对“逻各斯”极力宣扬,虽然有时言“逻各斯”而意在“秘索思”,有借助“逻各斯”权威光环的嫌疑,但通过分析《理想国》的对话体形式、对世界本源的探索以及严格的等级秩序,可以清晰梳理出《理想国》中丰富的“逻各斯”思想。
对话体是《理想国》最显著的文体特征。《理想国》十卷皆以对话形式展开,通常以苏格拉底的提问开始,然后在其精神助产术的循循诱导下,引导对话者得出与苏格拉底主张相似的结论。“对柏拉图来说,对话是一种精心指导的灵魂互动,在这种互动中,人的整个灵魂被展示出来,不仅有他的理性,还有他的精神和欲望。”[5]对话体的层层推导、严密逻辑可以最大程度地将各方探讨的问题的本质挖掘出来。柏拉图的对话体与“逻各斯”密不可分。“逻各斯”的整合能力使《理想国》的对话体吸纳了戏剧、史诗、神话、寓言等众多文体要素,增强了说理分析能力。苏格拉底精神助产术的屡试不爽即是鲜明例证。
对世界本源的思考也是《理想国》中“逻各斯”的闪现。“逻各斯”追寻永恒、稳定的真理,往往通过否定感性易变的现实世界来探寻其背后的稳定成分。在《理想国》第十卷中,苏格拉底与格劳孔就床与桌子的本质、制作与模仿进行了探讨。
画家、造床匠、神,是这三者造这三种床……神由于知道这一点,并且希望自己成为真实的床的真正制造者而不只是一个制造某一特定床的木匠,所以他就只造了唯一的一张自然的床。[6]
一番讨论后,苏格拉底最终引导格劳孔得出了神造的理念才是真实,制作与模仿只是虚假的结论。这种形而上的推导正是“逻各斯”中理性力量作用的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也蕴含“秘索思”的神秘成分,毕竟理念世界终究是无法感性接触、认知的。
“逻各斯”对理性的追求使其走向对等级的划分。在《斐德罗篇》中,柏拉图就曾对灵魂进行了九类划分,这些划分以对神及真理的接近即以对“逻各斯”的接近为准则。《理想国》中的等级色彩同样浓重,如对“王者型、贪图名誉者型、寡头型、民主型、僭主型”[6]五种政体及对应人物心灵的划分,对城邦的三种等级与人心的三种快乐的划分等。
等级划分是“逻各斯”作用的结果,其划分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看似合理的比较来对人心优劣进行分类,既巩固了统治秩序,又立下了高贵的谎言,从而降低底层人民反抗的可能性。法国当代激进哲学家朗西埃就曾在《歧义:政治与哲学》一书中批判柏拉图《理想国》思想中的等级主义。朗西埃指出,柏拉图关于共同体的计划“完全取代了政治的民主形态”,预设了“共同体时间与空间的完全饱和”,在严格的等级关系中,“安分守己便是对人民‘自由的严正回应”。[7]换言之,在柏拉图所设想的理想国中,共同体处于饱和状态,民众被划分为不同等级并被严格规范,“逻各斯”以强有力的论证能力说服民众要安于本分,取消了民众反抗的机会。
《理想国》中的“逻各斯”思想十分显著,具体体现在内容、形式各个方面。但就此将柏拉图划分为“逻各斯”主义者未免过于武断,其思想中还有许多“秘索思”倾向,如对话体中的寓言、神学色彩等。这些“秘索斯”往往以服务“逻各斯”的隐秘方式呈现。
三.《理想国》与“秘索思”
学者宋继杰研究了柏拉图早期的《普罗泰戈拉篇》到晚期《法律篇》,指出“秘索思”在其中共出现87次,并将其用法归为三类:一是指涉希腊传统神话;二是本人想象的神话;三是本人的学说。在柏拉图的文本中,“秘索思”的用法发生了变化,原本较中性的“秘索思”逐渐向负面意义倾斜。究其根源,主要有三种原因,一是神话难以进行理性论证;二是神话具有特定性,缺乏普遍性;三是演绎规则不严密,缺乏逻辑性。[8]这些变化预示着“秘索思”的缺陷在柏拉图时期已经被揭示,而柏拉图对其的使用也将发生变化,不会像使用“逻各斯”时那般“光明正大”。
《理想国》中的“秘索思”蕴含着神秘、独断以及煽动性等特征,是柏拉图宣扬自身政治哲学思想的重要武器。以下从神学色彩、寓言叙事以及对诗的态度三个角度出发对《理想国》中的“秘索思”进行探析。
《理想国》中的“秘索思”与书中浓厚的神学色彩密切相关。在第二卷中,柏拉图就曾以苏格拉底的口吻为诸神辩护,认为神合乎正义,是善的原因。
神既然是善者,它也就不会是一切事物的原因——象许多人所说的那样。对人类来说,神只是少数几种事物的原因,而不是多数事物的原因。我们人世上好的事物比坏的事物少得多,而好事物的原因只能是神。至于坏事物的原因,我们必须到别处去找,不能在神那儿找。[6]
以上充满想象以及独断论色彩的观点无疑是“秘索思”式的。
寓言叙事也为“秘索思”的滋生提供了土壤。显然,《理想国》中的寓言叙事是为“逻各斯”服務的,换言之,其根本目的在于划分等级、维护城邦秩序。然而,寓言通过形象的故事来传达寓意,多为诗性讲述,与理性论证不同,不使用概念或逻辑,由此也就有了淡“逻各斯”而重“秘索思”的特征。在洞穴寓言里,柏拉图将人的生存环境喻为洞穴,洞穴中的多数人终其一生都将墙上的幻影当作真实的世界。通过洞穴喻,柏拉图形象地道出了有知者与无知者之间偌大的隔阂,也隐喻了城邦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如城邦对人的禁锢,心灵向上的困难等。在对灵魂构造的分析中,柏拉图也使用了寓言叙事,讲述并赞同了腓尼基人关于灵魂含有不同金属成分的传说,由此说服城邦中的民众要安于本分、服从政治安排。不难见出,寓言叙事是柏拉图宣扬政治哲学观点的重要武器。寓言的想象性、幻真性为其著作增添了煽动人心的功能,这也滋生了《理想国》中的“秘索思”。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对诗人的态度并非全盘否定,而是有褒有贬。在第三卷中,柏拉图直接否定了诗人。
假定有人靠他一点聪明,能够模仿一切,扮什么,象什么,光临我们的城邦,朗诵诗篇,大显身手,以为我们会向他拜倒致敬,称他是神圣的,了不起的,大受欢迎的人物了。与他愿望相反,我们会对他说,我们不能让这种人到我们城邦里来;法律不准许这样,这里没有他的地位。我们将在他头上涂以香油,饰以羊毛冠带,送他到别的城邦去。[6]
到第十卷时,柏拉图对以荷马为代表的诗人进行了审查,重申了驱逐诗人的决定,但态度已有所放松。
然而我们仍然申明:如果为娱乐而写作的诗歌和戏剧能有理由证明,在一个管理良好的城邦里是需要它们的,我们会很高兴接纳它。因为我们自己也能感觉到它对我们的诱惑力。[6]
在后来的著作《法律篇》中,柏拉图也再次谈到了诗人与城邦的问题,并得出立法者与诗人都是创造者的结论。如果悲剧诗人能像立法者一样对城邦有利,并以与立法者相同的声音发声,便可以获得承认[9]。柏拉图前后态度的转变无疑隐含着其对“秘索思”的考量。柏拉图对诗歌的态度是复杂的,他看到了诗歌对人心的腐蚀与迎合,但也看到了诗中“秘索思”的强大煽动能力。“秘索思”的幻真性、渗透性让它可以直击听众的心灵。
总的来看,“秘索思”与柏拉图自身的思想背景密不可分,具体体现在《理想国》中对神的敬畏、灵魂不朽的观念与寓言叙事手法等方面。柏拉图对“秘索思”的使用是深思熟虑的,既批判了“秘索思”中不利于城邦与人心稳定的成分,也充分利用了“秘索思”的直接性与煽动性,编造了各种政治谎言。
四.总结
有学者作过有趣的说明,当我们谈地球悬于海洋或从海洋突起时,这是一种神话叙事,而把它改写为‘一切万物出自于水,就成为了代表“逻各斯”的普遍公式。[10]在“逻各斯”与“秘索思”之间,其实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理想国》旨在宣扬“逻各斯”,但实则在内容、思想、形式等方面都富含“秘索思”思想,由此可见二者的复杂、交织状态。
纵观历史,人们常将“逻各斯”与“秘索思”置于二元对立中。科学与艺术的对立,哲学与宗教的对立,逻各斯中心主义与后现代的对立,其实都可以理解为“逻各斯”与“秘索思”对立的延伸。当这种对立出现在艺术创作中时,任意一方对另一方的绝对性压倒都会对艺术产生不利影响。当艺术中全为“逻各斯”时,艺术就成为哲学,失却了艺术特有的审美价值。如柏拉图的艺术主张,诗歌只能写神的好,不能写神的坏,音乐只能保留两种形式等。这些从政治功用出发来考察艺术的主张无疑是对艺术的压制和摧毁。至于西方当代先锋艺术,在某种程度上也有观念化、哲学化的倾向,许多艺术非阐释不能被理解,一些艺术甚至成为了纯粹观念化的产物,如杜尚的艺术品,布里洛盒子等,它们与日常现成物几乎没有差别,却进入了博物馆,追根到底还是背后的一套现成物可以作为艺术品的理论在支撑。显而易见,这样的结果便是艺术对美的背离。反之,当艺术被“秘索思”独占时,就沦为神秘主义,也失去了理解和阐释的空间,艺术将无法被解读。
无论是艺术创作还是艺术接受,“秘索思”与“逻各斯”的截然对立都将限制艺术的发展。以包容、动态的眼光看待“秘索思”与“逻各斯”,或为艺术与美的持续发展开辟更广阔空间。
参考文献
[1]陈中梅.“投杆也未迟”——论秘索思[J].外国文学评论,1998(2):13.
[2]Bruce Lincoln. Gendered Discourses: The Early History of "Mythos" and "Logos" [J]. History of Religions,1996,36(1):2,5,10.
[3]陈中梅.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409,456.
[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形而上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6.
[5]Kent F. Moors. Platos Use of Dialogue [J].The Classical World, 1978,72(2):78.
[6][古希腊]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75,102,366,391,407.
[7][法]雅克·朗西埃著,刘纪蕙等译.歧义:政治与哲学[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92-94.
[8]宋继杰.柏拉图思想中的“秘所思”“逻各斯”与“神学”——以《蒂迈欧篇》为中心[J].清华大学学报,2016(2):48-49.
[9][美]理查德·克劳特编,王大庆译.剑桥柏拉图研究指南[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399.
[10]李包靖.布鲁门贝格的诗学与解释学研究——以《神话研究》为中心[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31.
(作者介绍:李丽萍,厦门大学中文系1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美学与中西美学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