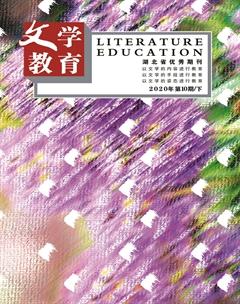神话中的人工智慧
古希腊人传说,火神和工匠之神赫淮斯托斯发明了一组奇特的三脚鼎,能在众神的宴会席间自动穿梭,为他们传送各种神酒仙馔,宴席结束,还能自动返回火神的工坊。值得庆幸,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神话实现了的时代,传菜机器人的出现已经是两年前的旧闻了,今天的任何一个凡人,都可能享受到神仙都梦寐以求的神奇技术。这是一个皆大欢喜的故事。
电影《她》(2013)是一个现代人讲的神话,故事发生在不会太遥远的2025年。离婚后的作家西奥多迷恋上了电脑上传来的女声,她虽然有一个人类的名字“萨曼莎”,实际上却是一款能陪人聊天的智能操作系统OS1。在相处过程中,西奥多和萨曼莎似乎都有了爱情的感觉,萨曼莎甚至化身在一个真的人体替身上,来体验人类的情感。但是,当西奥多发现“她”有8316位交流对象,且与641位发生了“爱情”时,这段“关系”走向了崩溃,留下一个令人惆怅无限的结尾。
技术与神话的关系历来遭人误解。实际上,这两者根本就不是泾渭分明或愚智立辨的两块。看起来,神话往往是人类关于技术的梦想和预演,但远远不止于此。要厘清其间的细节,美国学者雅筑安·梅爾(Adrienne Mayor)2018年出版的新书《天工、诸神、机械人:希腊神话与远古文明的工艺科技梦》开了个好头。可惜,作者的论述太过局限于小小的地中海沿岸,而且,作为一本歷史学著作,也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我们需要做些延伸的思考。
一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是所欲随心的,不需要任何机巧和努力,就能变幻出大千世界,这是神仙生活的诱人之处。但神话还有另外的讲法,有时候诸神也需要依靠某些技术手段,才能完成开天辟地、生物造人的伟业。盘古以斧开天,女娲抟土造人、炼五色石补天,后羿张弓射九日,嫦娥服药奔月宫,无不是依靠了某种能增强自己权能的技术和设备。
相对于神仙,Homo faber(会制作的人)更加依赖也更加自信于技术和机具。希腊神话里说,诸神在造出人类和动物之后,派普罗米修斯和弟弟埃庇米修斯去给它们分配能力,但埃庇米修斯央求哥哥让自己来完成这一工作。结果,由于他太投入,在将獠牙、利爪、双翅、硬蹄以及速度、嗅觉、眼力、伪装等各种技能悉数分配给动物后,发现没有什么留给人的了。最终,哥哥普罗米修斯从神界给人偷来天火、工艺和语言,而他自己也因此惨遭严惩。
但这则神话的语调不像是种抱憾,更像是人的自信甚至狂妄。确实如此,依赖语言和技术,赤裸虚弱的人类如今站在了地球食物链的顶端,甚至开始祸害脚下的大地。因为普罗米修斯赋予人类的工艺,不是像扇翅飞行那样功能固定的本事。但人类的本质也不只是会制作工具,而是会发明工具、梦想从未见过的工具。人类虽然没有召之即来的神力,却不断地用技术填充着需求和现实之间的缺口。如今,人类正在掌握越来越多的神力,上下入地不再是梦想,千里眼、顺风耳也已实现,全天候的卫星监控与全时段的媒介渗透甚至开始取代上帝的全能。
但是,是不是所有的技术梦想都会让人欢欣鼓舞呢?在伊阿宋夺取金羊毛的神话里,阿尔戈英雄们要面对的一个劲敌,是国王埃厄忒斯播种的龙牙变成的武士。这些包覆在青铜盔甲之下的巨人,犹如鬼魅,令人胆寒。但这支勇猛的部队却缺乏一个关键的特质,一旦开动,就只知进军、攻击,无法撤退,也不受统御。正是利用了这一弱点,伊阿宋往巨人群中投下一块巨石。机械部队误认为受到到同袍攻击,于是互相杀伐,最后内讧而亡。
这些机械士兵的根本缺陷,就是不懂得辨别敌友。可以说,这是一则关于技术失控的古老寓言,但还有比这更让人难堪的技术发明。也许对人而言,没有比永生更强烈的梦想,所以关于驻颜回春的“生物工程”是神话中的永恒主题,寻获不死之药的炼金术或炼丹术曾遍布整个古代文明。但一旦真的永生,会发生什么呢?西西弗斯使计擒获了死神,使得生物再也不会死亡。接下来,世间繁衍过度,人类也吃不到了肉食或献祭诸神,而老弱病残不得不忍受无尽的痛苦;更有甚者,因为不会有战死的危险,战争也没有了严肃和冒险精神。于是战神阿瑞斯决定放走了死神,把西西弗斯也送到死神怀中。不死带来的竟然是一个如此荒诞的结局。看来奥德修斯宁愿放弃不死之身,离开天堂般的奥杰吉厄岛和情人卡吕普斯,决意回乡与妻团聚,倒是真正的明智之举。因为,成为神仙的代价,便是失去人类因死亡才珍贵的种种牵记。正如李商隐的诗里所言,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所以,技术作为梦想,与梦魇之间的距离有时候并不远。
二
但是,人类为什么还是痴迷于技术之梦呢?就因为人的赤裸虚弱,因为人不能够依靠本能来滋养他的生存,人类生活也以此面临着永恒的缺乏保障或可靠。人类发明的种种技术手段,都旨在为生活提供了可靠的保障。但一个可靠的世界也有其代价。
哲学家海德格尔把物的本质视作“用具”,以至于创造了许多拗口的用法,比如鞋具、住具。而且在他看来,人的生活就处在一个无远弗界的用具关联之中,世界几乎就是一个由用具组成的链环。这是一个用来保障生存的世界,一个作坊般的世界图像。不过,连他本人后来都发现了,这样一个世界并不美妙。如果手头眼前都是人之造物,都是用具,即使人能以之完成巧夺天工的作品,供人使唤和享用,这样的世界也缺乏某些深长的意味与诱人之处。
很不幸,我们今天的都市已经是一个这样的世界图像。城市是人类追求保障性的极致,城市中的每一事物,都是有用的“用具”,于是,城市变成了一家大工厂,甚至一架大机器。“配套成熟”的城市生活确实实现了某种天堂般的保障:便捷的交通,储备充足的超市,二十四小时的热水的家,恒温的工作间,以及保障城市运作的环卫、消防、医疗、教育、心理诊所、殡葬。但是,正是在这样一个城市,发达的技术提供的不仅是保障,还有更深的障碍。因为,现代的技术仿佛正在获得自己的意志,不再与我们的需求相关——就像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手机或电脑的系统要定时地“更新”一样。而且,在这样工场世界,人并不像看管机器的主人,人的存在倒像是为了保障机器的正常运转。人自身、人的需求也正在变成这个机器的一部分,在空调、西瓜、wifi的包裹之中,人体其实也像一架机器那样在正常运行。而这种生活,并不像神话中的天堂。这不是说,汽车尾气、垃圾污染这些尚未解决的问题,让城市不像天堂;而是说,运转正常的城市、彻底解决了这些遗留问题的城市,会越发缺乏天堂的某种意味。因为天堂,在保障和技术之外。
实际上,技术梦确实并不是人类唯一的梦想,对技术、机具的恐惧与逃避历来是一个强劲的文化母题。庄子就讲过一个故事,说子贡路过汉阴的时候,看见一位浇地的老人,方法落后。他先开凿一条通往井底的坡道,再抱着罐子从井里取水,来回往复,费力无功。子贡告诉他,现在有种设备叫桔槔,一天就能浇一百畦。没想到老人教训说,我岂不知道有这东西,不过,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这样下去,最终会失去让人失去“道”,所以我不用它。庄子所谓的道是什么呢?
三
《列子》里面讲过一个类似的故事。海边有个人喜欢鸥鸟,每天早上到海边去,与他一起嬉戏的海鸥有上百只。他父亲说,我听说海鸥喜欢和你玩,你抓一只来,我也玩玩。第二天这人来到海边,海鸥都在空中盘旋,再也不飞下来了。这个鸥鹭忘机的故事在文人传统中影响深远,却并不是什么高雅之士才能达到的境界,而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种基本情态。用哲学家列维纳斯的话说,这就是人类在直接的生活享受中感受的那种无知无识的幸福。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在这些直接的享受中,世界神秘地与我到来,与我相会,但我既没对它的任何认识,也没有将它作为物来占有。正如海德格尔后来也指出的,这是比异化了的技术态度更基本的一种态度,就是让开满鲜花的树站在其站立处,人在自由的、任其所是的目光中观物——他称之为“泰然任之”。
这才是神话和天堂所呈现的那种无尽意味与诱人之处。细究创世纪的开头,上帝的功绩其实并不是发明,而只是发现,所以说“神看光是好的”,这就是一种邂逅幸福之时的肯定。这种“恰好”的幸福,这种无知无惧地沉醉在直接的享受之中,也正是伊甸园的本质。而某种意义上,我们也从未失去伊甸园。因为在那些“诗意”的时刻,比如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时刻,不去探究气团与洋流的运动,更不试图掌握风云的变幻,这就是人的神话时刻。
当然,这里有对自然的利用和享受,却没有占有的机心。与世界邂逅,又不干扰世界的神秘不测,这是神话式的态度。所以,中国古代的神仙,更善于驯养灵物,而不是发明自动机械。无论白鹿、黄鹤还是黑虎、青牛,都不是自动机械,而是仍然保持了其神秘不测的生灵。无疑,这样的世界可能缺少保障,却未丧失神秘。实际上,不可靠的世界才保有无限的神秘。说神话是用想象征服自然,说自然被支配后神话就消失了,这是现代人的傲慢和蒙昧。在谷物下种之前祈祷,在瓷器烧制之时祭祀,酿造要等到七七四十九日,所有这些“迷信”建立在技术不可靠的背景中,但也因此唤起了一个充满神秘的世界。而一个可靠到不需要神的世界,其实更加不宜居。
所以,毫不奇怪,在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神秘主义又重新兴起。都市人纷纷逃向自然、田园,逃向最后的“净土”,市民开始青睐长满虫眼的有机蔬菜和前工业时代的产品,政府也四处建设自然保护区、绿地公园。这正是试图保留自然的神秘和生存的诗意的努力。无论这些举措在目前是多么于事无补,对于恢复世界的神秘、对于召唤出一种非异化的生存而言,绝对不可或缺。
四
技术并非人类的唯一梦想。技术之梦与天堂之梦,控制之梦与泰然任之处于一种永恒的矛盾之中,而制造机器人的梦想把这一矛盾推到了一个极点。“制造”一个和自己一样的生命,这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对于一个能自然繁殖后代的物种,这实在是一个难以理喻的梦想。
某种意义上,机器人的梦想是可靠之梦的一部分,获得一个越来越得心应手的用具,始终是技术梦想的目标,今天的人工智能技术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实现着这一梦想。但是,即使人的需求多么变幻无定,我们也只需制造出能更精准地领会我的意图、更高效地完成我所不能的作业的机器,而并不需要一个像我一样的机器。一个越来越“听话”的機器,它不好吗?
是的,还不够好。一个只会“听话”的智能同样缺乏某些魅力,一个能让我随心所欲的机器也缺乏吸引力。正如列维纳斯发现的,人身上有一种无法止息的“欲望”,一种对他人的欲望。这种欲望不是我要控制这个他人,却是被他所控;不是要他听话,而是我听他的话,我们互相说话,互相倾听。这恐怕才是隐藏在人工智能梦想中的最深的梦想。因为普罗米修斯不仅为人类偷来了火和工艺,还有语言。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一个大地万物都会开口说话的世界,是人类童年最初的梦想;而一个能陪伴我聊天的机器人,是这个梦想的成年变体、“变态”。
所以,在人工智能背后,仍然有更深的失控之梦,有控制之梦和失控之梦的缠斗的极限。而现时代对于人工智能的热情,仍主要停留在控制之梦中。人工智能仍然是作为某种更高级的机器,作为控制自然和他人的机器而出现的。对它的忧惧,同样如此。那些最常见的追问,比如机器人会不会伤害人类、奴役人类,同样是一种建立在试图控制他人的“小人之心”上。如果,有一天真制造出了一种生灵,具备了我们的本质——虽然我们都不那么清楚自己的本质——有了需求,有了死亡,有了情欲,有了“欲望”,他们更可能像我们一样陷入同样的迷茫。幸好,这样的生灵并不会很快到来。与其忧心那遥远的、可能奴役我们的智能生命,倒不如忧心已经制造出来,用于奴役同类的智能机器。因为,今天人对同类的奴役和伤害,远甚于尚不存在的机器人。这仍然是一个要自然“听话”、要他人“听话”,却没有学会倾听的时代。
技术是现代人根深蒂固的迷信,与此相应,那些关于技术梦想的古老神话,也被视为发达技术的预演。实际上,相对于一根筋的技术梦想——这一梦想的极限就是人工智能——神话提供了更为丰富和深刻的智慧,警戒着技术一意孤行的“进步”冲动。
胥志强,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