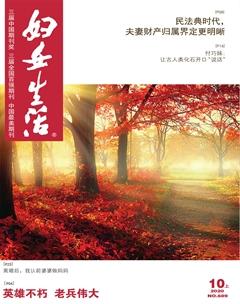科学家也可以是懂生活情趣的时尚女性
一润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科研人员尤其是科学家,都是刻板、教条、固执、不修边幅、不顾生活的。而我,希望破除外界对科学家的这种偏见——
从汽车修配厂的翻砂工半路出家进入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做科研
笔者:能谈谈您是怎么从事科研工作的吗?
阎锡蕴(以下简称阎):我1958年生于河南开封,进入基础生物学领域完全是半路出家。16岁那年,我到河南一家汽车配件厂当翻砂工,干的是很多人难以承受的重体力活。因吃苦耐劳,我年年获得“劳模”称号,短短4年就升为三级工。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入河南医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中日友好医院工作。为了提高我的科研能力,单位派我到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实习。在那里,我遇到了时任所长贝时璋,人生从此改变。起初,我对理论完全不在行,只好从消毒、准备器械这些与医学沾点边的事情干起。不久,实验室一位老师生病休假,贝时璋提议:“能不能让阎锡蕴接棒?”就这样,我战战兢兢地接下了这个任务。为了不把实验做砸,我在老师们的鼓励下,埋头工作,有不懂的就向他们讨教。最终,实验达到了预期目标,我和老师们都很高兴。
笔者:那后来是贝老劝您留在所里做研究的?
閻:是的。就是那一次做实验,让我发现做科研很有趣。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我对那次实验仍记忆犹新。我在生物物理所的实习期是一年,期满后我对留在所里做研究还是回到医院当医生犹豫不决。最终让我决定改行做科研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贝老对我说的一番话:“我看你是块搞科研的料儿。你年龄还小,专业知识可以去补,况且医学对生物物理研究也有帮助……”事实证明,我日后在科研上的几次突破,都得益于医学与生物物理学的交叉优势。
笔者:留在生物物理所后,为强化专业知识,您下过不少功夫吧?
阎:留所后,我从基础理论学起,从最简单的实验做起。后来,我先到北京大学进修,学了一年高级生化课程,又前往日本名古屋大学深造,学习分子生物学。与此同时,在生物物理所前辈的悉心指导下,我又系统地学习了细胞生物学。1989年,在贝老的实验室中工作6年之后,我被公派赴德国海德堡大学、德国马普细胞生物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也算是出国留学吧。那时我女儿刚刚2岁,我在国外很想她,再加上语言不通和学术上的巨大差距,我经常难受得想哭。
科学设想被证实当然好,可有时实验结果出乎意料,也会带来意外发现,纳米酶的发现就是这样一个意外
笔者:您是纳米酶的发现者,能说说发现的经过吗?
阎:纳米酶是我和团队深耕10多年的新领域。对我而言,探索未知尽管困难重重,但有一种神奇的魅力,特别是当你的科学设想被证实的时候,那种窥破自然奥秘的喜悦感真的太好了;即使有时候实验结果出乎意料,也会带来意外发现,那种喜悦更加难以言说。纳米酶的发现就是这样一个意外。当年,我带领团队发现了一个肿瘤新靶点,在探索肿瘤诊断新方法时,遇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磁纳米粒子竟然与过氧化物酶底物发生了反应。起初,我们认为这可能是某种污染所致。可经过多次重复实验,这种情况仍然无法避免。当时,我大胆设想:难道这个惰性的氧化铁具有过氧化物酶的催化活性?随后,我与团队用一系列严谨的实验证明了这个假说,接着将成果发表在《自然纳米技术》上。很快,此文在全球业内引起轰动,英国皇家化学会刊发表综述,认为这是酶学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在此之前,没人相信,作为惰性物质的无机纳米材料会发生和酶一样的反应。而这一项发现,可以说颠覆了科学界传统意义上对“无机”与“有机”的认识。
笔者:“纳米酶”到底是什么?有什么用呢?
阎:纳米酶是一种既有纳米材料的独特性能又有催化功能的模拟酶,具有催化效率高、稳定、经济和可规模化制备的特点。我当时作为纳米酶的发现者,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原始论文自2007年发表后已被引用1800余次,成为开拓纳米酶研究新领域的奠基之作。在发现纳米酶后,我和团队成员并没有发完文章就了事,而是将纳米酶引入肿瘤生物学研究,将其用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效果惊人。我还绞尽脑汁建立了纳米酶活性检测的标准体系,使纳米酶应用研究标准化、可质控、可量化。目前,已有超过100种不同纳米酶相继被发现,纳米酶研究已在30多个国家的300多个实验室开展,在生物、医学、农业、环境治理等多个领域展现出可喜的应用前景。不久的将来,纳米酶将会为人类健康、能源再生及环境保护等做出更多贡献。国际专家普遍认为,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中国纳米酶研究引领全球。
笔者:您取得了如此卓越的成就,肯定获得了不少荣誉吧?
阎:是的。我在生物物理学领域已探索了30多年,成就颇丰,也收获了很多荣誉:2012年,纳米酶研究入选年度中国十大科学进展。2015年,纳米酶的应用研究获Atlas国际奖,同年我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接着,亚洲生物物理联盟换届,我有幸被推选为亚洲生物物理联盟主席,成为该组织有史以来首位女主席。2017年,我获得首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还相继当选全国第十二届、第十三届政协委员。2019年,我荣膺“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称号……其实,我是生活在了一个好时代,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得到了国家如此多的荣誉。以后,我唯有更加努力,才能不辜负这些荣誉。
工作和生活从来都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女性科学家既可以很优秀,也可以很优雅
笔者:听说您跳起舞来很疯,可一旦工作起来,认真得让学生们都感到有些可怕,是这样吗?
阎:确实是这样。在生物物理所的新年联欢会上,我们实验室的保留节目是欢乐群舞。身为主任的我每次都不落下,无论是《江南style》《小苹果》,还是《燃烧我的卡路里》,我都跳得激情四射,丝毫不输年轻人。学生们都说:“阎老师跳起舞来很疯!”可回到工作中,我的认真却让学生们有些害怕。平时开组会,从图表的展示方式到单位的大小写,我都严格按照发表文章的标准要求学生。学生的毕业论文,修改十几遍是常事,多的甚至达到20遍。有一位博士生很努力,但4年间换了5个课题仍一无所获。有人劝我降低一下标准,我总是摇头:博士的标准不能降低。只有严格要求,才是真正对学生负责,这是贝老留给我的优良学风。至今我仍然感激贝老当年对我的指引,也一直保持着他所塑造的研究所的学术基调。由于我严格要求,我的学生在国内外科技界频频获得各种学术奖项。
笔者:您常说当科学家并不意味着要放弃生活中的美好,是这样吗?
阎:不错。人人都爱美,当科学家并不意味着要放弃生活中的美好。我过去不注重服饰,对生活也比较马虎。2003年,我参加一次全国女科学家大会,看到不少同行不仅工作出色,而且着装得体,光彩照人,我眼睛为之一亮,才意识到,原来女科学家也能如此美丽。从那以后,我开始认真打理自己。有一次,一个著名媒体人采访我,说我“一丝不乱的浅褐色短发,合体的中式服装,精致的耳坠,淡淡的妆容,举止优雅,年近六旬与常人想象中的女科学家有些不同”,我很高兴。
说到这里我非常感谢我的爱人和女儿,他们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爱人经常夸我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女科学家,还是一位贤惠、懂得生活情趣的时尚女性。每当换季时,我都会挤出时间和爱人、女儿一起逛商场挑衣服。在男装柜台,我和女儿争着替爱人挑选衣服;在女装柜台,爱人又会忙着为我和女儿挑选服装。搭配服饰也成了我们一家三口的幸福时光。我时常感慨:“工作和生活从来都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女性科学家既可以很优秀,也可以很优雅。”為更好地平衡工作和生活,我还专门在中科院组织了“女性与生物物理之美”系列讲座,为女科技工作者营造家一样的互助氛围,让大家共同出彩。
笔者:都说您是一位“三热爱”科学家,能具体说说吗?
阎:在我的办公室里,奖状、奖杯数不胜数,但我觉得,中科院“五好家庭”纪念杯和全国妇联颁发的“最美家庭”奖杯,才是最珍贵的。爱科学、爱生活、爱美丽,是我心中的“三热爱”。在中国,人们一直认为,科研人员尤其是科学家,都是刻板、教条、固执、呆板、不修边幅、不顾生活的。我希望破除外界对科学家的这种偏见。所以,在公众面前,我着淡妆,戴耳饰,妆容得体,身姿优雅。我喜欢明亮的服饰,说话直爽,感染力十足;我还会和学生一起跳舞,为爱人做生日蛋糕……在学生眼中,我爱美丽、有智慧又懂生活情趣。其实,我也想告诉他们,搞科研固然有枯燥、艰辛的一面,但不要忘记,科学研究也是快乐的旅程,是一项有趣的工作。像大多数科研人员一样,我也非常忙。为此,我练就了一套高效的时间管理法。在家中,我双手很少闲着,看到家务顺手就做了;没时间去健身,我就见缝插针,在灶台旁、办公室,用自创的健身操放松身心、锻炼身体……下厨烹饪,甚至扫地、擦桌子在我看来都是健身。我还有让家务活变得有趣的小窍门——创造性劳动。比如切西瓜,我把它切成西瓜船,这样干起来有趣,看起来赏心悦目,吃起来也感觉更爽口。
2019年6月9日和9月17日,我应邀赴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演讲,一些老教授看到我都很惊讶:“阎老师,你也六十多岁的人了,怎么保养得这么好?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呀!作为一名科研人员,真难得!”我说我平时虽然忙,可对生活还是蛮讲究的。咱搞科研、做学问的也要讲生活情趣,追求生活品位。老教授们听了频频点头。我以《在科学中寻找人生意蕴》为题,围绕从零开始、把每一件小事做到极致、探索科学奥秘、做“三热爱”科学家等,讲述了自己的工作体验、科研经历和人生感悟,台下数千名师生不停地鼓掌……
〔编辑:潘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