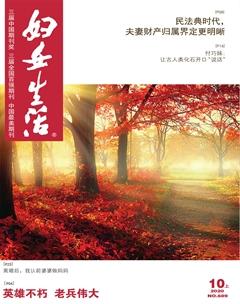付巧妹:让古人类化石开口“说话”
欣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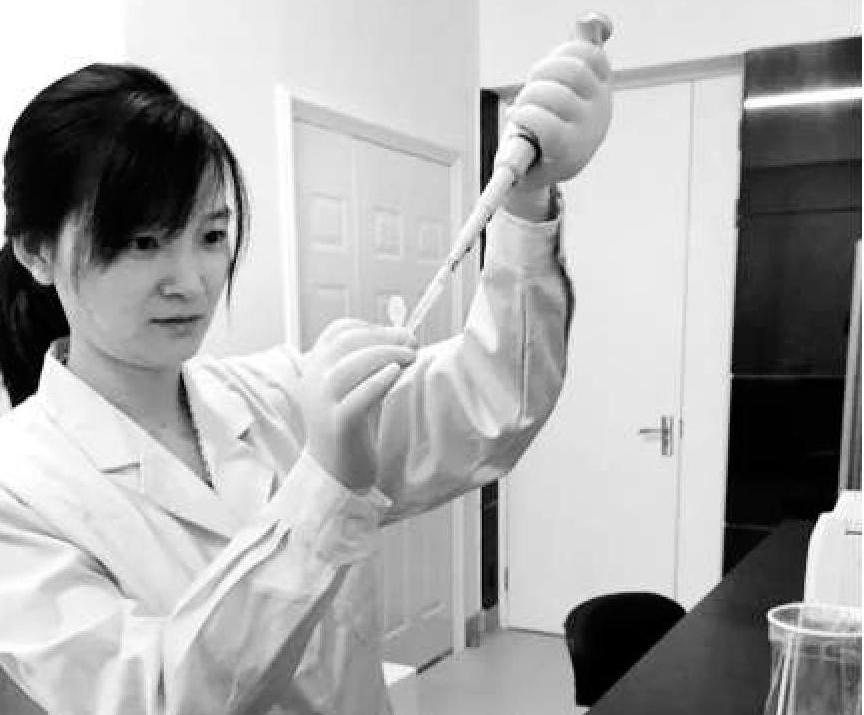
身为“80后”科学家,付巧妹利用古DNA捕获技术,翔实地绘制出冰河时代欧洲人群的遗传图谱,首次揭示了该时期欧亚地区完整的人群动态变化情况,让欧洲的有关专家为之震动。2016年,她被英国《自然》杂志评为中国十大科学之星之一,同年获得中科院青年科学家奖。近日,她又入选2020年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
“最年轻”的科学家讲一个最古老的研究课题
2020年9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80后”科学家付巧妹在会上与总书记进行对话,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以下是付巧妹与总书记对话的部分内容。
付巧妹说:“我的工作是围绕人类古基因组学,从事演化遗传的研究,也就是通过古DNA探究‘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
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地问道:“从哪里来,你们搞明白了吗?”
“在努力搞明白!”付巧妹向总书记汇报了这些年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经常有人问,‘你的研究有什么用。我曾在很难维持实验室的时候,也想过要不要去做热门研究。希望国家进一步引导不以‘有没有用评价和发展基础研究……”
总书记听了以后深有感触:“对冷门怎么看?按一般概念,一些冷门的东西没有用。这种认识可能把一个领域的事业耽搁了。做科研事业的评估,要有长远的眼光、世界的眼光、科学的眼光。”
——摘自《人民日报》2020年9月13日一版头条
两次“放弃”只因有梦想,确定研究方向义无反顾到国外读博士
笔者:能讲一下您从小的生长环境吗?
付巧妹(以下简称付):我出生在江西农村,小时候和很多乡下孩子一样贪玩,是乡亲们眼中的野丫头。正是少年的天性释放,让我潜移默化中喜欢上了生物。上小学时,因为作业不规范,我经常被老师批评。上初中后,我的性格收敛了很多,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那时,成绩好的学生可以读师范,师范毕业就可以当老师拿工资。再加上我父亲是教师,于是,我报考了师范。
笔者:您放弃当教师备战高考,阻力大吗?
付:读师范后,很多人的上进给了我触动。师范生当时不学英语,但我身边好学的同学就躲在卫生间里学英语,说是为高考做准备。我们班主任就通过自学考取了心理学博士学位。受他們的鼓舞,在师范毕业前的两个月,我决定放弃当教师,向父母提出参加高考读大学的想法。母亲对我的想法表示支持,父亲虽有顾虑,但没有阻止。我也做好了考不上回家种地的最坏打算。
笔者:您读两年高中就考上了大学,为何又放弃了保研的机会?
付:师范毕业前两个月,离高一下学期结束时间很短了,我便直接从高一下学期开始学习。后来,我考取了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学习过程中,我发现这并非是一门纯粹的考古专业,以化学为主,数学、物理、计算机等课程都在修读范围内。大学毕业前夕,学校给了我保研机会,但我对生物研究情有独钟。于是,我放弃了保研,加入考研大军,考取了中国科学院的硕士研究生,从事骨骼研究,通过骨骼的化学元素了解早期人类的食谱。
笔者:您到德国攻读博士学位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付:我在中科院研究的是早期人类的饮食,但我对人类的演化进程非常感兴趣。人类的起源与归宿,既藏着族群生命本质的奥秘,也隐含着个体的自我意识与选择。追踪古人类的演化历史,最有效的方式是获取他们的古DNA。科学家获得古DNA,一般需要从几千年到几万年前甚至几十万年前的骨骼化石中提取。在古DNA研究方面,德国马克斯·普朗克进化人类学研究所是无数DNA研究者心中的学术圣地。斯文特·帕玻教授是古DNA研究领域的泰斗,他在学生时代就偷偷克隆了千年木乃伊的古DNA。我幸运地申请到了在帕玻教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的资格。
为了考核过关,苦学一年瘦了10公斤,用不厌其烦的求证精神赢得导师赞赏
笔者:在大师手下深造压力很大吧?
付:和国内不同,我攻读德国马克斯研究所的博士更像是工作,前半年是试用期,每年都有考核。自从进入研究所,我每天都在苦学,生怕考核不过关被赶回国。与读高中第一年一样,我到德国一年内体重降了10公斤。我在国内学习了文物保护学和体质人类学,但从未接触过古DNA或基因组方面的研究。刚到研究所参加讨论会时,团队成员讨论尼安德特人基因组序列草图,我像听天书一样。为了尽快赶上,我疯狂地阅读文献,实在消化不了就主动求教。怕频繁求教打扰别人,我就把一个星期的问题攒起来,集中请教,一问就是几十个问题。到研究所的第四个月,因为我学习能力强,而且能自主互动,被所里批准正式攻读博士。
笔者:您参与开发出古DNA捕获技术,对于研究古人类进化史起到了关键作用。那么什么是古DNA捕获技术?
付:所谓古DNA捕获技术,就是将现代人的DNA做成一个吸铁石般的引子,突破古人类DNA被环境严重污染、利用率不高的困境,将仅占0.03%的人类DNA从含有大量土壤细菌DNA的杂质中吸附、富集并“钓取”出来,使得大规模开展古人类全基因组研究成为可能。借助古DNA捕获技术,我第一次准确推算出现代人与尼安德特人发生基因交流的时间,成功为一个4万年前的“现代人”寻亲。依靠从该现代人下颔骨中获取的微量古DNA信息,我判定这个现代人的曾曾曾祖辈之一就是已灭绝的尼安德特古人类。紧接着,我从一块4.5万年前的早期现代人化石中获得基因组序列,发现人类迁徙时走出非洲的路线并非只有单一南线,而是存在着“北线蹊径”等多种路线的可能。随后,我绘制出翔实的冰河时代欧洲人群的遗传图谱,被业内人士评价为“重写了欧洲最早的现代人类历史”,在欧洲古人类DNA研究领域引起震动。
笔者:您的推断都是建立在试验之上,有很多试验让您难忘吧?
付:每次试验,让我最珍惜的是做试验的材料。要知道,化石形成是件很困难的事。据统计,大概每10亿根骨头,才能有1根变成化石,这些化石对推测史前故事弥足珍贵。数万年前人的一小撮骨粉,可能就藏着人类迁徙、人群演化与人类文明的历史秘密。2010年,我参与的国际团队就根据古人类的一根小手指的少量骨粉,发现了未知古人类丹尼索瓦人对大洋洲以及东亚人群的一些遗传影响。因为用来试验的材料宝贵,失败后再来一次是不能承受的后果,因此,每次做试验的过程都堪称经典。有一次我做完试验,已经凌晨2点了。回到家躺到床上,我脑子里习惯性地闪回实验进程,复盘到关键处,有一个细节好像有问题。我一个激灵从床上坐起来:刚才是怎么做的?对结果有没有影响?有什么影响?直到确认准确无误,我才安心入睡。
笔者:导师帕玻称您是他最出色的学生之一,您是如何赢得他的认可的?
付:导师欣赏我在研究方面的主动性,以及迎难而上的挑战精神。2012年,研究所拿到一块4.5万年前的人类腿骨化石,尚未确定如何研究时,我就提出了对这块化石的研究方向,做估算、列计划,给出解决方案。导师对我的方案比较认可,指定我担任此项目的负责人。在此之前,几乎没有学生在重大项目上挑大梁。在研究所,平时在某些节点有难度的试验,也只有我能做成。2015年,我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了题为《一名拥有近代尼安德特人祖先的罗马尼亚早期现代人》的研究文章。此文更新了以往学界认为的尼安德特人在5万年前和现代人有基因交流的观点,将发现现代人与尼安德特人基因交流的时间往回拉了近1万年。当时,帕玻教授也质疑是不是搞错了。为此,我增加数据量,调整实验方式,几个月的验证后,我给出的回答是:“绝对没问题!”帕玻教授对我不厌其烦的求证精神很是赞赏。
回国效力组建高水平团队,用认真的工作态度为年轻人做表率
笔者:您在德国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为什么又回到国内呢?
付:我对中国和东亚发生过什么很好奇,再说我也想把所学知识回报祖国。回国后,我组建了自己的团队,把研究转向最早定居亚洲的智人,我也想研究近至数千年前的亚洲历史。我国大量古人类骨骼没有做过DNA研究,我希望能对亚洲先民的历史进程重新书写。中国拥有众多史前人类的遗骸和遗迹,且中国许多地区也发掘有大量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的人类遗存,这些都为我们开展相关古DNA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资源。在古DNA研究领域,世界正在看中国。如何保持领跑优势,是我和团队的责任与担当。下一步,我和团队将对亚洲人类族谱进行研究,或许我们将再次改写人类的历史。
笔者:研究古DNA,对现代人有哪些帮助?
付:很多人问过我类似的问题,可能大家都认为这样的研究不能直接带来经济效益。其实,基础科学研究很难在研究起步阶段就说清楚对于后世的作用,但我们看到很多例子是有影响的。比如,我们东亚人相对欧洲人更容易患上Ⅱ型糖尿病。我们通过研究古DNA,发现尼安德特人对东亚人有更多影响,这里面就存在着较大的联系。再比如,去年有个团队研究鹿科动物,提取了一些鹿角再生的分子,这是否会对我们人类研究再生和衰老有所帮助?这些遗传演化领域的疑问,有待我们逐层深入去研究,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笔者:平时您是如何激励团队年轻人的?
付:我们古脊椎研究所有一句所训:做老实人,探前沿事。我认为这是青年科研人员应该秉持的科研态度。年轻人做科研,尤其是在古DNA这种不能快速出成果、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科研领域,我会告诉他们要沉得住气,甘于坐冷板凳,不急功近利。经典的研究、突破性的成果,总是由扎扎实实钻研、积淀而来的。此外,我要求年轻同事在科研领域要拓宽视野,不自我设限。科研探索是一个不断挑战旧知、迎接新知的过程,尤其对于自然科学研究,要敢于创新和迎接挑战。
〔编輯: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