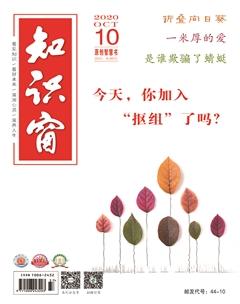让球不停向前滚动
魏子剑
我最早和小伙伴竞技球,是儿时趴在地上玩实心玻璃球。那是梦幻般的童年滚动的五彩星体,是可以把世界折射成希冀的魔镜。稚嫩的身躯在侏儒式的精灵面前变得如拉伯雷笔下的巨人一样高大,微缩的胜利和失败,流动着喜悦或悲伤的金沙。于是,我便以为随意构造的游戏场地就是整个世界的脸庞,而自己则是主宰它欢笑或哭泣的中枢。可事实上,我那时还不懂世界——满裤兜的五颜六色只是生活的偶然,所厌弃的黑白单调才是布满生命的脉络。
不知不觉中人就长大了,球也随之放大了些许。正规的小学校园里分布着不怎么正规的乒乓球桌,那是课余的幸福所在。球的颜色单调了许多,不再有透穿刺眼的阳光。虚弱的内心因手中拥有武器而暂时筑起堤坝,依旧不变的是那份没有根据的美妙自信——球总会弹起来的。
初中时,球真的弹起来了,并且由于手掌变大,个头向上蹿,我的兴趣便逐渐转到了篮球之国。NBA侵入我的大脑早于ABC,记灌篮高手绝对比背英文单词轻松容易得多。这时,我的人生目标单一得就像纯净的滇池,理想的终点站是大学,正如篮球场最终的目的地是把球投入篮筐。九年义务教育加上三年高中,只是从后场把球运到前场,偶尔的高分或许相当于几次绝妙的过人或传球。篮球场在自己眼中很小,几个大步就过了中界,敌人也不多,五个而已,只要控制好手臂、手腕和指掌,用眼睛有意識地瞄准目标,无意识地投篮,总会投出好球。
年轻的激情所能理解的仅限于“前进”一词,球不能回场,否则就犯规了。于是,我想方设法向前、突破,并且认为最后总会进球的,我不可能失败。可是,然后呢?球进了之后呢?进了大学之后呢?我没有想过真空里的幸福背面还画着什么图案,也忘记了思考下一个球该怎么打!
我成为大学生了。篮球不知不觉渐渐远去,或许是头脑清醒了几分,不会踢足球的人无缘无故地喜欢坐在屏幕前表达悲喜。沉淀思绪后我才明白,也许人生的抽象体更贴近一场足球比赛吧!
谁能琢磨得透生命的长短呢?或许长寿到非得打满加时赛用点球抹下无望的眼睑,或许被一个金球突然宣判了死刑。谁又能绝对地为成功这个“胎儿”把脉呢?拼搏、流汗,甚至流血了,可结果并不一定是非零的。
同样需要勇敢,需要攻过半场,突破禁区的比赛,或许足球更能让人成熟地意识到,适当的回场传球,就像缩回来的拳头,再打出去更能伤人要害,仅仅有猛不可挡的激情是不够的。
后来,人生不再像用手投篮那么简单,此时我才感觉到手的无力,在足球运动里,手只能作为附加的防范武器。长时间的倒脚、时时刻刻的准备、极少的良机,必须靠脚和头的配合才能成功。这时,我才明白人生的艰辛只会越来越多。
生活的方式绝对多于足球场上进攻的路线或踢球的风格,目标不会是球门大小所能包容的,我们遇到的对手也不会只是十一人……足球场或许只是一个变形的舞台,台上歌舞风格独特,就能吸人眼球。我们都是演员,当然也需要观众和掌声。但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呢?是进球后的赞扬、掌声、金钱和诱人的荣誉吗?我更愿意把那兴奋的狂奔理解为创造者的喜悦。
让球不停地向前滚动,不断创造出美妙、深刻的弧线,或许这就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