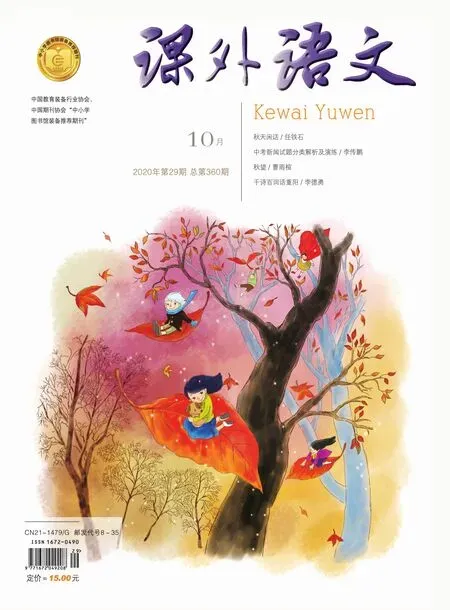千诗百词话重阳
⊙李德勇(江苏省连云港市岗埠电视台)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从王维这首脍炙人口的重阳诗《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可以看出,重阳节这一天在唐代是非常受重视的,而且人们有登高、插茱萸的习俗。而通过众多古代文人骚客的诗词,也可看出重阳节在古代的盛况和重要性。
重阳节登高插茱萸
重九起源甚早,旧以阴历九月初九日为重九,南朝梁王筠诗:“重九唯嘉节,抱一应无贞。”又古以九为阳数,故又称重阳。魏文帝《九日与钟繇书》:“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故曰重阳。”而重九登高,最早见《续齐谐记》:“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长房谓之曰:‘九月九日汝家当有大灾厄,急令家人缝囊盛茱萸,系臂上登山,饮菊花酒,此祸可消。’景如其言,举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这段记述,虽近乎神话,但在那水旱的古代,居民有登高避灾之举,自亦颇合情理。
其时道家势力遍及民间,曾倡议:“茱萸为辟邪翁,菊花为延寿客,假此二物,以免阳九之厄。”(见道家古书所载)由是俗尚所趋,历代相沿。
唯考诸古人登高行事,不独九月九日为然。据《荆楚岁时记》云:“正月七日登高赋诗。”《陔余丛考》亦云:“昌黎集有人日城南登高。”于此可知,人日与上元日皆有登高之举,不过,习俗相循,仍以重九登高,为人所重视,至今不废。

登高远眺吟九日
登高原为寻乐,当秋高气爽,登高远眺,逸兴飞,才不辜负佳节。因之,古来文人雅士,每于登高之时,吟咏志盛,迄今留下许多佳句,传诵不衰。如钱起:“浮云瞑鸟飞将尽,始达青山新月前。”张继:“万迭银山寒浪起,一行斜字早鸿来。”唐彦谦:“云静南山紫翠浮,凭陵绝顶望悠悠。”朱湾:“水将天一色,云与我无心。”以上诗句,皆是重九登高时乘兴吟咏的,真情实景,描绘得淋漓尽致,及今读之,犹令人遐思弗已!
历代的重九诗文,经文人学者一致认为:文以魏文帝《与钟繇九日送菊花书》为最早;赋以宋传亮《九月九日登凌器馆》为最早;诗以陶渊明《九月闲居》及《己酉岁九月九日》诗为最早。陶渊明在诗文上,处处显示向往自然,如《归园田居》:“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以及《归去来辞序》:“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从此开启了田园派的诗歌,并被人称为“隐逸诗人之宗”的诗,为唐代表文字。
陶渊明之后,南北朝的重九诗,竟一反陶的风格,如谢灵运、谢瞻、萧子良、王俭、梁简文帝、沈约、丘迟、任昉、庾肩吾、何逊、刘孝威、王修已等,几乎等于同一版本,皆属侍宴应制之作。直至江总《于长安归还扬州九月九日行薇山亭赋韵》一诗,方才打破了侍宴应制的格调。江诗云:“心逐南云逝,形随北雁来。故乡篱下菊,今日几花开?”

登高赏菊酒重阳
重九登高、赏菊、饮酒,原属应节雅事,尤其是古今诗人,每每一手握笔,一手执壶,总是离不开酒,何况值此重阳,没有名酿,如何度此佳节?
唐代重九登高,颇为盛行,连皇家也登高赋诗饮酒。唐中宗《九月九日幸临渭亭登高》诗,句云:“九日正乘秋,三杯兴已周。”其兴致之沈,可以想见。而杜牧描述重阳醉酒诗《九日齐山登高》云:“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违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晕。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还有诗云:“重阳酒百缸。”所谓“酒百缸”,或为诗人笔下夸张之辞,但诗人在重阳佳节,乘兴不停地饮酒,醉醒后再饮,其酒量亦足惊人了。
杜甫《九日》诗云:“重阳独酌林中酒,抱病起登江上台。”另有句云:“旧日重阳日,传杯不放杯。”老杜抱病时,还要登高独酌,那无病时,自然就要任情醉酒了。至于饮酒饮到醉醺醺地连归途都辨认不清的也大有其人,诗人张谔就是其中之一,他的《九日郊游》诗云:“秋天林下不知森,一种清游事已均。绛叶从朝飞着夜,黄花开日未成旬。城远登高能几日?茱萸凡作几年新。”
满城风雨近重阳
重阳,古有小重阳与展重阳之称。因以重阳遇雨,无法登高,如不举行,未免扫兴,于是,延至翌日补行登高,故称小重阳。倘使遇到连日风雨,未能成行,便乃延一星期或十日,至九月十五日或十九日补行登高,俗谓展重阳。
然而也有兴趣特浓,冒雨登高,即景抒怀的,如潘大临传诵千古的独句诗“满城风雨近重阳”。潘大临闲卧休息,忽闻枫林风雨之声,一时诗兴大发,正握笔题咏间,突被催租人骚扰,打断诗兴,只得此一句。徐泫《九日雨中》:“目极暂登台上望,心遥长向梦中归。”他乡作客,心系故里,大有“一杯今日酒,万里故乡亲”的感慨!唐代女诗人薛涛《九日遇雨》诗又云:“万里惊飙朔气深,江城萧索昼阴阴。谁怜不得发山去,可惜寒花色似金。”亦可谓深谙雨中登高的情趣。
——徐诗云素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