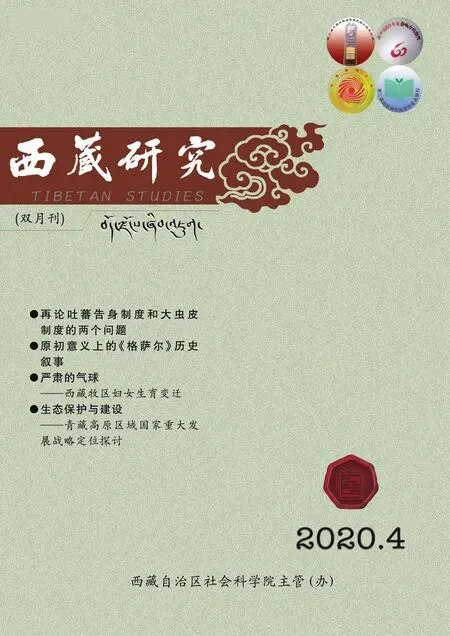20世纪以来中国西南仪式音乐研究述评:兼论音乐西南学构建
杨 扬
(太原师范学院音乐系,山西 太原 030619)
一、引言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推进,尤其是海上丝路的建设,中国西南地区日渐成为国内学界所关注的热点,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等学科都极为注重对中国西南地区的研究。中国西南地区自古以来是诸民族、各种文明汇集的地带,文化、历史等问题较为复杂。对于西南地区全面深入的了解与分析,不仅需要较为前沿的学科方法,还需要大量的民族志与相关资料的收集,从这一点上来看,虽然当前学界已对此进行了一定的整理、收集与研究,但西南地区民族文化复杂的情况仍然需要大力挖掘与整理相关民族志个案与资料。
从历史上看,中国西南地区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这源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不断的相互接触与交往,尤其是隋唐时期的吐蕃,通过与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使得中原地区不断地定义其西南边缘以及西南族群的概念,从而使西南地区的地理范围不断变化。由此可知,西南是一个相对的空间概念,其包含文化区域与地理区域两层意义。从地理区域来说,西南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西南,系指自司马迁《史记》以来的一种观点,即“西南巴蜀外”的滇、黔两省以及川西南的一部分;广义的西南则将历史概念与地理概念结合起来,是一个以今天的川、滇、黔三省为主体的,其外延到广西、西藏甚至湘鄂西部的地理区域[1]29,而本文对于中国西南仪式音乐的梳理,主要依据当前学界所关注的对象以及历史上的传统,不涉及广西、湘鄂西部等区域的仪式音乐文献。
仪式是音乐艺术存在的重要母体,随着学界对音乐研究的逐步深入,仪式音乐愈来愈受到学者们的重视。通过对仪式音乐的探究,不仅可以延续以往音乐学学科所重视的形态研究,而且也衔接当前学界普遍追寻的文化式的音乐研究范式,并且,仪式音乐同样也是西南音乐的普遍存在形式,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仪式音乐研究,西南地区的仪式结构、类别极为丰富,所以对于西南地区仪式音乐的研究,不仅可以加深学界对仪式音乐的认识,同时也丰富与拓展了音乐的文化研究维度。由于西南音乐与其所在的母语环境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仪式音乐研究也便成为西南音乐研究的主要对象。目前学界对于西南音乐的研究仍然处于个案式的探索,在曹本冶主编的《中国传统民间仪式音乐研究——西南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中,曹本冶与杨民康等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西南仪式音乐成果与文献进行了梳理,但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范围上,其未全面梳理近代以来国内外学界对于西南仪式音乐的研究。鉴于此,本文借鉴以上两位学者对西南仪式音乐梳理的结构,并且填充近代以来国外对西南仪式音乐的研究成果,更为全面地梳理西南仪式音乐研究文献与论著,借此来审视西南仪式音乐研究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基于对上述文献的梳理与研究现状和特征的分析,试图由此推导出研究西南音乐的音乐地方学、类型学——音乐西南学。
二、20世纪以来中国西南仪式音乐研究述评
中国西南地区文化具有复合性与复杂性特征,在此区域中,汉传、藏传、南传佛教等流派并存。此外,同属世界三大宗教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也在本区域盛行,尤其是云南、贵州等省份,还有土生土长的道教等。同时,该区域的民间信仰仪式也同样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并与其他宗教信仰相互依存、彼此共生,以上多重原因造就了中国西南仪式音乐的面貌。相关论作也依据中国西南仪式音乐的面貌,从不同的角度对西南仪式音乐展开研究。
(一)国外研究情况
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外就有工作人员、传教士等不同身份的人员来到中国西南地区,由于不同的身份与目的,他们在进行相关活动的同时,也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音乐艺术进行观察、记录与研究。在这些人员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传教士塞缪尔·克拉克(Samuel R.Clarke),他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到贵州,在贵州做了20多年的新教传教士,1911年出版了著作《在中国的西南部落中》(AmongtheTribesinSouthwestChina,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此部著作分为两大部分,其一介绍苗族等少数民族风俗,其二论述传教士在苗族地区的相关活动与成果等。英国20世纪20年代驻成都领事的外交官G.A.Combe,到四川西部的康定地区时,观看了藏传佛教宗教活动,并通过当地藏族民众和懂藏语的外国传教士,详细了解宗教仪轨及仪轨中舞蹈和音乐的意义。从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初,驻四川成都的外国传教士和大学教师们,创建了一种学术刊物《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其前身是《传教通讯》),其中一些论作涉及西南仪式音乐等方面的内容[2]。
之后,国外对中国西南仪式音乐的研究人员主要集中于相关学界的学者们,不同于20世纪初对西南仪式音乐记录、整理的方式,这些学者对西南仪式音乐的研究呈现出个案与精深性的特点,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论作有Danniel A.Scheidegger:A General Survey with Special to the Mindroling Tadition (《藏族人仪式音乐:关于敏珠林寺传统之一》),此著作成书于1988年。吴犇向彼兹堡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Ritual Music in the Court and Rulership of Qing Dynasty(1644—1911)(《清廷仪式音乐与清朝统治(1644—1911)》),其关注的对象为清朝的祭祀、朝会、庆典等清宫仪式,还有蒙古族、藏族的藏传佛教仪式,等等。此外,Helen·Rees以其博士论文A Musical Chameleon:A Chinese Repertoire in Naxi Territory(《音乐变色龙:纳西属地的中国汉族曲库》,1994)为基础,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纳西洞经音乐,并出版了专著Echoes of History-Naxi music in Modern China(《历史的回声:纳西音乐在现代中国》,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在此书中,Rees通过纳西音乐的文化变迁来看洞经音乐的操控者如何回应外界的变化,以此构建或重构族群的认同与边界,等等。
从以上国外研究西南仪式音乐的成果来看,20世纪初的相关成果主要是对西南仪式音乐的记录与介绍,以及对其音乐形态的分析等。其后,随着音乐学学科研究范式的转换,以及对西南仪式音乐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外对于西南音乐的研究开始以“将音乐当做文化来研究”(study music as culture)的视角展开,并通过仪式与音乐的互动关系来探讨音乐的文化意义与功能等。
(二)国内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对于中国西南仪式音乐的研究已全面展开,并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以不同的角度切入予以探讨,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由曹本冶主编的著作《中国传统民间仪式音乐研究——西南卷》。该书的内容与章节共分为三部分:绪论、上篇与下篇。绪论部分对中国西南地区民间信仰仪式音乐特征进行概括。上篇为专题综述,共5篇文章,主题为对不同语支或不同民族的民间信仰体系、民间信仰特点和仪式音乐传统进行整体性和概括性的描述论述。下篇为个案研究,共4篇文章,是研究者深入实地调查,获取一手田野调查资料,并在仪式音声或仪式音乐研究的框架下,对仪式个案进行整理分析与解释等。在理论方法上,该著作运用曹本冶所提出的仪式音声理论,以“音声”作为研究仪式的切入点,在具体实践中运用音声声谱、内外、远近、定活等方法来对仪式事项进行研究。该著作意在突出仪式音乐在中国传统音乐整体系统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对该领域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同时,以仪式音乐的视角,较为全面整理、梳理与分析西南地区仪式音乐的概况、特征,并且理论的运用与切入的视角为中国“本土化”的民族音乐学科的建立提供有益的学术探索。另外,中国音乐研究所自成立之初,就将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作为调查和研究的重点,尤其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音乐的调查,既对西南不同少数民族的音乐艺术以民歌、器乐、舞蹈等类别进行整理,同时也对不同音乐体裁的历史渊源进行研究。虽然这一阶段的考察多是注重西南少数民族音乐的形态与分类,但其中也兼顾到了一些仪式音乐。对于这些音乐的收集与整理,不仅为我们全面了解西南少数民族音乐艺术,以及日后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在工作方法和调研水平方面也为我们积累了大量经验[3]。综上,相关论作与田野考察多是从总体性的角度分析、了解、整理西南仪式音乐文献情况,而在西南仪式音乐的研究中,还存在大量个案性的研究。鉴于中国西南地区宗教与仪式复杂性的状况,对于中国西南地区仪式音乐个案研究的文献梳理,笔者将借鉴当前学界对中国西南仪式音乐的过往梳理与分类,从制度性宗教的仪式音乐与民间信仰仪式音乐两方面来对相关文献进行论述与分析。
1.制度性宗教仪式音乐方面
在此方面研究的相关论著有更堆培杰的专著《西藏宗教音乐研究》[4]。在该专著中,作者将藏族宗教音乐依据藏族历史与宗教的关系、宗教形态,划分为苯教音乐与藏传佛教音乐。从篇幅上来看,苯教音乐与原始宗教音乐单设一章(第一章),而藏传佛教音乐为4章(第二章至第五章),可以看出更堆培杰的研究侧重于藏传佛教音乐。在藏传佛教音乐方面,更堆培杰根据藏传佛教修行目标、仪式音乐的功能、审美特征、不同寺院的不同法事等对藏传佛教音乐的乐器、乐态、乐谱、相关乐人等逐一论述。更堆培杰的《西藏宗教音乐研究》是了解与认识藏传佛教仪式音乐的重要著作。中央音乐学院袁静芳教授主编,嘉雍群培所著的《西藏本土文化、本土宗教——苯教音乐》[5]中,将苯教的论述分为:苯教历史溯源与分类、苯教的诵经音乐、苯教的说唱音乐、苯教歌(乐)舞、苯教密宗仪轨“羌姆”、苯教器乐与乐器等共6章,较为全面地介绍了藏族地区苯教与苯教音乐,并对现存的藏族苯教宗教与仪式的现状进行了论述。同时,本书打破了以往在藏族宗教音乐研究中重佛轻苯的传统,填补了藏族苯教与苯教音乐研究领域的空白,是认识、了解苯教的重要著作,此著作对藏族音乐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此外,格桑曲杰的专著《西藏佛教寺院仪式音乐研究》[6]也对藏传佛教仪式音乐有一定的论述与介绍。
西南地区藏传佛教仪式音乐研究的相关代表性论作有姜读芳的硕士学位论文《藏传佛教“祈愿大法会”中的音乐及宗教思想——以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格迦寺为例》,该文以一年一度的祈愿大法会为研究对象,从藏传佛教观与哲学观、美学等角度论述藏传佛教音乐的哲学内涵、美学思想及治疗的功用等[7]。卢婷的硕士学位论文《藏传佛教觉囊派中壤塘确尔基寺岁末驱魔法会音乐研究》,以藏传佛教觉囊派中壤塘确尔基寺岁末驱魔法会作为研究对象,对法会中的音乐及其相关文化进行研究。研究过程中,卢婷以亲证践行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对法会及法会音乐作共相与自相的分析,通过外在形式和内在理念、我认知和他我证悟相结合,卢婷认为音乐在法会中不仅是一种艺术形式的存在,它更是法会仪轨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的意义与佛教教义、理念是紧密相联的,它不仅为法会烘托了一种神秘氛围,它更是僧人对佛法的参悟、修行的方式[8]。
在基督教仪式音乐研究方面,陈蓓的博士学位论文《黔西北大花苗基督教会音乐文化研究——以葛布教会为例》[9],通过以葛布教会为例的黔西北大花苗基督教会音乐文化的研究,探讨了基督教这一“舶来文化”的传承和变迁,并在“大文化”背景下对民族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得失有所探讨,同时,分析音乐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杨民康的专著《本土化与现代性: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研究》[10],同样也是对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仪式音乐文化研究的重要著作。在南传佛教方面,杨民康的著作《贝叶礼赞——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研究》[11],其以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为研究对象,分10章对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中的音乐进行论述。该著作不论是从个案的角度,还是理论方法的角度,对于音乐文化研究者来说都是一部重要读本。
2.民间信仰仪式音乐方面
在西南民间信仰仪式研究的论作中,其研究方式与视角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在这些论作中,有从音乐与其所在场域的互动关系,来探讨音乐文化的伦理关系与文化意义等,较有代表性的论作有罗佳与杨正文的《音声韵律、节奏与仪式场景的意义——雷山苗族年节音乐浅析》,该文以曹本冶所提出的音声理论为切入点,对雷山苗族年节音乐进行解析,并在苗年的民俗节庆的场景中,对音乐的伦理、节奏、乐器等因素进行描述,同时对音乐的文化内涵进行解释[12]。此外,还有路菊芳的《四川越西彝族“尼姆撮毕”信仰、仪式和音声三重关系之探析》[13],该文以四川越西彝族祭祖仪式为考察对象,从仪式观念、仪式行为、仪式效应3个方面探析信仰、仪式和音声的三重结构关系及仪式音声特征。拙作《四川平武白马藏族婚俗仪式中的音声元素探析》[14]也属于此类型的研究。该文以“音声”作为契入点,将四川平武白马藏族婚俗仪式中的音声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平武白马藏族婚俗仪式中的音声形态特征,以及白马藏族操控婚俗仪式音声的内在文化逻辑。通过观察婚俗仪式与音声的互动关系,笔者认为,平武白马藏族借助音声来区分婚俗仪式中不同身份的人员,并以内外有别的方式对新郎新娘的身份进行重新确认。同时,在功利性音乐观念的影响下,白马藏族借助个人与家族性的婚俗仪式与仪式中的音声对村寨集体进行地缘性的认同。
在西南民间仪式音乐研究中也存在对于仪式音乐形态关注的论作,例如何岭在其《布依族婚礼八仙乐整体性量化分析——以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布央”八仙乐为考察案例》[15]中,以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布央”八仙乐为考察对象,运用整体性量化分析法,并从曲式结构、色彩变化、音区音域等角度来对仪式中的八仙乐进行分析,以此来揭示八仙乐与仪式的关系。崔善子与金艺风的《苗族鼓藏节仪式音乐研究——以贵州榕江县记怀乡记怀寨为例》[16]也是此方面研究的代表,该文以发生于贵州榕江县记怀乡记怀寨的苗族鼓藏节仪式音乐为研究对象,并对仪式音乐中的铜鼓节奏型、吟诵调祭祀歌、芦笙曲“给略”进行音乐形态等方面的分析,得出铜鼓节奏性由一个段落的二次变化重复构成,其结构内部都以基本节奏型与变化节奏型的结合而构成,作者认为这样的构成使其节奏富有即兴性。对于芦笙调“给略”的分析,作者则从乐器的编制、音域、和声构成与声部结构等方面,来进行形态特征分析,并指出芦笙调“给略”中的这些和声音程是旋律型中的核心音调不断地变化重复中所形成的,是一种即兴演奏中相互结合的产物,并无规律性。
在中国西南文化艺术中,女性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其不仅是文化艺术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其民族文化的重要传承人。在西南仪式音乐研究中,也存在以女性为视角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是周楷模的《民间仪式中的女性角色、音乐行为及其象征意义——以中国白族“祭本主”仪式音乐为例》[17],文中,周楷模以白族的祭本主仪式为个案,并对仪式中女性歌舞进行分析,以此探讨作为性别研究的女性角色、行为与宗教传统、民间信仰演化之间的象征性关系。通过对于祭本主仪式中女性音乐行为描述与分析,作者认为:女性在本次仪式中的音乐行为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这些意义揭示着世俗角色与神圣的角色在世俗和宗教、远古与现代的仪式中进行着不断转换的角色互动关系。仪式中,女性角色与宗教中的“女性崇拜”的深沉关系,也将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人类信仰历史的源头,为女性的“民间信仰创造”提供一些鲜活的史实。同时,周楷模也指出,在女性的仪式角色纳入到性别研究视野中时,还应注意民间仪式音乐行为、音乐场景中关于“性别建构”或“性别认同”等文化特质。
西南仪式音乐不仅蕴含着民族精神的文化象征,同时也是民族文化艺术教育与传承的重要场域,在西南仪式音乐研究中也涉及到相关问题,如贾力娜的博士学位论文《三官寨彝族丧葬仪式音乐及教育功能研究》[18],该文以仪式音乐作为切入点,探讨三官寨的彝族丧葬仪式音乐及教育功能。该论文的研究拓宽了教育本身狭义的论域,并从仪式的角度来看文化整体语境在彝族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等。随着对西南仪式音乐研究的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西南仪式音乐存在多种文化相互共生的文化状况,所以在相关研究成果中,不仅涉及到西南仪式音乐个案性的研究,并且也论述了多种文化、大小传统文化等的现象与更深层文化意义。例如万代吉的博士学位论文《藏族民间祭祀文化研究》[19]。作者在整体论的基础上,以人类学中大传统和小传统对比分析的思路,分析藏族民间祭祀文化的渊源及特征,把藏族民间祭祀文化置于小传统中,试图从这个角度分析藏族民间祭祀文化与原始信仰、苯教、藏传佛教的关系。作者认为藏族民间祭祀文化具有自己的特征,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受到了大传统文化的影响,但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是互动、互容和互补的。作者还认为藏族民间祭祀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心理功能,同时也具有普遍性和传统性、多元性与娱乐性、世俗性与功利性等特征。
从以上相关西南仪式音乐研究的论著来看,目前国内学界对于西南地区音乐的研究已逐渐铺开,并且研究视角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其研究人员身份不仅是本区域内的专家学者,如杨正文等,还有其他学术区的专家、学者也参与到西南地区仪式音乐的研究中。这些研究成果多是以某一族群的仪式与宗教信仰中的音乐认识为主,或者是宏观性的对本区域的民族仪式音乐文化进行分类研究等。在诸论中,不仅对仪式音乐的形态进行分析,还通过音乐与仪式的互动关系,对相关问题进行解释。然而,无论何种形式的研究,其研究视角与地域极为分散,并多是以学者本身的知识结构或兴趣对相关仪式音乐事项进行探究,研究没有较为清晰的系统与逻辑,也没有形成团队优势。此外,与其他地域的仪式音乐研究相比较,无论从规模上、还是研究深度上,西南仪式音乐研究仍具有进一步探索的潜力,同时,西南地区仪式音乐种类繁多,但随着西南地区经济发展逐步加快,现代化发展又对仪式音乐形成了碾压之势,这些因素导致西南仪式音乐研究面临着更为严峻与紧迫的情况。所以,从以上对目前研究现状与方式的分析中,可以了解到当前学界对西南地区仪式音乐的研究尚存在不足之处,同时,研究的进度与广度大大地落后于西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西南仪式音乐,乃至西南音乐研究难以满足当下西南地区经济发展需要。由于本地区内民族、历史、文化的复杂性,上述个案研究仍然难以全面了解西南地区的音乐文化面貌,对本区域的研究依然需要大量的个案研究堆积。
通过对20世纪以来中国西南仪式音乐研究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到文献中大量存在从某角度切入,来对某一族群的仪式音乐进行个案性的研究,如女性角度、音乐形态视角、历时性的角度、文化角度、教育视角等,而这一类的研究从研究属性与方式上来看,属于西南仪式音乐分类性研究(1)西南研究中的分类研究具有两重含义:一是对某西南各族依据不同的特征进行分类研究;二是在对某一族群个案性的研究中,依据该族生存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文献记载等多种因素,将其与他者进行区隔,并进一步对其进行精深性的研究,而在这一过程中,同样具有分类研究的属性。。不仅如此,在上述文献中还存在另一种研究范式,即依据大小传统关系,以及多种文化共生的状况,来探讨民间仪式音乐内部,或者民间信仰仪式音乐与宗教性仪式音乐之间的关系,此类研究属于西南仪式音乐关系性的研究属性,如前文所述万代吉等人的论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由此可见,在西南仪式音乐研究中,关系与分类这两大主题与范式凸显。同时,依据前文文献梳理的情况来看,西南仪式音乐研究不论从质量上,还是数量上,已具备一定的规模,并且西南音乐研究视域较为明确,再加之关系与分类两大主题与范式的明晰,以及当前西南仪式音乐研究亟待改善的需要,是否得以断定:针对西南音乐研究的类型学、地方学——音乐西南学可以建立?此外,关系与分类两大主题仅是西南音乐研究独有的研究范式吗,西南音乐研究与西南研究是怎样的关系?
三、音乐西南学的构建
中国西南地区的研究是诸多人文类学科的重要论域与学术讨论区,就音乐学来说也不例外。从上述对西南仪式音乐文献的梳理可知,不论是成果数量,还是质量,西南仪式音乐研究已初具规模。然而,随着音乐学等学科在此领域研究的逐步深入与开展,在西南音乐文化层面的研究范式以及形态特征逐步显现。同时,对于西南地区音乐研究而言,其不仅丰富了学界对中国音乐形态丰富性的认识,在学理与研究视角方面,也是极大地扩充了西南研究的论域。由此来看,以上西南仪式音乐研究范式的浮现,以及研究对象的明确,是否可以建立起针对中国西南地区音乐研究的类型学与地方学,以促使西南音乐的研究学科化、专题化、跨学科化等,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音乐西南学的提出,并不是空中楼阁式的学科构建,其建立与产生和历史传统有着紧密的互动关系。
(一)从西南民族研究、西南研究到西南学的提出
近代以来,国人对于西南的关注与研究主要经历了3个阶段:晚清时,国人鉴于英法以安南、印度为前哨,虎视中国,呼吁加强西南边疆的国防建设;民国前后,随着西方民族学译著在中国传播,受其影响,国内学者开始对西南族群进行零星的调查和研究;现代意义上的西南研究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末,抗战后形成高潮。彼时全国主要高校及研究机构陆续西迁,大批学者组织调查团队,深入高山纵谷,探求西南民族的体质、语言文化及历史演变之轨迹[20]。起初,由于现实的需要,针对西南地区的研究居于主导。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参与到西南地区研究的学科越来越多,如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语言学等,研究视域的拓宽,使得对西南地区的研究逐渐由民族研究过渡到西南研究。经过一段时期的沉淀,并基于西南研究的现实需要与学术要求,1948年,在西南研究的基础上,江应樑代表南方学界提出“西南学”构想。从“西南民族研究”“西南研究”再到“西南学”,是西南研究趋于高潮的产物,反映学界运用进化论的观点,将西南社会中的某些文化特征看作中国历史不同发展阶段在现实社会的遗存[20]。当然,时代所限,对西南学研究切入角度的局限存在争论,但类型学的建立,为日后西南研究提供了学科化、专题化的发展方向。然而,随着学术团队先后宣告解散,“西南学”逐渐湮没于学界。
当前,学界对于西南地区的研究再未搬出“西南学”这一学科概念,但在西南研究领域中,一些主题与论题依然挥之不去,这首先体现在西南研究主题之一——民族分类研究。对于此类专题的研究始于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该传勾勒出西南地区的大体轮廓:此地分布着众多的族群,这些族群在政治、经济、习俗等方面与中原有着诸多的迥异之处。其后对于西南地区的记述因循着《西南夷列传》的记录与书写方式。近代,西方殖民者、传教士、人类学家等进入西南之地,并采用较之《西南夷列传》更为细微的分类手法,对西南地区的人种、语言、风物等加以研究与记载。从这一角度来看,西学的渗透是对分类研究的进一步深化。20世纪20年代起,一批受到民族学等西学规训的国内学者也参与到西南研究中,他们在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追寻西学的范式,这样的分类研究方式一致持续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此期间,另一种研究理念与范式出现,这以马长寿对西南民族文化的认知与观点为代表,其认为本区域诸民族历史悠久,历代称王者凡十余次,诸族复居两大文明之间,往往能采撷众长,为其息养蕃孳之助。而外来之两大文明,虽鼓荡于西南凡2000年,然以性质不同,反不能收单独同化之效[21]。同时,在1978年,费孝通提出“藏彝走廊”的概念,主张对西南民族进行分与合,多与一的研究,这一观点对学界的影响至今。从马长寿与费孝通的观点来看,学界在对西南民族进行分族研究之时,已注意到族群之间的互动、文化间共生关系问题。在此基础上,王铭铭通过对西南地区的田野考察,并结合国外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研究的前沿动态,进而提出“文化复合型”[22]“中间圈”[23]“超社会体系”[24]等观点。至此,出现了研究西南文化的两种不同的论域与概念,即分类与关系研究,这样的研究范式的出现,不仅是学界研究深度与广度的加深与拓展的表现,也是西南区域研究中的民族文化特征所致,正如马长寿所提到,本区域内诸族采撷众长,但却又性质不同,反不能收单独同化之效,由于这样的缘由,造成了以上两种研究范式的出现,而分而未化、融而未合的西南民族文化特征也造就了西南研究的属性与性格。
以上所述西南研究历程,对于西南音乐研究,以及音乐西南学的建立而言,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从其研究历程中可探寻到,由于西南地区民族文化分而未化、融而未合的特点,使得相关研究方式方法得以形成。如此看来,关系与分类的研究范式与主题,并不是西南音乐研究所独有,而是普遍存在于西南研究的各领域中,所以从研究方法上来看,西南音乐研究与西南研究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是对西南研究传统的继承。此外,“西南学”虽在近代提出,但由于诸多原因,其湮没于学界,这也导致了西南研究未形成类型学,研究中容易出现各自为政,囿于学科壁垒等问题,西南研究虽然历史悠久、种类庞大,但未能成“学”,使得其不能对西南音乐研究进行有效的供给,从这一方面来看,音乐西南学的建立有其自身的迫切性与必要性。
(二)音乐西南学构建
早在古代,我国就有从地缘角度展开专项研究的传统,如春秋战国时期《尚书·禹贡》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地域文化研究著作[25]。到20世纪初至中叶,我国已有“敦煌学、徽学、藏学”等三大显学,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地方经济的不断发展,地方文化越来越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关注地方文化的专题研究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1986年上海学研究所举办首届研讨会;1991年泉州学研究所成立,同年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成立;1998年北京联合大学成立了北京学研究所;2002年温州启动温州学研究;2005年在内蒙古自治区的鄂尔多斯市成立了中国地方学研究联席会……截至目前,因地名学的地方学研究,已经蔚为壮观[26]。
随着地方学的不断深入与专项化,一些学科对本区域的专项研究逐渐成为地方学的亚学科,这其中以音乐尤为明显,如上述所提到的北京学、上海学的音乐研究均设立了音乐北京学、音乐上海学等类型学。音乐地方学的建立虽然存在着学科归属的问题,但其学科研究优势凸显,以往的音乐学研究主要涵盖传统音乐、民族音乐学、音乐美学、音乐史学专题等方面。而音乐地方学不仅涵盖了以上诸多的研究方向,同时又可以超越音乐学各门类传统的研究方式,着力探索精专、综合的研究思路,对同一专题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对不同专题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延伸研究广度。由上述音乐地方学建立的学理基础,再来观照音乐西南学的建立。学界对西南研究的历史极为久远,并且随着西南研究广度与深度的不断扩展,旧有学科中各自为政、囿于学科壁垒等问题越来越难以适应新时代西南研究的要求,加之我国西部战略的实施,全球一体化的加速,以及旧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理论与实践等都迫切要求建立起针对西南音乐研究的类型学——音乐西南学,以此来对西南音乐进行区域化、专项性的研究,满足当前的研究需求。
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方向,音乐地方学一经开启,便体现出其独特的学理特点与研究优势,即突出区域文化的地方特色,发挥地方发展的独特品味,更有效地整合地方资源,注重理论研究对当地建设的指导意义。在不断的推进过程中,以往的音乐地方学研究逐渐体现出两种整体性特点:第一,渐趋形成以城市为中心的地方学研究体系,这从“××学”的名称上便能清楚得知。第二,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双重重视[26]。除了以上的共性因素外,对比已建立起来的音乐地方学,如音乐上海学、音乐北京学、音乐哈尔滨学等,其研究都与所在城市文化性格有着紧密的联系,从而造就了在研究方式方法上的迥异。然而,不论是音乐上海学、音乐北京学,还是音乐哈尔滨学均将近代以来音乐文化的发展视为其研究的重点,如音乐上海学研究注重还原上海近代以来的音乐文化,探寻上海地区在中国近代音乐发展史中的独特历史价值。音乐北京学研究视角不仅侧重于金元以来的民间音乐艺术、宫廷音乐文化、金元诸宫调、杂剧艺术、明清曲子、说唱、古琴艺术、地方戏曲及京剧等,还极为重视近代学堂乐歌与专业音乐教育发轫等研究。音乐哈尔滨学研究注重近代以来白俄势力在当地的影响,以及伪满洲国时期日本文化的渗入等。由上述分析可知,虽然不同地域文化属性不同,研究方式上有所差异,但诸音乐地方学的共性因素较为明晰,即以城市为中心构建地方学研究体系,对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双重重视,以及将近代以来音乐文化的发展视为研究的重点,等等。相较之下,音乐西南学虽然与上述音乐地方学的研究类型与特征存在一定的交集,但差异性仍然较大,音乐西南学的建立与研究视角有着自身独特的特征。首先,音乐西南学的建立不是以某一城市为视角展开整体性研究,而是建立在比城市区域更大的范围展开研究,城市只是它研究中的一部分(2)在西南音乐研究中也存在对城市音乐文化的探索,如中国音乐学院陈波的博士学位论文《城市藏族音乐多元呈现与意义表达——基于成都的田野考察》,以及其相关的研究成果等。。其次,不同于以上音乐地方学以汉族音乐文化、租界地音乐文化为研究侧重,音乐西南学的研究对象多是西南少数民族音乐事项等。再次,以上所述几个音乐地方学均是以城市近代音乐文化发展为研究重点,而音乐西南学不仅关切近代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发展与变化,还要对西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共生性问题进行探讨,更要追问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历史渊源,以及当代少数民族文化何去何从的现实问题,同时,源于本区域民族文化分而未化、融而未合的特征,音乐西南学还要探讨民族音乐跨文化的现象等。此外,由于研究区域较大,研究的问题繁杂,较之其他音乐地方学,参与到音乐西南学的学科较多,如人类学、民族学、民族音乐学、考古学、文献学,等等。由此来看,音乐西南学构建是一个极为庞大的系统工程(见图1)。最后,一个学科的建立有两种情况:其一,是指有着特定的对象,以及针对研究对象所衍生出特定的研究方式与范式,如物理学、生物学等;其二,是依据研究内容而定,由于研究内容蕴含着丰富的价值,加之研究时间较长,已形成传统,故此另辟之学,如“藏学”“红学”,等等。从以上对于学科建立的框定标准来看,音乐西南学兼具两种类别学科建立的属性。首先,音乐西南学研究对象定位于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乐事,以及越南、老挝、泰国等一些东南亚国家的音乐事项,可见音乐西南学研究对象的范围较为明晰。其次,在研究方法层面,通过对过往西南学、西南研究的梳理,分类与关系这两种西南研究范式凸显出来,并成为当今西南研究的主要视角与范式,任何学科深入到西南地区研究中,都难以避开,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也同样如此,同时,这也为音乐西南学研究范式的构建提供了相关的研究方法。从上述对于西南仪式音乐文献的梳理中,可以看到多数仪式音乐的研究个案都是对分类这一主题与范式的研究,并通过分类研究展开对某一族群仪式音乐的探索。一些文献与研究成果中已经涉及到西南研究中关系研究的视角与主题,例如在曹本冶主编的著作《中国传统民间仪式音乐研究——西南卷》中,杨民康依据民间信仰、宗教信仰等的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关系对西南仪式音乐进行分类,由此可见,杨民康等学者已注意到西南音乐研究中的文化共生问题[1]30—33,所以,分类与关系研究范式已在民族音乐学领域中的西南音乐研究中出现。因此,从学科构建应具备的条件来看,音乐西南学不仅具备所谓学科之学的属性,其还具有因内容研究而逐渐成为一门学科的属性,这是不同于其他音乐地方学之处。

图1:音乐西南学构建图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音乐西南学研究方法与范式——分类与关系,似乎飘摇于范式与研究主题之间,所以针对二者的研究要视情况而定。分类与关系虽为音乐西南学研究方法、范式与主题,但又存在研究视角和方法泛化之嫌,试问对于哪一种音乐文化的研究,不存在分类与关系两个视角。由此来看,分类与关系研究范式容量较大,适用于西南音乐研究中这两个主题与视角的方法等均可容纳其中,从这一点来说,这对音乐西南学研究的诸论可以百花齐放,但又存在大而不当的问题,基于此,在涉及到两个主题与视角的研究方法中,应注意方式方法落地化的问题,来规避上述因素的发生。在以上问题中,尤以曹本冶的仪式音声理论具有代表性。在其主编的《中国传统民间仪式音乐研究——西南卷》著作中,他以“仪式音声”理论为切入点,来探讨西南少数民族仪式音乐事项。其理论是将民族音乐学的音乐视域拓展到音声范围,并且通过内外、定活、远近三个变量,以及音声声谱来展开对仪式音乐个案的研究,通过宗教仪式师徒相传的途径进行跨文化研究。从其理论方法的实践来看,无不体现出分类与关系研究范式,其中,以内外、定活、远近三个变量,以及音声声谱展开对仪式音乐个案的研究属于分类研究范畴,而以宗教仪式师徒相传的途径展开跨文化研究为关系研究范畴。然而,由于西南诸族分而未化、融而未合的文化特点,同时,处于西南区域的众多民族具有无文字民族的特质,如上文对西南仪式音乐研究的梳理中所提到的苗族民间仪式音乐、白马藏族仪式音乐,等等,所以,在运用仪式音声理论时,应对其理论进行适当的调试,尤其是在跨文化比较的关系研究中。以白马藏族仪式音乐为例,白马藏族是极为古老的民族,其居住于藏彝走廊的东部边缘,是典型的无文字民族。由于白马藏族宗教仪式有着原始宗教与民间信仰的属性,并且史料方面缺乏相关的记载,因此,对白马藏族仪式音乐进行跨文化比较与分析时,不应采取以制度性宗教仪式师徒相传的途径展开,而应以仪式音乐形态为参照坐标等其他路径展开对其跨文化研究的探索。根据以上分析可知,虽然分类与关系研究范式为音乐西南学提供了研究的方法与路径,其所涉及到的相关方法均可纳入其中,但二者的容量过大,较为泛化,因此,研究过程中,在分类与关系研究范式中涉及到的任何方法,应考虑到西南民族音乐文化的特性,相关方法落地化时,应对其方法进行一定的微调,来对相关事项进行分析,从而揭开西南音乐文化的真实面貌。
以上,通过对近代西南仪式音乐研究成果与文献的梳理,以及与其他音乐地方学设立和学科研究视域、方法的比较,并且对学科设立类型的论述,可知西南音乐研究早已具备一定的规模,音乐西南学具有建立研究西南地区音乐文化类型学与地方学的基本条件,同时,从学科建立类型的角度来看,音乐西南学不仅具备内容之学的学科属性,由于学科方法与研究对象的明晰,其还具有学科之学的属性。不过,由于研究视域较大,加之相关范式容量过于泛化,因此,相关方法在落地化的过程中,针对研究对象的特性,应适当微调,以此来贴近客观事实。
四、结语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建设,中国西南地区日渐成为国内外学界所关注的热点。对于西南地区的研究,国内外都已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传统,然而,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始于近代,其研究脉络大致经历了从西南民族研究、西南研究到西南学三个阶段,其中研究方法主要以分类的研究方式为主。同时,对于西南地区文化复合性的认识,使得关系性的研究方式成为了西南研究的另一范式与主题。由此,关系与分类成为了西南研究的主要视野与研究方法。关系与分类研究范式的提出,不仅是源于学界对西南研究的不断深入的认识,也是由于西南诸族分而未化、融而未合的民族文化特征所致。
在相关学科研究的带动下,音乐学、民族音乐学等学科也逐渐将研究视野汇集于西南地区,其中,西南仪式音乐的研究是其学科研究中的重中之重。当前,曹本冶、杨民康等学者以不同的角度,对西南仪式音乐研究进行了梳理与回顾,然而,不论在时间维度、还是空间维度上来看,相关文献的梳理有一定的缺憾。根据此前诸多学者对西南仪式音乐研究梳理中的缺失,借鉴前人对相关文献梳理的角度,本文以民间信仰仪式音乐、制度性宗教信仰仪式音乐两个方面对20世纪以来的西南仪式音乐研究进行综述,以此来了解西南仪式音乐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存在的问题。通过以上梳理可知,不论是国内研究、还是国外研究,对西南某一族群仪式音乐的分类研究依旧是当前学界所关注的焦点,此类研究占据西南仪式音乐研究中的较大篇幅,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杨民康等一些学者已对关系性的研究有所观照。可见,分类与关系研究已在音乐学、民族音乐学的西南音乐研究论域中体现。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音乐学,还是其他学科,对于西南地区的研究均存在诸多不足,并且西南地区的现实情况也较为紧迫,而这些因素迫切地需要针对西南地区音乐文化研究的专题化、类型化,加速对于西南地区音乐文化的了解与挖掘。
早在古代,我国就有从地缘角度展开专项研究的传统。改革开放后,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地方学如雨后春笋般的建立起来。受此影响,在音乐研究领域,音乐地方学也开始出现,如音乐上海学、音乐北京学、音乐哈尔滨学等。从以上学科的建立来看,此类音乐地方学有着极为相似之处,即将近代以来音乐文化的发展视为研究重点。从一个学科的建立类型的情况来讲,以上所述的诸多音乐地方学,多是内容之学,而音乐西南学不仅具有内容之学的属性,还兼具学科之学的特征。通过对已有的音乐地方学建立与发展过程的论述与分析,以及对西南仪式音乐研究的梳理,可以肯定音乐西南学足以具备成为针对西南地区音乐文化研究的地方学与类型学,同时,基于当前旧有学科中各自为政,囿于学科壁垒等问题越来越难以适应新时代西南研究的要求,音乐西南学的建立迫在眉睫。在笔者看来,音乐西南学具有以下特征与优势:第一,音乐西南学研究视域明确,是以西南诸族的音乐文化为研究对象,不同于以上音乐地方学的关注点,音乐西南学不仅侧重于西南诸族音乐文化的横向研究,也观照历时性的问题,同时,其关注的研究视域与角度更为多元、广泛,具备强大的跨学科优势与支撑;第二,音乐西南学学科研究方法较为明晰,如上所提,西南研究中的两大范式——关系与分类,在西南仪式音乐中凸显,由此来看,这两大范式不论是西南研究、还是西南音乐研究,都是萦绕不开的两大主题,从这一角度来说,关系与分类同样也成为音乐西南学研究的学科方法;第三,关系与分类的学科范式容量较大,在其域内涉及到的相关方法均可运用于西南音乐研究中。当然,在相关方法落地的过程中,由于本区域民族文化的特征与复杂的状况,应对研究方法进行适当的微调,来适应西南音乐文化的研究,以使研究结论更为客观。
音乐西南学的提出与建立是西南音乐研究逐渐走向成熟的表现,它的建立对研究中国西南音乐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首先,音乐西南学不仅在原有音乐学元理论方面产生一些落地化后新的理论方法与范式,随着音乐西南学的研究深入,也一定会为一般“音乐学”或所谓世界的“音乐学”的丰富和完善,做出中国学界的积极贡献,为之提供更多需要反思的依据与例证。其次,从现实角度来看,随着一带一路与西部开发的力度加大,西南地区卷入全球化、现代化的态势随之加快,这一因素不断影响着西南地区的音乐文化生存状况,基于此,有目的的、有系统的、有组织的,并在一定的方法框架内展开对西南地区音乐文化的研究已迫在眉睫。所以,音乐西南学的建立,不仅是对音乐学、人类学等学科理论方法的延伸,从现实意义来看,学科的建立对西南地区音乐文化的发展与传承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与意义。最后,西南地区在地理区位上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而放眼全世界,类似于西南地区的文明过渡地带大量存在,学界需对这些区域文明文化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推进。不同于传统学术区的研究,对于此类区域的研究,从这一种角度而言,揭开了不同于以往的新世界。由于地缘上的相似性,音乐西南学的建立、实践与研究,将为此类区域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经验与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