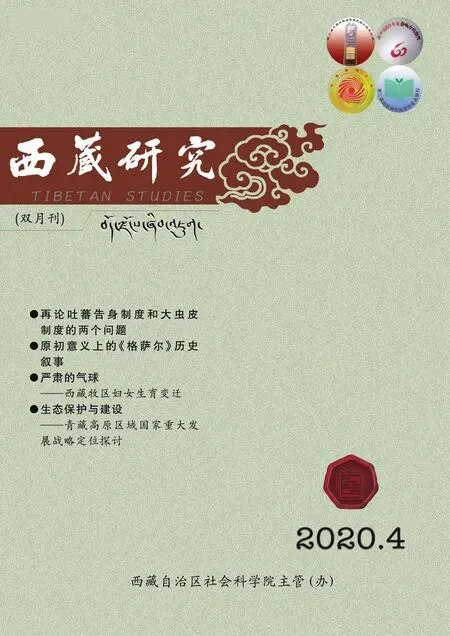原初意义上的《格萨尔》历史叙事
诺布旺丹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北京 100732)
近年来,笔者在研究实践中,越来越意识到《格萨尔》史诗起源问题的认识对其诸多命题的理解和阐释的重要性,深感“不明其源,则难解其流”的真谛所在。故笔者将《格萨尔》史诗的起源和演进等问题又重新纳入到了研究视野,并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探讨和争论在学界由来已久,但似乎老生常谈,已成为一种顽疾,甚至演变成为一场没有结论和终点的持久战。笔者认为,对这一瓶颈式问题的解决,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第一,《格萨尔》史诗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现象,其中包含着诸多历史的要素,首先要采用历时性的视角,运用历史和辩证相统一的原则。一方面将格萨尔的生平及其历史置于藏族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时空下加以观照;另一方面采用一般的历史研究方法,把史诗主人公及其主要的业绩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个体和客观历史事件,对他们进行量化分析。第二,史诗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学样式和文类,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和族群中,早已成为国际学界的研究对象,产生了诸多的学术流派。其中关于史诗起源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的热点,不断涌现出值得借鉴的学术成果。另外,当代结构主义思想等新的学术理论和方法对于此类问题的分析研究颇具建树。运用新型学科理论和方法并借鉴外来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平行比较研究,将为《格萨尔》史诗起源的研究及其演进问题的梳理提供新的思路。
一、研究问题的视角
一部史诗往往是多种文类的集合体,文类构成了史诗的内在文本结构,而文类又是理解一种文学文本特性最直接、最显性的层面。综观史诗,我们确实会观察到《格萨尔》史诗文本是由不同的文类部件组成的,并非一种文类贯穿史诗文本的始终。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三类:历史性文类、神话性文类和艺术性文类。其中“历史”只是史诗诸文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后来的口传语境下,不断经历“去历史化”的过程,神话化和艺术化的意象逐步融入到“历史”中,进一步构筑了“史诗大厦”。正如罗伯特·斯科尔斯等在《叙事的本质》中所言:“作为一个特征,原始史诗叙事运用具体的历史人物、地点或事件,将其和源自神话的人物进行虚构性组合,进而创造出自身的叙事手法与技艺。于是,在《贝奥武甫》《罗兰之歌》及《尼伯龙根之歌》中,我们发现了这种组合,无论是许耶拉克,还是查理曼,抑或是阿提拉,均多少在历史上依稀可辨,而在他们身边还站着神话—虚构式的贝奥武甫、罗兰或西弗里德(Siegfried)”[1]60。显然,历史与虚构的互渗也是世界其他史诗的一个显著的特点。这么一来,就产生了史诗文类的内部分层结构,形成了历史、神话和艺术的深层融合,产生了“史”和“诗”的结合,“be”与”mean”的呼应,“已然”和“或然”的融通,从而使史诗文本肌理不断从客观向主观、从经验层到感觉层、从世俗到神圣演进。这是在《格萨尔》史诗的文类演进方面带有深层和终极意义的一个命题,对其加以探究固然重要,但是,如果对原初意义上的格萨尔历史不作学术梳理,难窥其堂奥,也难以厘清《格萨尔》史诗源流关系,发现《格萨尔》史诗原初的动力学起源。
在《格萨尔》史诗起源问题上,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学术观点,一种是关于文学虚构或文学建构的观点,另一种是关于历史学(缘起于真实历史)的观点,两种观点各执一端。关于文学虚构的观点在世界史诗或古典主义诗学史上,没有同类的研究成果可以证明其合理性。相反,作为宏大的叙事,任何史诗的产生都不是凭空的和纯主观臆造的,必定有其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或文化基础。但史诗由于其口传性和变异性特点,关于它的起源问题,已成为世界史诗研究中一个较为常见、甚至自古争鸣不休的命题。由于史诗与历史、神话、宗教和艺术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史诗起源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近现代学术界认为,史诗是一个民族童年时代的产物。的确,在许多民族的历史上,远古神话成为史诗产生的源头。俄国神话学者梅列金斯基认为史诗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两种不同的故事文类,一是关于文明使者(祖先或创世者)的传说,二是早期的勇士民间故事,这类故事“以大地、地形地貌及天体形成、四季轮回、潮起潮落,各种动植物以及人类本身的起源,粮食作物、火以及劳动工具的产生,社会法规以及诸多仪式的生成为描写对象的神话居多”[2]20。在大西洋的拉美尼西亚、马来西亚的邦克群岛、太平洋岛的瓦努阿人、法国的拉美尼西亚、印第安人和古亚细亚人、爱斯基摩人等都有类似的神话故事,它们形成了不同规模的且属于它们自己的神话性史诗,但多属创世性神话。这些神话的主人公作为一种“文明的使者”,往往演进为勇士民间故事,成为史诗中的英雄。综上所述,以往的学术界普遍将史诗的产生归结于这个民族童年时代的精神遗产,神话则被视为史诗的滥觞。除此之外,还产生了历史学派、神话—仪式学派及心理学派等,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阐释、解读和分析了史诗的起源问题,并从各自的角度比较片面地强调史诗起源发展的逻辑起点。然而史诗是一个民族或族群在其口传时代创造的民间智慧的集大成者,其起源问题也是一个具有复合型、多元型和层累型特点的学术命题,似乎很难用某种单一的学派观点或视角加以滤清。因此,梅列金斯基对此提出过较为精辟的论断,他说,如果说历史学派是以独特的“天真的历史性”为基础,忽略了史诗的艺术概括的特点的话,那么新神话派则将史诗艺术简单解释为一种象征,且他们将该种象征归结为宗教抑或是病理学的“潜意识”范畴[2]9。历史、神话、宗教、艺术、隐喻、象征等内容几乎在任何史诗中都显得极为突出,且其关系绵密交织在一起,难分轩轾,其原因则是它们构成了所有史诗的基本命题。因此,在研究任何一部史诗时都很难绕开这几项内容。纵观世界诸史诗,不管它们当今的面目多么多姿多彩,内容多么纷繁庞杂,结构如何错综复杂,体量多么巨大,其起源显然都是有迹可循的。就《格萨尔》而言,它既非一个神话性创世史诗,也并非产生在藏民族形成的早期阶段,它是一部关于格萨尔王这位英雄的神圣叙事,本质上属于英雄史诗,而且它又产生于11—13世纪,这一阶段对于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民族来说早已进入到文明时代。因此,黑格尔的理论、梅列金斯基关于文明使者和勇士民间故事学说、神话—仪式学派、心理学派理论等不适用于对格萨尔起源问题的解释,即使像“勇士民间故事”学说这样的理论可以部分地解释《格萨尔》史诗演进过程的某一个阶段,但在起源问题上很难给出有效、客观、正确的结论。笔者对《格萨尔》史诗研究和世界其他相关史诗的观察表明,众多的史诗均起源于真实的历史,或以历史作为底色发展起来的。因此,历史即是众多史诗萌发的原点。史诗与历史关系问题的研究,长期以来在史诗起源问题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便是查德威克兄弟(Chadvick,K.M.andChadvick,M.K.)。在他们多卷本的巨著中,以历史学派的观点阐述了英雄史诗的起源问题。他们的核心论题就是史诗的历史可信度和故事发生的时间的准确度问题。他们将爱尔兰人史诗、《伊利亚特》,甚至《圣经》中的主要人物与编年史中的人物一一比照,并为所有史诗中的人物找到了历史原型。他们甚至认为,俄罗斯最初大量出现的史诗都是对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摹写[2]3。查氏兄弟的历史学理论对于《格萨尔》史诗起源问题的探究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在《格萨尔》史诗所包含的三种文类中,“历史性文本”则扮演着“基因”的角色,是史诗叙事本体和史诗故事文本的原型,同时也是史诗形成过程中的两个重要的步骤,即神话化和艺术化的奠基性前提因素。
二、作为原初“历史”的《格萨尔》
探讨《格萨尔》史诗起源问题的前提是承认《格萨尔》史诗仍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它有一个最初的起点,沿着这个基点,史诗得以不断演化。笔者将这种原初阶段的“历史叙事”称为“原叙事”“原初叙事”“原始经验”或者“原型叙事”[3]。“原叙事”更多地指称产生在人类早期的叙事,在这里即指《格萨尔》叙事文本的初始形态,它是未更多被主观意象所染指、未被文本化的自然历史形态。它由物理构成的空间世界和逻辑秩序构成的时间坐标来体现,由因果性联系构成。而“历史”一词,来自于古希腊爱奥尼亚方言“Historie”,这种写法的根源是印欧的“wid-weid”,指“看见”,从中又衍生出了梵文“vettas”,指“证人”,在希腊文中“istor”也即“‘目击’证人”。“istorein”即指“设法去知道,去弄明白”。后来希罗多德在其《历史》的开头就将其定义为“《研究》和《调查》”。“看到”,方可“知道”。甚至有人认为“历史”有三层含义,一是关于一系列事件本身;二是关于这一系列事件的复述;三是一段历史就是一段“复述”。这种“复述”既可以是真,也可以是假;既可以是“历史事实”,也可凭借历史事实“杜撰”[4],也就形成了通常所谓的“历史”和“故事”之区别。
显然,人们对“历史”有着不同的理解,并且形成了不同的“形态”和“范畴”。但作为一种初始形态,其客观性仍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这种“原初历史”或原始经验便是世界上众多史诗形成的起点和活水源头,甚至是诸多史诗文本的“故事主题”或“故事范型”。历史性作为英雄史诗的底色,是由其本质特点决定的。但史诗或在史诗中反映的历史又与一般的“历史”不同,在世界几大主要史诗中,多数都产生于数千年之前,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古希腊荷马史诗《奥德赛》和《伊利亚特》以及古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均如此。就史诗属性而言,它们均属于英雄史诗,英雄史诗中的主人公往往都是一种半人半神的英雄形象,它们伴有浓郁的神话色彩。尽管其中神话与历史并存,其比例有轻有重,印度史诗带有更多神话色彩,而希腊、荷马和古巴比伦史诗便带有更多历史成分,显然神话与历史是史诗文本中两个最重要的基因。因此,对它们的起源也自然要追溯到神话或历史那里。但由于那时尚未出现书面记载,仅靠口传记忆传承,并且时间跨度巨大,无从稽考在其最原始形态方面留下的任何直接的客观证据。正如当代文艺理论家所秉持的观点那样:史诗与恐龙已经绝迹。尽管我们可以合成一部史诗,并做到与原始版本有几分相似,就像我们能够在博物馆里拼装出恐龙一样,但问题是,原始版本得以产生的条件已不复存在。大自然在创造那些漂亮的怪兽时所展示的纯真已经消失。对此,她绝不会去复原;而叙事艺术家也无法凭借经验与想象对取自神话和历史的素材加以真正原初性的组合[1]9。但“真正的英雄诗歌讲的是人,尽管可以将诸神引入情节中,人依然是主要兴趣所在”。英雄史诗的主人公往往都是真实存在于历史的人物。在希腊,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荷马史诗中阿伽门农的金色迈锡尼、以及涅斯托尔(Nestor)的沙色皮洛斯(sandy pylos)(1)希腊海港,《荷马史诗》被描述为勇士涅斯托尔的城邦。参见罗伯特·斯科尔斯詹姆斯、费伦·罗布特·凯洛格:《叙事的本质》,于雷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0页。。古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也是以苏美尔早期王朝初期的社会和历史为背景的,甚至吉尔伽美什本人也被考古证实为真实的历史人物,乌鲁克第一王朝的君主。历史学家认为,他与基什国王阿伽及回教统治的西班牙的战争为“英雄时代”背景。亚美尼亚英雄史诗则以10世纪亚美尼亚基督教与来自埃及和波斯的伊斯兰教徒之间的战争为背景。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地区的史诗则以14—15世纪土耳其人入侵东南欧为背景,讲述基督教与回教徒之间的战争故事[5]39,很可能是一部反映了王朝初期基什与乌鲁克争夺巴比伦尼亚霸主地位的史诗。日耳曼人的英雄史诗,如《老埃达》中的沃尔松家族传奇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中反映的情景,大致与5—6世纪史诗的民族大迁徙和欧洲蛮族国家建立时期相吻合。法国的《罗兰之歌》是8世纪查理曼大帝的英雄史诗,讲的往往都是史诗英雄主人公的神圣业绩,但它所表达的则是以整个民族或相关族群的集体记忆和沧桑变迁的历史命运。一个又一个实例证明,大凡英雄史诗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历史”。即使黑格尔这样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家都认为客观的历史构成了英雄史诗的内核,认为史诗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全部世界观和客观存在,在经过它本身对象化的具体形象,即实际发生的事迹,就形成了正式史诗的内容和形式”[6]406,并认为“荷马和传说出于荷马之手的诗篇要比所歌咏的特洛伊战争晚几百年。特洛伊战争是一件实际发生过的事,正如荷马确实是个历史人物一样。”[6]407尽管如此,史诗永远无法像编年史一样呈现历史的细节,因为编年史是对“历史”的一种“事实记忆”,而史诗则是一种“价值记忆”,“事实记忆”在无文字时代很难凭借口头保持其真实细节跨越数千年之久。相比之下,《格萨尔》史诗形成较晚。那时已经出现书面记载,而且许多物证尚可去搜罗,大量相关的民俗文化事象依然保存和延续至今。因此,它们为其起源问题的揭示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可能性。本文拟通过地理学、历史文献学和民族志学等记载描述关于《格萨尔》史诗相关的历史地理、人物的谱系和活动情况等,以期获得关于《格萨尔》史诗作为原初历史时期的基本信息,然后运用社会记忆学理论对这些描述进行学理性分析。


阿底峡56岁,宗喀王尺南德赞即角厮罗42岁……岭·格萨尔16岁时阿底峡圆寂……岭·格萨尔50岁,米拉日巴尊者48岁……萨迦·索朗泽毛6岁,萨迦贡嘎宁保56岁,帕毛珠巴和嘎尔玛都松钦巴38岁。藏历第二甲子已亥土猪年,即1119年,岭·格萨尔王在地处黄河源头的玛沁雪山附近逝世,享年81岁”。格萨尔诞生于土虎年的说法在史书上有较为确凿的记载,因此,笔者也倾向于格萨尔生于1038年,卒于1119年的观点。


除此之外,关于格萨尔的英雄业绩在一些史书中或只提及或用转述的口吻描述,关于他的活动的遗迹或武器铠甲,以及生前的遗物在藏族地区各地零星可见,包括被称为格萨尔家庙的玉树囊谦县达纳寺保存着其三十员大将的灵塔。本文并无意通过文本上的记载勾勒出一幅完整的《格萨尔》的历史画卷,而是旨在通过这些零星的记载说明格萨尔这个历史人物的真实存在性和《格萨尔》史诗的前历史形态。
三、研究问题的方法与资料的取舍
本文所引用的资料主要是文字文献而不是口传文本。根据社会记忆学理论,这些资料均属于功能性记忆材料。文献记载是一种文字性的记忆。文字性的记忆与口头记忆不同。文字性记忆分为储存记忆和功能记忆两种。储存记忆是指那些尚保存在文学文本或用绘画、舞蹈、音乐等艺术的形式,或在博物馆中收藏的,或以未被辨别的考古性文物等形式残存的文献性资料,甚至这部分材料尚有可能遗存在尘世生活中,在民间被搁置,它们往往都是杂乱无序或未被分类,更尚未经过人为的选择。而功能记忆性的文献材料则经过了选择、配置、联结和意义建构的过程,已成为一种富有意义的、可用于构建文化身份认同的文字性材料。这些功能性记忆材料最初或来自于其他功能性记忆材料,相互间形成了互文性联系,或来自一些储存性记忆材料,经由整理者加工、编排和意义的联结。功能记忆的文献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合法化的,与政治、权力等官方有关的,体现为一种官方的政治性记忆;一种是固化在社会记忆里,用于纪念、致敬、历史自觉意识、建构文化身份认同等目的,往往在节日、宗教仪式或历史性文献中被体现出来;另一种是非官方的批判性或颠覆性的反回忆性材料。本文所引用的文献资料主要包括前两类。一部分来自中央王朝的官方史料,如《明史》《元史》《中国历史地图集》等,这部分资料,旨在构建国家话语权力,具有官方话语色彩,是一种站在宏观角度跨越社会、种族、地理三种界限、具有全局性意义的功能记忆文献;还有一部分来自藏族传统的文献资料或研究成果,如大司徒绛曲坚赞的《朗氏家族史》、巴沃·祖拉陈瓦的《贤者喜宴》、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布吉的《安多政教史》、松巴益喜堪布的《问答》、毛尔盖·桑木旦的《藏族史悉皆喜乐明镜》等,这部分文献资料或研究成果是与纪念或致敬性意义有关,也与为了塑造格萨尔作为集体认同的象征性表达、或体现族群的自我表达和历史自觉意识等有关。还有部分来自非藏族学者的研究成果,如任乃强先生的《藏三国的初步介绍》、刘立千先生的《刘立千藏学著译文集——杂集》、石泰安的《西藏史诗和说唱艺人》,这部分研究成果旨在客观阐述格萨尔及其历史文化,并且其表达方式采用了现代批评分析性方法,具有理性和科学的色彩。另外还有松巴堪布《问答》中关于格萨尔英雄业绩的记载,已在上面做了说明,在此不再赘述。以上几种不同类型的文本尽管旨趣或意旨有所区别,阐述的方法迥异,但它们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格萨尔及其岭部落作为真实历史人物或历史现象的不同侧面。除此之外,在西藏及其他涉藏省各地纪念馆、庙宇、寺院或民间遗存有诸多的格萨尔文物,但由于它们均属于储存记忆性文献或文物,未经过人们的筛选、甄别和整理,故未在此作为本文的依据。在资料的取舍上,在此未将过去学界往往注重的艺人的说唱本或《格萨尔》史诗的文本作为史料依据。有两个原因:一是口头说唱文本,未经过文人、学者或官方的甄别和科学的选择,带有很强的随意性和主观性,不足为证;二是根据社会记忆学理论,口传的历史分交际性记忆和文化记忆两种,交际性记忆是属于记忆者的经验或鲜活的记忆,他们往往是事情的经历者或见证者,或者记忆者是通过经历者的记忆或回忆获得的,有较强的客观性,这种记忆的鲜活性至多可以维持三代人或80年左右,之后进入文化记忆阶段,文化记忆阶段的历史便进入了绝对的过去,其阐述不免带有很强的故事化倾向,或传说化色彩,已经从历史的“复述”过渡到了对历史的“建构”或“重构”,而且由于口传时代人们的思维往往缺乏逻辑性或推理能力,带有很强的想象或诗性色彩。
四、结论
“历史叙事”是世界上诸多其他史诗产生的起点,但多数史诗由于其时代的久远性,其真实历史面目无法从文字性文献资料和民俗生活等得到复原,只能通过神话、考古等形式间接稽考和获取。即使这样,学者们仍然从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古希腊荷马史诗《奥德赛》和《伊利亚特》以及古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甚至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日耳曼人的英雄史诗《老埃达》、法国的《罗兰之歌》、英格兰的《贝奥武甫》等诸多英雄史诗中找到了它们的历史原型,对其起源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并认为它们是对当时不同历史事件的“模仿”和“再现”,起源于“具体的历史事件”。另外,在学界还形成了英雄史诗起源问题的“历史学派”理论。相比之下,《格萨尔》史诗产生年代相对晚近,诸多的文献、文物、遗迹以及鲜活的民俗事象均真实记载和呈现了关于《格萨尔》前史诗时代的历史情形,成为观照格萨尔历史的镜像。通过对相关功能性记忆资料的解读,运用相关的理论和方法以及世界其他英雄史诗起源问题的学术成果,我们至少可以获得如下结论:格萨尔是一个生活在11—12世纪的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他生于1038年,卒于1119年,是三江源地区“岭”部落的首领,也是一位英雄。后来《格萨尔》史诗无论在体量上如何扩展、内容上如何演化、结构上如何变化,“历史叙事”都是它们的“原型”和“本体”,也为史诗后来进一步发展为历史神话化、神话艺术化奠定了基础;他所统治的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牧业部落,起初与周围的各部落互不统属,元朝后期尤其是明朝,中央政府在此设立了管辖机构,成为与西藏腹地等几个重要的地方性权贵并驾齐驱的部落联盟;当时岭国及其三江源地区的大部分地区仍处于以口头交际为主要手段的前文字社会,由神话时代向英雄时代过渡的时期,口头传统是他们唯一的交际手段,族群的集体记忆是祖先历史文化的熔炉;由于地理上的边缘化,佛教文化尚未成为该地区主流意识形态,神话和原始思维仍主导着该地区人们的价值观。格萨尔时期,也是佛教开始进入三江源地区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