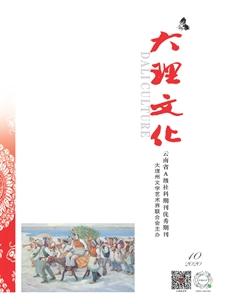父亲(外一首)
叶华荫
一
猶如长年打交道的泥土
父亲其貌不扬
宽厚手掌
垒出茅草房
将我乡野上的童年收藏
一天天
穿着农民这套世袭的制服
从老屋进进出出
蜜蜂似的迷恋阳光
认字不多
但农家残破的院墙
围不住他望子成龙的希望
燕巢上低矮的屋檐
遮挡不了他噙着思念的目光
每回想家
总是最先出现
汗珠子挂在宽阔额头
憨厚羞涩的笑脸
柔软低垂的夜幕
便悬出一滴游子咸涩的泪
用轻柔的光
抚慰浑身疼痛的村庄
二
收割稻谷的人
收取玉米的人
纷纷从家里涌出
驾着车
背着筐
远远望去
父亲
只是其中一个小黑点
大不过一粒雪白的米饭
乡土读物中会动的名词
飘着淡淡汗酸
曾经饱满的额头
多皱而黑亮
不再强壮的手脚青筋裸露
负重时身子老是摇晃
三
我是二十六年后
乡土上再次长出的一个你
身强力壮的父亲
侍弄过田地也没法休息
要么握锄
铲除我心底滋生的杂草
要么拿剪刀
修理我行为上多余的枝节
由于怕疼
一提起父亲
我就胆颤心惊充满恐惧
无视你的良苦用心
还记恨过你
后来人们说我
身上有泥土的芬芳
手上有草木的汁液
才看见
父亲的皱纹里
瞬间溢出舒展的笑意
四
父亲的翅膀
常因我的失意而疲倦
无力庇护我是他的致命伤
那样的日子喉咙里卡了刺
父亲总是疼痛难忍
翻滚哀叹
父亲的面容
常被我的欢悦洗亮
我幸福的河流
必将汇入父亲的海洋
点点滴滴的甜蜜
他都会从我稚嫩的花瓣
小心收进心灵的蜂房
年近八旬的父亲
如今依然每天
置身在子孙的苦乐中间
承接生活的反复锤錾
硬朗如一尊雕像
奶 奶
一
以血肉之躯死守
温暖着乌黑矮小的茅草房
小村观音河里
那使了一辈子的双手
既厚又大
坚韧粗壮
老茧凸出黄硬刺眼
握锄耕种
挥镰收割
拉孩子
洗衣做饭
喂猪洗碗
不会累似的
眼睛一睁忙到黄昏
晚睡早起养成习惯
年过古稀了
性情不变
除非卧床
从不偷闲
二
不轻易串门
别家有事才去坐坐
不是自卑
一切在知足中
理所当然地劳作
田地里
屋内外
被要吃要喝的家
紧牵着奔波
七十四年的光阴多么宽松
却习惯紧握
春种
秋收
衣食来自重复耕作
平滑的额头
积聚起越来越多的阡陌
当箐底的石竹棍
拄成第三只脚
已撑不住
飘摇风雨里
你棉纸样的单薄
三
只要能动
就不停从手里
耕耘出炊烟
爷爷走得早
等一个人熟稔了
那些田地
脸上的地界
随之明显
皮肤翻卷风沙
目光干涩黯淡
芦花开上头顶
转眼已是雪天
老牛老马难过冬啊
带走属于自己的
最后一个冬天
随之而来的春光
将一张沧桑
慈祥的脸
塞进打湿衣襟的冬雨
制成一粒永久怀念
坠在儿孙胸前
四
爬满藤条的额头和老脸
不断生长的晶莹果子
除了换粮
有时是我的零花钱
有时是书纸笔墨和新衣裳
可有的还没成熟
黑夜的藤蔓
突然就绞杀了你的藤蔓
不得不丢下
难舍的小院
任山雨
在亲人胸中肆意弥漫
你我亲密共处的日子
霎时分出里外
一阴一阳
无所不能的时间隔断空间
我迎接太阳
你跟浓黑阴冷混为一谈
旧衣服烧给了你
就不会再出现
两行清泪点燃一盏心灯
逝者如斯
木框紧咬遗像
疼在后人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