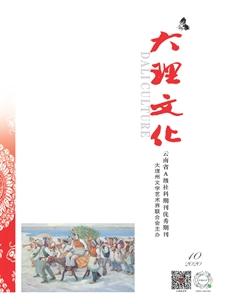一个安妥心灵的地方(外一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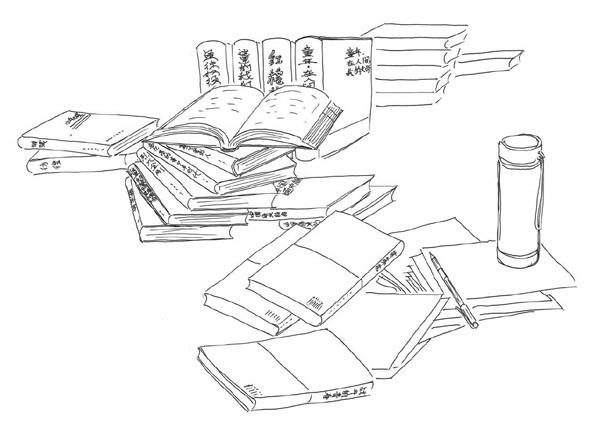
无论你最后挣了多少钱,拥有了多高的职位,你发现,你最终追寻的,只是一个能够安妥灵魂的地方。
——马德《你可以是最漂亮的人》
书是一个教师吃饭的家什,啃书自然就成了我每日必习之功。大半辈子从事教育工作的我,与书结伴,一路走来,直到退休。自己又喜欢读书,喜欢买书、订阅书报杂志,业余还喜欢写作。当年梦寐以求的,就是何时能有间书房,有张书桌,还有个书架,能安静地读书和写作。
当民办教师那几年,就住在家里,卧室就兼书房,饭桌也是书桌。没有书柜,连个简易书架也没有,书就放在几个破纸箱里,和些烂鞋臭袜一起,塞在床底下,难免有鼠咬虫蛀也顾不得了。在一个嗜书如命的读书人心目中,这简直就是亵渎。那时的主流社会“以阶级斗争为纲”,我“出身”不好,到处讨人嫌,升学、参军、就业,甚至找对象,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与我失之交臂。那种近乎“生而有罪”的困境,书的主人没有尊严,它们也不可能有尊严。
那时候,我感到迷茫和苦闷。我的生活中好像缺了点什么,我没法跟别人一样过正常的、有尊严的生活。我虽然喜爱诗和远方,但在我的现实里,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没有诗、远方,也没有我的位置;我不是不喜欢与人交往,我受不了交往中那种被人鄙视、被人怜悯、疑惑与嫌恶混杂的神情,让你整个心为之颤栗不已。虽然受到那么多的伤害,但我并不自怜,也不需要别人的悲悯。人的天性,本来就惧怕孤独,只要不是行尸走肉,都是需要寄托的。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对抗孤独。那时候,我的寄托就是拼命地找书看,书能把我带入另一个世界,让我燃起生活的希望和信心。只有游走在字里行间,我才会有一种安全感,找到一份安定,还有思想可以跟着这些书籍去随意飞翔的自由,才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我没有把读书当作任务,而是作为对抗生活、对抗平庸的一种方式,从未放弃建立尊严的努力。书中那些美好的人和事物,足以让我抵抗我所经历的黑暗、残暴和绝望,同时获得思考和挣脱的力量,顶住生活的压力,期待着明天崭新的开始。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我总觉得我的生活还在别处。
我当民办教师(身份依然是农民)那16年,报酬是每天10个工分,每月到生产队领3元补助,报销1公斤煤油。我们生产队是个穷队,分红最多的那一年,10个工分分到了0.28元钱,那时刚好能够买到一包“金沙江”牌香烟。自由市场(因不合法,那时叫“黑市”)大米0.5元左右一斤(那时粮食交易计量用“升”,每升大米6斤,价3元多),只能买到半斤多大米。大多数年成,10个工分只能分0.20元左右。分了口粮,生产队年底结算,反倒成了欠生产队债的“超支户”。
在那个极端的年代里,在社会的底层,在生存底线上苦苦挣扎,是阅读帮我渡过了人生的难关,不自卑、不沉沦,咬定精神救赎的理念,在无望中希望,在卑微中自尊,艰难地迈向有灵魂的生活。而今,还有谁能理解,1978年以及那以前漫长的岁月里,一个乡村“智识者”(鲁迅语)内心的希冀、绝望、痛苦和挣扎?内心深处那一点从未熄灭的萤火般的光亮,那就是他浪漫的理想和对自己命运的憧憬。这理想和憧憬在愚妄的时代喧嚣中显得那样另类、荒谬和孱弱,然而,这却是他赖以生存下去的精神支柱。
人有人的命运,书也有书的命运。
“文化大革命”初始,1966年8月,红卫兵挨家挨户抄家“破四旧” (破除所谓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书籍除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外,其他不分青红皂白,统统被列为“四旧”,抄没烧毁。比如,鲁迅先生的《呐喊》和《彷徨》,系旧版竖排繁体字,且书页发黄,红卫兵小将不识,竟把它们当黄色书刊抄去烧毁了——这是事后才知道的。当时全县中小学教师集中在县城搞运动,我并不在家,但我的书竟一本也没被抄走。据家里人说,是我们村红卫兵的头,一位叫“四海”的铁姓姑娘,对那些外村来抄家的红卫兵铁铁地甩去一句:“这是我们张老师的书,你们别动!”一句话,救了我的这些书。有《红楼梦》《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和《裴多菲诗选》,还有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上中下三册一套的《古代散文选》、汝龙先生译的平明版契诃夫小说《恐怖集》,已被报纸点名批判的当代作家艾芜、柳青、赵树理、周立波等人的作品,好险哦!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解放,用人唯才是举,不讲关系,也不讲出身、资历、学历。县里民办教师转正,公开考试,公平竞争。通过考试,我以优异的成绩得以转正。没错,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人。我平时就喜欢读书,本来就热爱教育工作,有幸碰上了这历史大变革的机遇,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当年,像我这样改变了自己命运的又何止千万!
转正后,我被调到一个乡镇初级中学任教,卧室不仅要兼书房,自己做饭吃,还要兼厨房,摆放锅碗瓢盆柴米油盐。所幸有了一张书桌,能备课改作业,还能摆放几本工具书和订阅的书报杂志。那是间土木结构的瓦房,我在床头的土墙上钉了两根木桩,搭上一块木板,把一部分中外名著放在上面。其他的大部分书仍委屈在几个包装箱里,堆放在靠书桌一面的墙角旮旯里。要看一本什么书,或查找点什么参考资料,仍然不方便。
那时正赶上拨乱反正,一大批古今中外名著重新出版,我不吸烟、不喝酒,转正后待遇有所提高,买书便也大方起来,几年下来,狭小的家中塞满了书。那时,白天忙工作,晚上勤阅读,这日子不知有多惬意。有时,为了读一本好书,时常夜以继日,丝毫也不觉得累。教学相长,日积月累,厚蓄而发,其来有自,提高了自己的教学能力。同时,业余创作把触摸生活肌理的体验内化并诉诸文字,也有了收获。践约自己的憧憬和向往,在省、州报刊发表了文学作品,并获奖,赢得了社会的认可和尊重。
调到县完中宾川三中任教后,学校给我安排的住房是个套間,二十来平方米,还有个简易的小书架,书桌是三屉两柜的,我和我的那些书的境遇有所改观。那些自学生时代以来,一二十年间省吃俭用陆续购置的书,其中几十册,还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破四旧”抄家,幸运地得以存留下来的。它们是我的“隐形伴侣”,不离不弃,陪伴着我,熏陶着我,和我一路前行。我把它们视为我生命的一部分,让书香承载着梦想,直抵灵魂和远方。就是它们,在我最落寞的时候,温暖了我的生活,构成了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不盲从,没有失去自我,没有沉沦堕落,不断地自拔与更新,帮我完成了人生角色的转换,找到了我在生活中的位置。
20世纪80年代,据说有文件规定,县级机关及学校职工福利分房,县处级干部才能享有50平方米的住房。那年月,一个县能有几个县处级干部!后来我在一本什么杂志上无意中读到了,1980年,著名作家后官至文化部长的王蒙住房即为40平方米,才晓得那个“有文件规定”的据说,并非空穴来风。
1987年,学校修建了教师宿舍十五套,40平方米的九套,30平方米的六套——显然就是按这一“文件规定”办的,当年年底建成。福利分房,我分到一套30平方米两室一厅的住房。虽然没有一间书房,但把卧室和厨房分开了。而且,在设计修建这些教师宿舍时,学校考虑周到,利用空间,在每套住房的隔墙上装修了一个小书柜。我又跟后勤要了两个小书架摆放在卧室里。我的工作条件,也是我和书的境遇又大为改善。我在一篇散文里戏称它为“半缘居”,取唐朝诗人元稹“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之诗意以明志。
1998年,申报中学高级教师职称时,州教育局的领导到我们学校调研,跟我们座谈。谁也没有想到,该领导座谈中竟问到每个教师的藏书,有没有800册?他说,读书是每个人的内在需要,是自我修养的完成,它关乎一个人的人生品质与生活质量,关乎一个人的成长。他强调,在这件事上,学校和教师负担着起承传续的角色。对此,近年人文学者钱理群先生的说法则是:“什么是教育?就是爱读书的校长和爱读书的老师,带领着学生一起读书。就这么简单。”
进入新世纪,住房实施商品化政策,学校组织教职工集资建房,每套120平方米,四室两厅。我终于可以给自己设置一间书房了。装修时,我在书房里特意做了两个高齐屋顶的大书柜,书桌呢,与时俱进,直接就做成了电脑桌。有一间书房,有书桌、书柜,看着那些伴我大半辈子一路走来的书,静静地列队站在我的书柜里。时光流逝,书页已经泛黄,文字却依然是崭新的;潮流可以过时,而思想却永远活着。心被这特定处所的气场渗透,感觉特别踏实而充实。每次看到有那么多的好书,还没能来得及阅读和重读,总会有一种被鞭策、被鼓励的幸福感油然而生。大半生憧憬和向往的有文化品位的生活,终成现实。
退休之后,有间书房,安妥心灵,弃绝浮华。无事静坐,有福读书,一卷中外名著在手,在此即可与千载之上、千里之外的大师们,进行跨时空的心灵沟通和对话,分享他们的人生智慧与人生经验。在全然属于自己生命的空间,为自己的心灵“美容”。偶有所感,作文遣兴。现实的情境虽然无趣,但内心的情景是最美好的。我的内心是我的梦,是五彩云霞空中飘,天上飞来金丝鸟,依然保持着对未来的向往。
择友与读书
小学毕业的孙女回家说,老师说了,你们找男朋友、女朋友,要到图书馆、阅览室里去找。听了让我吃了一惊。转念一想,也没有什么不妥,这个成长的年龄段给他们提个醒,也是必须的,意在鼓励他们读书学习。一般来说,一个爱读书、爱学习的人,人品不会太差。再说,图书馆、阅览室,还有书店,不比公园、饭店、歌舞厅、游乐园、棋牌室、烧烤摊人员复杂。在那里,能找到有理想信念的朋友,还能找到你自己。应该说,它们本身就是我们值得信赖的朋友。
新华书店就是我一生亲近守望的老友,说来话长。
1951年,新政权在宾川建政的第二年,新华书店落户宾川,在古镇州城南街的旧天主堂内,和县文化馆在同一个院子里。那一年,我刚好开蒙入学。那时,我常和祖母去赶州城街。祖母就在南街摆摊,出售自产自销的农产品,没我的事。我就自个儿溜进了临街的天主堂,去文化馆借小人书看。在那里,第一次见到新华书店代销处,两条板凳、三塊木板搭的摊子,出售新书新报刊。
两年后,代销处改为“新华书店宾川支店”,迁至州城西街南侧,铺面临街,在一坊瓦屋面楼房的底层。白底红字的木牌上,繁体行书“新华书店”四个大字,神采飞扬。人家说,那是毛主席题写的。还记得父亲在那里给我买过一本《人民画报》,奖励三年级期末考试名列榜首的我。画报封面上端画的是一只展翅飞翔的白鸽;白鸽下,是天安门和广场上庆祝国庆浩浩荡荡游行的群众队伍,是彩照。封面题为《和平的天安门》。1950年,为纪念社会主义国家在华沙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毕加索特意挥毫,画了一只昂首展翅的鸽子,著名诗人聂鲁达把它称为“和平鸽”。鸽子是那个时代供奉的“和平”的图腾。
古镇州城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新华书店的这两处遗址,至今仍在。
1954年,我从乡下老家到古镇州城上学,新华书店就成了我学生时代时常光顾的“阅览室”。我究竟在那儿买过多少书,大体上还是记得的,毕竟都是我当年心爱之物。岁月流逝,时代变迁,大都已淘汰散佚了。让我感慨的是,在我的数千册藏书中,现在还能找到在那儿买的一本《谁是最可爱的人》,青年出版社1952年出版,那种繁体字竖排右侧装订的老版本。而影响了我一生的那本《高尔基的青少年时代》,却再也无法找到。还记得这本书是根据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改写的。
1956年,新华书店随县委、政府迁往牛井镇,三间铺面,仍然是土木结构瓦屋面的老宅,就在下窝铺南面,牛井镇老中心街的下段。至今还面目沧桑地守望在那里。每当我从它身旁走过,我都会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它,向它行注目礼。多少往事随之涌上了心头。
1958年的一天,我们在新村坡原宾川一中分校建校劳动。那天,在那儿买到刚出版的《烈火金刚》的那个同学,得意洋洋的神气,让穷学生的我,羡慕得要死。我拿不出那1.20元书钱,当时我们每天的伙食费是0.17元,那是我们一星期的伙食费。还记得那个买了《苦菜花》读了的同学,眉飞色舞,唾沫四溅,给我们讲述土匪头子柳八爷和八路军于团长比试枪法那一章,听得大家如醉如痴为之倾倒,让他大出了风头。
我也在那儿买过一些书,大多是参加工作以后的事,如《山乡巨变》《长长的流水》《南行记》《播火记》《战斗的青春》《李自成》等。那时,新华书店给像我这样手头并不宽裕,而又特别喜欢读书的读者不少优惠和方便。过一段时间,书店就把一部分存书打折出售,特别是有的读者因调动搬迁,或清理旧物清理出来的旧书,还可以在那儿寄售,价格便宜。我买的大多就是这两类书。现在还有一部分藏在我的书橱中,上面还有原主人的签名。比如,余冠英选注的《乐府诗选》,苏仲翔选注的《李杜诗选》,刊载何其芳《论<红楼梦>》的《文学研究集刊》,蒋天佐译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还有普希金的《波尔塔瓦》《青铜骑士》,高尔基的《给青年作者》,艾青的《诗论》,魏巍的《黎明的风景》等。
“文化大革命”期间,“红色恐怖”让读书人心有余悸,“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紧箍咒言犹在耳,我仍在它开设于宾居街的门市部里,买到“文化大革命”前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它至今仍是我的枕边书之一。这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关于佛教起源及其各宗派的论述,道出的宗教真相,让我震惊不已。数十年对真理真相的追寻和探索,对社会人生的观察与思考,心中的不少疑窦,在这里找到了答案。
1972年,新华书店告别栖身10余年的民房老宅,迁往新村坡,建盖了自己崭新的楼房铺面。这里曾是上世纪宾川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改革开放,思想解放,我在这里获得的精神食粮就更为丰厚了。我至今仍珍藏着的,1977年《世界文学》复刊内部发行的1、2两期,就是朋友私下领我到书库里买到的。上面连载了前苏联作家鲍·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和巴金选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让当时因书荒十年“精神贫血”的我,差不多是一口气读完了它们。有些书你读了好多本其实就等于读了一本。比如我曾经读了很多本描写战争的小说,但直到读了《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才算是读到了第二本,直到读了巴别尔的《骑兵军》才算是读到了第三本。中学时代,我曾不止一遍地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又不知有多少次翻开书中“一个人的一生应当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一段“警语”,默默诵读。它成为我所崇尚的人生观,引导着我探求人生的道路。但直到读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读了毛姆的《人生的枷锁》,知道人生的真谛绝不止这些,还有爱,还有丰富的人性,让我豁然开朗,明白应该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健全的人。我力所能及地购买了解禁出版的一部分经典名著,一个个大师站在了我的书架上。缕缕书香,似阵阵清风,轻轻拂面,缓缓抚平我因生活奔波而浮躁起皱的心页。那是我读书受益最多的一段人生。
我喜欢的书,同一种版本,有购置了两套的。比如,傅雷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一套放在枕边,一套藏于书橱。同一外国名著,我喜欢购置不同的译本比较阅读。比如,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刘辽逸译、草婴译;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高长荣译、范晔译;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张秉衡译,蓝英年、谷羽译;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吴劳译、殷惟本译。让我购置珍藏阅读的不只文学作品,还有《通往奴役之路》《万历十五年》一类学术名著。我不记得是谁说的了,经典就是可以反复阅读的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无论何时何地,与它们邂逅,总会有一种潜在的与之凝视与对话的感觉,给我以信心、定力和底气,一下子振奋起来,心里泛起生活的激情。
半个多世纪,一路走来,新华书店伴我成长,与之交往,即使在“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那个年代,也从未间断。只因一生敬重知识,崇仰文化,而读书的价值又绝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人性无法改變,读书却能扩大认知,纠正偏见,唤起你的悲悯心、反省心、进取心。当一个人无知的时候,可能会做出没有人性的事情,这才是最可怕的。在一个喧闹的世界里,多读书,多思考,不随波逐流,就是活在了人生的高地。有些东西是至死也不能丢的,比如内心的善良,比如正直,比如骨头,丢了,我们自己都会看不起自己,还指望谁能做你的朋友!
编辑手记:
李维丽的《云龙的河流》是作者在写作上的一个突破,“河流”,就这两个字似乎就能预想到这将会是一篇大气磅礴、奔流澎湃的文章,而且她不只写一条河流,而是将云龙境内的几条河流并在一起写,这本身就是一大挑战,何况是对于一个惯常写“细”、写“轻”、写“情”的女性作者而言。这篇文章的精妙之处就在于很好地处理了“大题材”与“小写法”之间的关系。面对云龙数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境内奔流不息的河流,作者很巧妙、很真实地避开了地理大散文的写作,没有洋洋洒洒、旁征博引的引用及感叹,她很注意写她看到的,旧州的那一座古戏台、通京桥头那一户准备早饭的人家、皂角达用小麻织布的女人、漕涧老街打瞌睡的小猫……这些活生生的场景犹如一个个衔着烟斗“讲古”的老人,历史烟云也好、沧海桑田也罢,都能于一呼一吸间为我们和盘托出。澜沧江之奔腾不息、沘江之质朴宁静、关坪河之原生态,漕涧河之古秀烂漫,每一条河都展现了自己的气质和灵气,但都无一例外地以奔流的形态流了千年,滋养着云龙那一方土地及所有生命。忆苏的《蔬笋记》则关照日常和人们最为亲密的东西,葱、韭、白菜、蕨菜这些充满烟火气息的“俗物”,在作者精、雅、灵的笔下也变得典雅灵秀了起来,一个个洋溢着生命的活力和生活的本真气韵。作者笔力老道,每一个蔬笋都有着不同的气质,它们或者是水灵清秀的小姑娘,或者是敦实朴素的妇人,或者是从远古走来自带清气的女子,有着灵慧之气、澄明之质,且没有刻意雕琢的痕迹,都是与生俱来又浑然天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