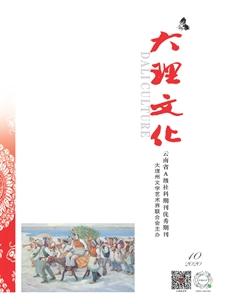杨蕊的诗歌
杨蕊
好久不见
起风的时候
正好路过那条开满桂花的街道
淡淡的香味
在悠闲的人群中扩散
坐在古铜色的椅子上
一抬头,好像
就能撞见你温柔的眼睛
翻越千山万水
面对无数个接近目的地的路牌
才能触及你所有的悲喜
和离别后不断重叠的
生活场景
旧事物
一棵干枯的桂花树影子
突兀地占据着
花坛的一小块空地
枝条细长而凌乱
把它和一些旧物件归类
比如那张用花梨木加工的圆桌
它封存的春天
还在遥远的雪山
雨水穿过陌生的村庄
浸透老屋的房梁
石头镂刻的水缸长出苔藓
它们深藏着哲学家的语言
半缸清水
用尽一生的光芒
來笃信
时光的深厚
和疏浅
梨花序
梨花从远处捎来信件
有清风 炊烟 雨露
还有做过的梦
突兀的露天火车
穿过梨花群落
几万株梨花俨然是迁徙之徒
借着梨花的白
布施道法
月光在他的衣领上打结
生活的泥泞暂时放下
敬奉最纯净的泪水
大地悲悯
灵魂和草木不朽
在雨里
和窗外的雨仅隔着一张
米白色的帘子
帘子上有跳跃的图案
像春天里穿花格子衬衫的少女
我在屋里听,雨
落在桉树的枝叶上
落在枯萎的扁豆花上
落在一顶废弃的车棚上
反复地听
陌生感越来越多
但,可以肯定
即便我在人群中泪流满面
谁也不会轻易发现一张悲伤的脸
我和熟悉的事物在雨中
温柔地告别
唯有,带着所有的幻想
离去
才能保持彼此最初的信仰
偶遇的花
夕阳里
一朵花,初识人间烟火
夜幕来临
它收起所有的秘密
路过它的身旁
它轻悄悄地告诉我
它的名字
也带草木
受雨水润泽
正在忏悔前世的罪过
蚂蚁和花朵
半夜,雨水
在花瓣上堆积成淡紫色的湖
天空撒下黑色的穗须
幻想和忧郁堵截了花朵的迅速枯萎
从它们落地的声音开始
不知道这些柔软的花
是在什么时候飘落的
花柄上还粘着蜜汁
是蚂蚁喜欢的丰收时节
我从蚂蚁的眼里
仰望过一朵花的世界
突然涌现在胸口的语言是什么
是解缚的鸟群,消融的影像
黯哑的灯塔
遥远的
消散
我们失去的黄昏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失去了黄昏
甚至失去了它的颜色
春天里
没有人发现我们在花海中
手牵着手漫步
鲜亮的白鹭把胸脯挺得很高
狩猎的号角凭风歌唱
深邃的孤寂
悲伤,像疯长的野草
漫长的雨季
黄昏在绵密的河岸线上
带着糖果的味道
隐没
邮寄麦田
母亲回到乡下,做小本生意
田间地头长满野菜
她兴奋得像个孩子
向我炫耀那半箩筐折耳根和香菜
我总担心她日夜行走在雨中,不按时吃饭
雨后,我和天空一样悲伤
电话里,小镇上的麦子黄了
突然间,像吹来了一阵风
麦穗是金黄的
麦秆也是金黄的
所有的麦田连成一片
这是多年前
我站在山顶所看到的田野
母亲不断给我寄来小镇上的蔬菜 水果
麦穗 泥土 乡音
怀抱着远方的田地
做一个完整安稳的梦
细碎空间
孩子睡着了,我感觉他在做梦
皱眉头,咧嘴笑
翻个身,手托着下巴继续睡
简单却踏实
深秋过半,很多事情还不能结尾
家里的阳台一直空着
雨水落进来时
采一把野花插在旧瓶子里
我比原野更富足
这一生
只做两件事
记住一些人
忘记一些人
在交错的时空里
互不相欠
牵牛花
一朵独自盛开的牵牛花
突兀地生长在凌乱的石子间
我在一个清冷的早晨撞见它
我们彼此都是不速之客
它是荒地上最冒昧的颜色
紫色,深紫色
带着理想主义者的浪漫和忧郁
它是时光片段里的感性存在
知道,傍晚
它将会收紧所有的色调
之后,随性舒展
花瓣边缘的流畅曲线
让我安心地释放着生活的拘谨
此刻
它给了我恰到好处的留白
但又不完全是为了我
久久地对视
眉宇间,阳光浅浅
最终,我还是在牵牛花身上发现了
它被鸟雀啄食的痕迹
此前
它过于华美
风不忍心到来
苦 渡
这些年,我经常怀念母亲的村庄
它的名称、轮廓、形状越发清晰可辨
但我忽略了它本身存在的意义
婚姻、青春、死亡、流转、变迁
实质性的重量和厚度不断叠加
疼痛不是多余和伪装的
总在夜猫掀起瓦片的时候更加剧烈
時间旧址里的那个人患病死了
总感觉是有人在故意开玩笑
桃花带粉,春天刚到
人间是一个渡口,渡生,渡死
石块垒砌的坟堆朝向麦田
过早拔节的麦穗露出柔软的光芒
扶犁耕田的人已躺在它们身边
雨水过后,麦粒硕大
他悲苦的半生像极了春风
追逐麦浪,是他一生的信仰
我需要在身体里供奉一座佛堂
点灯、添油、跪拜、诵经
安放所有的悲苦和疼痛
石头的宿命
几年前,我在金沙江边捡了一堆石头
圆的 方的 红绿点状的 带条纹图案的
与江水告别
把它们带回遥远的城市
用透明的大水缸养在客厅里
石头纹理错落有序,借水穿越
一片广阔的原野,是我安身立命的场所
有房檐后最早开花的那棵老梨树
我常记起和我捡石头的人
他养的石头变成他故乡的模样了吗
他朝圣的雪山,是否已开始落雪
偶然的一天
听说,之前捡石头的地方
早被江水淹没
我开始担心
屋里的这缸石头回不到那个水湾
我也回不到捡石头的那个地方了
这应该
就是宿命
谎 言
月光把寒气引落到
低矮的灌木丛中
高处的树枝躲过一劫
谁会在乎花朵的腹背受敌
说谎的人,面不改色
利剑穿心的疼痛是真实的
其他的都是谎言的托辞
谁敢肯定
那张变形的脸没有毒咒
早在数月前的夜晚
温柔的灵魂已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