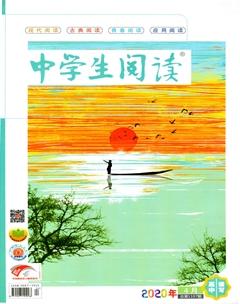黄挎包
认识她的那个日子,是极平常的一个日子。楼下门卫打来电话,说我传的人到了。
“让她上来。”说完,我放下话筒,端坐在办公桌前等候。我要等她上来,然后很严肃地指给她一个我事先摆好的凳子让她坐。这是我的习惯做法,我要在心理上给被传唤人一种压力,好让她觉得不说实话是不行的。
等了半天,不见人上来。
怎么?莫非找不到门?可传票上写得明明白白。正琢磨,有人轻轻敲门。
“进!”我很生硬地说。可是,当门被慢慢地推开时,我不由得打了个愣怔。
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门口站着的竟是个架着双拐的女人。
我端坐着的身子伏向前,紧接着又站起来。
“我找曹乃谦。”
她拾起胳膊,把传票递给我,因呼吸急促,话语断断续续,声音也极微弱。
“噢,对,请进,请进。”
我跨着大步子急急地迎上去,想去搀扶她,可又急急地退至墙边,给她让开了道儿。
她撑着双拐,“咯噔、咯噔”地进了屋。她的左腿是健康的,脚步也正常。短小的右腿则完全悬在空中,随着步子一下一下地晃悠。
“请坐,请坐。”
我又跨着大步子急急跟了上去,想搀扶她,可又没上手,退至一旁。
她很费事地坐下,将双拐并在一起靠在怀里。虽然她努力控制着不出声,但从胸脯的一起一伏和微微圆张着的嘴,仍能看出她还在急促地喘着气。不用问,这种状况是四层楼的六七十级台阶造成的。
当她偷偷地看腕上的手表时,我才想起把她传唤来是为了询问有关她丈夫的情况。
可是,说老实话,我实在是没心思问什么了。
早知道这样,我该主动去家里找她。
就怪她涉嫌犯罪的丈夫,他怎么不说清妻子是个残疾人呢?我只知道她是个23岁的年轻人,没工作,有的是空闲时间,所以我才把她传唤来。
案情进展很顺利。她丈夫被刑事拘留了。
“去搜搜家,说不准还能发现点什么新线索。”分管局长说。
当时,天已经很黑了。她家是常见的排房格局,独门独户的一个小院儿。
听到有人敲门,她在屋里很响亮地应答了一声,随后就“咯噔、咯噔”地出了院,边走边叫着她丈夫的名字。我能听出,那叫声里有种期盼如愿的愉快,有种喜出望外的激动。到了当院,她才意识到并不是丈夫回来了,她才停下脚步“谁们?谁们?”地问。那声音微弱、颤抖,分明有种失望的悲哀在里面。
“是不是我的男人回不来了?”当我们进了屋,她看着我问。
她从我的沉默里似乎知道自己的担心已是事实。她跌坐在锅台上,左臂的拐杖“吧嗒”一声摔倒在地上。
她哭了。
她默默地哭着,任一串串的泪珠往下滴落,也不去擦一擦。
炕頭上,棉花绒毯围着个不足半岁的小娃娃。婴儿不懂母亲的痛苦,举起胳膊伸探着。昏暗的灯光摇曳着模糊的人影。
我把拐杖扶起来,轻轻给她靠在身旁。
搜查完该她签字时,她握笔的手在不住地哆嗦。捺手印时,怕模糊了指纹,我捏住她的食指帮着捺。可是,当我接触到她那冰凉抖动的指头时,我的手居然也不由得抖了起来。
那天夜里,我一个接一个地做噩梦。早晨醒来,头脑昏昏。夜里梦魇的惊悸还没有消除,我又发现我的黄挎包找不到了。那里面不仅装着头天的搜查手续,还装着手铐和记录着半年来工作情况的笔记本。天哪!这要是真丢了,少说也得给我个记大过的处分。
细细地回忆一下,我才想起那黄挎包仍旧挂在她家的衣帽钩上。
我赶快骑车向她家猛劲儿地蹬,可是她家的院门上着大铁锁。
顾不得许多了,我从墙头跳进院里,趴在玻璃上一看,糟糕!衣帽钩上并没有
我的黄挎包。
她给扔了?等我来取?还是给藏起来,等着敲我的竹杠?不,不会的。我摇摇头。
难道她?对!她一准是到公安局给我送黄挎包去了。我骑车向公安局猛蹬。
她架着双拐,在四楼楼道口旁靠墙站着。看见我,她那焦急的神色换上笑容。她左右看看,见两旁没人,便打开挂在左拐上的黑提兜,里面是我的那个要命的黄挎包。
“看看丢什么没?政府的事,重要。”她说。
她向我道别后,便撑起双拐走了。
我木呆呆地立在原地,听任她那双拐“咯噔、咯噔、咯噔”地狠狠敲击在我的心上。
(选自2019年12月18日《检察日报》,有改动)
阅读点击
文中的“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请概括其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