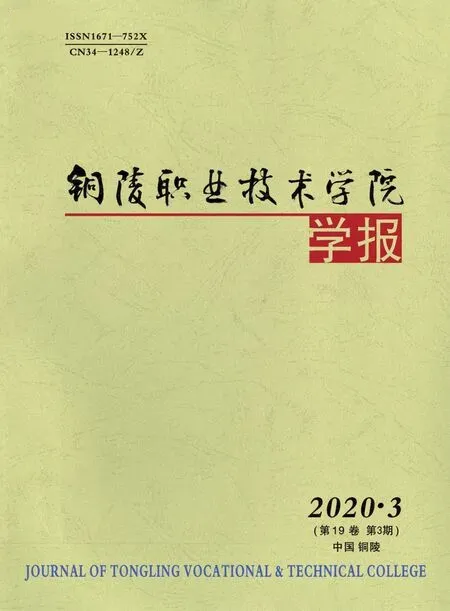张大千仕女人物画中的虚境营造
陈小平,赵晓洁
(内江职业技术学院,四川 内江 641100)
关于 “虚境”,清代方士庶在 《天慵庵随笔》里说:“山川草木,造化自然,此实境也,因心造境,以手运心,此虚境也。虚而为实,是在笔墨有无间,——故古人笔墨具此山苍树秀,水活石润,于天地之外,别构一种灵奇。”[1]这几句话蕴含着中国画创作的精髓,具体可从以下方面理解:一,绘画以“虚境”作为审美追求。因“虚境”借“以手运心而就”,包括作画之情感、思想及精神旨趣;二,“虚而为实”,亦即将情感、思想和精神旨趣器赋于“造化自然”,通过比拟、象征、借喻之法,使画中之实境与主观生命情调交融互渗,获得天地之外的‘灵境’。换言之,心灵之“虚境”须通过描绘“实境”来表达。三,“别够一种灵奇”之法即“虚境营造”之法。“境”是“‘象’和‘象外’虚空的统一。”[6]通过“象”来表达“象外”意,“象”是画中实景表达出的现象,由此现象引领观者进入画境之无限的本体意义,故而“虚境”亦是蕴含着“境”的“象”。 “营造虚境”即是营造有“境”之“象”和“象外”之无限远意。
张大千仕女人物画,在表达“象”和“象外”之无限远意的“虚境”过程中,通过其独居匠心、别具一格的实境写照,充分展现他意趣高雅、形神兼备、构思独特、笔墨精湛、独具风格的综合艺术形态,这与其所践行的艺术思想分不开,笔者尝试以 “虚境营造”的角度,从审美追求、形神独运、主题配裁、道技锤锻、遗世避俗等方面,粗析张大千人物画独特的审美意趣及创作辑要,以求更好的领略其艺术思想及创作程式。
一、审美追求
张大千对仕女人物画有独特之审美追求,有独到之表现方式及处理手法,形成了独特的“张式”仕女画风。其言:“凡画,人物最上,山水次之。而画人物又以人物器宇为上,要能绘出人物之崇高气质,所谓理想中之典型。”[2]“仕女容貌与服饰,要高贵明丽,丰艳窈窕,各极其态;更要娴静娟好,有林下风度,遗世而独立之势。”[2]张大千仕女画“理想典型”的崇高气质以及“林下风度”,正是方士庶所言“于天地之外,别构一种灵奇。” 其主张“画仕女要文而不弱”,[2]特别是敦煌之行后的仕女人物画打破了明清以来,襟弱仕女之形象。[4]其仕女人物很少表现明清时期宫廷园榭式的苑体特征,而是配以富有精神象征的桐、竹、梅、柳,表现出富有诗意的生命意趣。这也正是“张式”仕女人物画最为独特的审美意蕴。
二、形神独运
张大千仕女画对形神兼备之索求,可谓独运匠心。其言:“作画,首先要了解物理,体会物情、观察物态。了解这三点后,画出的画才能形态逼真,神韵生动而跃然纸上。”又言:“画背面,那就要在腰背间,着意传她袅娜的仪态。”[2]1945年所绘《蕉荫仕女图》,[7]画一仕女背影,执扇逶迤而去。首先,此画用“虚”灵的笔墨表现了衣着在裙摆、袖口和红色腰绳上的飘逸动势,而这些动势均由腰间传出,间接表现了背影之袅娜仪态。其次,在人物形象上,头部朝向画之正后方,团扇朝画之右后方,让人物上半身朝右,腰身及左胯则朝向画之左前方,带着衣袖、裙摆及红色腰绳款款向前,有种步履向前,腰胯先动之意,直接表现了背面人物之袅娜仪态。画中对婀娜之态的美妙的表达,是通过对腰胯之“力”在头部、群摆、袖口及腰绳中传动应带而得到有效表达,此中 “力的传动所导致的动态就是须要了解的物理。画中人物之袅娜仪态蕴含着仕女柔美、静穆、楚楚动人、轻盈漫步的理想性格特征,反应的是作者对仕女“幽闲、贞静、妖娆艳治”之美的理想期许,作者欲在图中充分表达美的理想,非仔细观察“物态”特征而不能。例如,仕女肩部用笔圆润雅丽,裙摆薄纱用笔行云流水,移顿飞凌都是准确表达物态的有力写照。画中最为点睛传神之处,在团扇和微侧的头部面向而照,将观者之眼、之心定格在对仕女面部的期待上,这正是作者体会“物情”之至高境界,这境界较之“犹抱琵芭半遮面”犹有过之。关于仕女人物画面部描写,张大千的分析总结也显得精到之极,由额至下颌之“七不得”甚为经典,是其“三物”理论的再次展现。其云:“凸不得、凹不得、塌不得、撅不得、缩不得、丰不得、削不得”,[2]“凸不得”是指仕女额头不能凸,额头凸显老态,仕女额头须饱满柔和;“凹不得”是指仕女眼眶不能凹陷,否则憔悴无神;“塌不得”是指鼻梁鼻头需坚挺饱满;“撅不得”是指仕女嘴巴不能上翘,否则无贞静之态;“缩不得”是指下颌不能后缩;“丰不得、削不得”均指画下颌不能过胖或者过瘦,过胖显得臃肿,过瘦则少之典雅。
张大千以“情”为意蕴,以“理”为逻辑,以“态”为表达,奠定了其艺术思想的理论基础,资其仕女人物画情景交融,独运形神,达成理想审美意境。其对人物之体察感受,妙悟入微,使其仕女人物画比之历代仕女之艳丽华贵,又多了几分恬静适意,娴雅虚淡之美,与其所谋“林下风度,遗世独立、超然物外”之审美境界相得益彰。

张大千 蕉荫仕女图
三、主题配裁
关于仕女人物画之主题配裁,张大千认为画仕女唯“梧桐、竹子、梅花、柳树、芭蕉、太湖石、荷塘、红栏、绿茵”。[2]诸类品物含高洁、忠贞、孤寂、俊雅、轻柔、清逸之喻,作为仕女之配景更能凸显女性精神气质特征,强化作者理想中的典型形象。以梧桐为例,梧桐在传统文化中有其特有的意向指趣,因其为制作古琴之良材,而有“良材”之喻,雍陶写《孤桐》:“疏桐余一干,风雨日萧条。岁晚琴材老,天寒桂叶凋。已悲根半死,复恐尾全焦。幸在龙门下,知音肯寂寥。”更是表达了惜材与知音的意向。又因梧桐雌雄同株,故唐代有诗曰“梧桐相待老,鸳鸯会双死”以表同生共死,忠贞不渝的爱情。王安石写:“天资直森森,孤高几百寻。凌霄不屈己,得地本虚心。”以喻其高洁孤寂,不入时流的品格。又比如竹子象征着虚怀含蓄,内敛恬静的精神气质。梅花有不与百花争芬芳和凌霜傲雪的品质。柳树通常用以表达别离和迎春的情景。芭蕉有离愁之情,荷叶有婷婷之资,荷花有圣洁之性。至于红栏在宋词中犹表相思之意。在《携梅仕女图》配景为梧桐、篁竹;《摩登仕女图》配竹石、垂柳;《艳秋娇态》配芭蕉。[7]总之,张大千对仕女人物画配景的特殊要求和选取,绝不是想当然随意搭配,而是物与人审美气质上的相互生发,塑造物我合一的整体体验。如此配裁亦警示画者须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准把握,对传统美学意义须深入思辨,方才有完整塑造理想仕女形象意蕴的可能。其言仕女“切不可用松、杉、柏等树。”意将松、杉、柏等苍劲雄强之物归纳为男性气概之象征,爰非仕女绘画之配景耳。因此,作者从主题配裁上的严格要求,确为营造其仕女人物画中理想的虚境意象,准确表达作者理想审美意蕴。
四、道技锤锻
张大千在《谈画工笔山水》有云:“画要有气韵,一落板滞,就不入鉴赏。之中要点,不仅要把画面宾主虚实,前后远近弄清楚,而且要在用笔、用色、用水上灵活生动。”[2]此语颇为朴实明白,金针度人,虽针对画山水而言,不惟山水画适之,更可视为画之总纲,故画人物无不遵循此则。有“气韵”即是画要有“境界”,要使画面有“象外之象”,一落板滞更为下乘,无“境”可言。“宾主虚实,前后远近弄清楚”即是谓画之“构图”,“六法”之中所谓“经营位置”。中国画之境界深远,见于画中之可视之象,更见于画中不可视之象,即画中“留白”。老子云“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白”是不可视之思想境界,黑是可视之行为举止,“式”为道之运行方式。在道家土壤里生长的中国画无处不体现着道家哲理。故而中国画之留白直指不可视之象——虚境之处,通常给人意境之赏。在张大千所绘仕女画中,有这样一种典型的构图形式“仕女人物置于画之中央,背面配以芭蕉、柳树、竹石或荷叶等,仕女脚下一片虚空,裙裳下摆及鞋脚均不画出,或脚下配以腾云,所绘仕女仿佛从画中轻踏云雾飘然而至,如面飞仙。”如 《摩登仕女图》、《天女散花》、《柳荫仕女图》、《携梅仕女图》、《芭蕉仕女图》等。[7]此种构图形式为张大千仕女人物画之虚境营造一大特点,于历代仕女绘画群萃中独树一帜。之外“用笔、用色、用水上灵活生动”,亦即笔墨、色彩技巧须经锤锻,娴熟灵活方得气韵生动神妙。阴阳相合,虚实相生之法,贵为笔墨锤锻之妙悟。笔墨有而为实,无而为虚;多而为实,少而为虚;浓而为实,淡而为虚;沉着而为实,轻浮而为虚;显而为实,隐而为虚。虚实之间,相生克而成运转,相运转方成统一,相揖让各显其风,相倾缠互表其情。其仕女画用笔以中锋取势,侧锋取妍,多率意写出,笔笔相生发,环环相连接,真放而精微,意全而生动。张大千《课图稿》有言:“用笔拿中锋做中干,侧锋去帮助它。中锋把体势建立起来,侧锋来增加它的意趣。中锋要质直,侧锋要姿媚。”[5]质直重在写出,姿媚贵在灵动。如《依竹仕女图》中表现肩膀、左胯及肘部等关节部位,着重表现衣物贴身部位用中锋之笔质直写出,于裙摆及袖口处用侧锋取其灵动姿媚之态。再配以浓淡相宜,虚实相生,明润厚重之用墨之法,使整幅绘画清丽自然,幽然典雅,出乎凡林。
张大千绘画技法承袭古人,其对传统笔墨、色彩、胶水有深入的研究和锤炼,也有使其画面具有亮、洁、明、艳等特点,光彩夺目的气象氛围是张大千绘画中的显著特点,也是其仕女人物画中明丽照人,亲目迩心之气韵精神。
五、遗世避俗
张大千强调在绘画技法上要脱俗。张大千的内心世界是高雅的,常将自己画成高士形象于林下或于云间,其对脱俗之求固然,犹言所画“仕女必须脱俗,有飘飘然之意。”[3]张大千绘画思想受石涛影响甚深,石涛主张“笔墨当随时代”,其言“石涛的画,无一不是来自生活而法度严谨,无一不新颖奇妙而自辟蹊径。”[3]纵观张大千仕女人物画,除临摹仿拟之作,大多仕女形象均与生活人物息息相关,均是生活中女性人物之升华,因此在人物面部及发饰形态上无不闪烁出晚清民国新思想的光芒。在人物姿态描绘上已超脱封建社会女性之束缚压抑而带有的深闺姿态,转而为大方、自信、娴静致远的精神风貌。可见张大千仕女人物画源于生活之美,故其必然探求高于生活之法,其训诫唯读书才能达成民族精神所向之文化境界。故其认为“趋利谄媚者,太俗气;草率急就者太浮气;因袭相陈者太匠气;若将生活中丑行诸笔墨,肆意渲染,更是秽气。”[3]实际上对于绘画而言,“浮气”、“匠气”、“秽气” 都是不高雅的,张大千在此将“趋利献媚”定义为俗气,是对仕女柔弱形象的批判和否定。“草率急就”心意不诚,达不到真、善、美的境界。“因袭相陈”者,其艺术缺乏生活中的鲜活感,更无创造美的能力,而将生活中的“丑行”当作艺术素材,其从根本上便落俗流,纵观张大千仕女人物画从无市侩之气。另外对文化内涵的萃取,也是其脱俗的一大法门。其谓 “作画如欲脱俗气、洗浮气、除匠气,第一是读书,第二是多读书,第三是须有系统、有选择的读书。”[3]故观张大千仕女蕴含清丽文雅,亭亭玉立,涤尽纤尘,确有仕人风神之感,又其精神风韵独卓,含丝丝静穆之情,无不令人有孤赏之意。其表现技法汲古而不泥古,笔墨语言风格统一,独居一宇。人物形象于“物理、物态、物情”深会敏悟,严谨思虑,更无浊世丑行之秽,可见其艺志精诚。故所绘仕女难寻诸家之痕迹,能绝因袭相陈而立新意。
据此,“虚境”作为中国画艺术特有的追寻境域,是几千年来民族精神之凝聚,是游艺者于人生体验感悟中闪耀出的灵光,是山重水复艰辛跋涉出的理想目标。张大千仕女人物画之“虚境”凝结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代表了其个人思想境界及艺术理想之追求。“营造”是对技巧的探求实践,是对生活感悟中的搜妙入微,更是对民族文化意境美学如琢如磨的纯化和升华。而对于美的虚境表达,“营造”更是情感的注入,是精神和情操滋育出的人格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