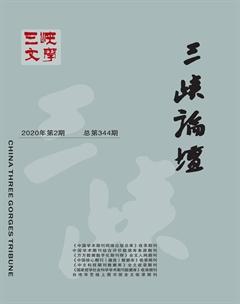由《曾国藩教子书》看曾国藩的科举思想
顾瑞雪
摘 要:作为晚清最具影响力的名臣大儒,曾国藩在教子方面也很值得称道。细绎曾氏的教子内容与方法,可以见出对举业的重视在曾氏的教育中占了不小的比重。从曾氏为子侄们荐读的书目,到指点他们如何学做八股文、习字,再到日常事无巨细的点拔和督责,均可见出科举在那个时代的真实情形。通过这一个案的考察,可知晚清科举制度的改革在19世纪中期仍迟迟未发,处于沉寂状态。
关键词:曾国藩;教子;科举思想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20)02-0092-06
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往往可由这个时代的先进分子身上体现出来。如果要探究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科举变化,曾国藩无疑是一个最佳考察人选。对于科举制度的改革,曾国藩未曾有一毫建言,这也就是说,曾氏并不认为科举有改革的必要。相反地,他从自己的经验体会出发,对现行的科举制度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与支持。从他的家书、家训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时时督责二子曾纪泽、曾纪鸿要认真读书,并充分準备乡试考试。他经常与子侄辈谈论如何练字、读经、作诗、备考等话题。他为子侄辈延请名师,这当然是为了他们的成长,但同时也希望他们能够在科考中获隽。因此,考察时代文化名人曾国藩对后辈的训导教育,能够较为真实地反映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科举制度的真实样态。
曾国藩出生于晚清一个耕读世家。他六岁入塾,八岁能读《四书》,诵五经。二十一岁考取秀才,二十三岁中乡试举人。二十七岁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从科举经历来看,虽然曾国藩亦曾在乡试、殿试中失利,但总的来说还算顺利,不到三十岁就进入翰林院,为踏入仕途做了良好的准备。相较之下,曾国藩的两个儿子曾纪泽、曾纪鸿的科举之路可就没有这么顺畅了。当然这并不是说曾氏两兄弟因为未能科考得中而变得不优秀。
曾国藩教育子侄时,反复审明惟愿后代子孙做明理的读书君子,不要从军,亦不必作官,这源于曾氏本人带兵打仗的亲身体会。他为纪泽、纪鸿、陈婿等人延师,桐城派古文大师吴汝纶之父吴元甲、晚清文学家莫友芝、知名学者邓寅皆先生等人,都曾任过曾家的西席。为促成子弟的成长,曾国藩尽最大可能为他们提供了最好的条件和最佳的指导。
作为一个科举过来人,曾国藩不仅在心理、精神层面给予子侄以鼓励和支持,还亲自就学习备考等方面与子侄进行切磋。生在科举时代,参加科考则成了读书士子的安身立命途径。纪泽乡试屡遭挫折后无意科举,曾国藩坦然接受这一事实,尊重纪泽的选择,并对他抗心希古的志向颇为激赏。但曾氏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次子纪鸿的要求。当听说纪鸿在县试中考了第一名,曾国藩非常高兴,并称许纪鸿的文章“清润大方”。[1]101当纪鸿问父亲是否应去科考时,曾国藩说:“尔既作秀才,凡岁考、科考,均应前往入场。此朝廷之功令,士子之职业也。”[1]125曾氏将应试科举作为读书士子的份内之务,这表明了他对科举的态度。在家书、家训中,曾国藩对纪泽、纪鸿等后辈说到了该读哪些书、如何积累词藻素材,如何做八股文,如何提高书写的能力等问题。下面谨就这几个方面简述之。
一、如何选择应读之书
经籍类是科举士子首要必读之书。咸丰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曾国藩写信给曾纪泽,叙及士子应读之书。纪泽向父亲汇报自己已经看完了“五经”。曾氏认为,除“五经”应熟记外,“十三经”中其他六经,即《周礼》《仪礼》《尔雅》《孝经》《公羊》《谷梁》诸书,均应请塾师口授一遍,以览知其大概。[1]26
史籍类中,曾国藩认为《史记》《汉书》均应熟读。他还不止一次地说到自己对这两部历史典籍的嗜爱。对读史的次序,他也加以指点。同治五年八月初三日,他信谕纪泽、纪鸿:“尔拟于《明史》看毕,重看《通鉴》,即可便看王船山之《读通鉴论》。尔或间作史论,或作咏史诗。惟有所作,则心自易入,史亦易熟,否则难记也。”[1]18
诸子籍中,曾氏比较推重《庄子》《孙武子》。曾氏曾说他嗜《庄》、韩文、《史》《汉》成癖,恨不能一一诂释笺疏,穷力讨治。[1]180
集部籍中,曾氏荐读《文选》和韩文。之所以喜爱韩文,乃出于爱其雄浑刚健的气势。
除此外,曾氏还建议二子应阅读《通典》、《说文解字》《方舆纪要》,姚鼐所辑《古文辞类纂》和他本人所编辑的《十八家诗钞》。
在曾氏推荐阅读的这些书中,经、史、子、集以及《说文》等训诂之学,均有涉猎。曾氏与纪泽交流读书经验,认为:“凡汉人传注、唐人之疏,其恶处在确守故训,失之穿凿;其好处在确守故训,不参私见。”[1]27并进一步对汉学、宋学之差异进行了解析:“朱子《集传》,一扫旧障,专在涵泳神味,虚而与之委蛇。然如《郑风》诸什,注疏以为皆刺忽者,固非;朱子以为皆淫奔者,亦未必是。”[1]27提醒纪泽读书时不妨以理性待之,“尔有志读书,不必别标汉学之名目,而不可不一窥数君子之门径。”[1]40取其合理处,弃其虚妄不实处。清代自乾嘉以来汉学日臻鼎盛,但曾国藩却无意于右袒任何一方,而是主张调和汉、宋。他同时告诉纪泽,治经时,无论看注疏,还是看宋传,总宜虚心求之。认为惬于心意者,则以朱笔标出;有疑问时,则将其收录于另一册本,将自己的疑义附记于此,哪怕仅有片言只语,倘随着读书能力的提高,知识积累愈加丰富,所疑之惑便可渐渐解之。清代著名考据家高邮王念孙父子即通过此种札记的方法卓然成为大家,曾氏勉励纪泽也应学习王念孙父子的朴学精神。接着,他又推荐纪泽阅读王引之的《经义述闻》《经传释词》,王念孙的《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等,亦须阅读。[1]33-34
曾氏曾就“看”与“读”之区别加以述之:“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1]19他还将之比方为富家之慎守与获利:看书就像在外贸易,能获得三倍;读书则如在家慎守,不会轻易花费。若以兵家战争作比,看书则像攻城略地,开疆拓土;读书如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1]19他还认为读书须能“虚心涵泳,切己体察”,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比方,说“涵”如春雨滋润万物,渠水灌溉稻田;“泳”则如鱼之游水,人之濯足。纪泽之所以不能深入体察经义学问之内涵,原因即在于缺乏“涵泳”、“体察”的工夫。切实成为读书君子,乃曾国藩对后辈子孙的期待。其殷殷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如果对清代科舉准备用书加以对照,可知曾国藩给子侄所荐读之书,乃是科举考试获隽的必备之书。清代末科探花商衍鎏曾撰《科举考试的回忆》一文,对自己的科途加以回顾。商氏自言六岁开蒙,读《三字经》《千字文》。这是幼童识字之基础。能背诵及认识大部分字后,开始读《四书》。《四书》须依朱熹之注,读正文时,亦应读朱注。塾师将新的内容口授一遍,学生即自己记诵,同时温习旧书。因“四书”是考试基础,三篇八股文题目的出处所在,故全部内容须从头至尾背诵至滚瓜烂熟方止。然后是读“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仍需全背正文,但无须背注。这是为科举考试四篇经文而备。此外还须读《孝经》《公羊传》《谷梁传》《周礼》《尔雅》,以及五、七言唐宋小诗、《声律启蒙》等,学作对句,学调平仄。还须读十七史蒙本,每每四字一句,句句有史实典故,这既有助于少年儿童了解历史,又可增加对典故的认识,可谓一举两得。十二岁后,始学作八股文、诗、赋、策论等。此时不但要读八股文、古文、律赋、文选之类,并且要读史书如《通鉴》、“四史”,子书如《庄》《老》《韩非》等各种书籍,俾腹中充实,以备作文之驱遣。[2]421-423
虽曾国藩不希望子孙后辈读死书,成为古板的学究或狭隘的文人,但纪泽、纪鸿获隽秀才后,曾氏对二子读书方面的指导,亦大有意于科举,则毋庸置疑。为培养二子的“时务经济”之才,曾氏要求二子须熟读《文献通考》,并会查阅会典,熟习文物制度,典章法则。曾国藩曾批点过《文献通考》中的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刑制、舆地等门。同治四年十一月十八日,他写信给纪泽、纪鸿,说自己在核改水师章程,让纪泽翻阅《会典》,查出千总、把总可各领多少养廉银。曾氏提示纪泽现行经制可查阅《会典》,因革之制则可查《事例》;对于提督之官何时改为武职,曾氏建议纪泽或可查《会典》,或可询之凌晓岚、张肃山等。这些问题可使纪泽对清代养廉制度的因革和文武官的沿革等职官文化体制,较一般人有更加透彻深入的了解。
曾氏曾将自己不懂天文、算学作为平生之一耻,希望纪泽、纪鸿能够有所补救。家书中谈及推步算学纵难通晓,但认识恒星五纬并非难事。十七史中各个时期的《天文志》和《五礼通考》中所辑录的《观象授时》,皆可做为学习资料。“每夜认明恒星二三座,不过数月,可毕识矣。”[1]24为使策论写得充实有光辉,曾氏曾要求纪鸿、瑞侄“可将《文献通考序》二十五篇读熟,限五十日读毕。”[1]176
曾国藩要求纪泽兄弟不仅要通训诂,还要善辞章,天文地理,典例文物,无不涉猎,这是典型的“通才”式君子教育。曾氏本人一生信奉儒学,他希望家中子弟亦能博学多识,无囿一方,成为于国于家大有用的通儒。
二、如何学做制艺
作为明清科举考试的程式之文,学做八股文是每一位有志于参加科试的读书士子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如何写好八股文是一门大学问,直接关系到考生举业的成败。曾氏认为首先应端正做八股文的态度,不可等闲视之,“制艺一道,亦须认真用功。”[1]175要虚心向八股文高手如邓瀛、李次青、黄泽生、胡东谷等请教。他听精于举业者说陕西路德的《仁在堂稿》及所选“仁在堂”试帖、律赋、课艺无不当行本色,宜古宜今,陕地近三十年来科第中人无人不出于路德之门,于是建议仍在为科举攻读的纪鸿、瑞侄“须买《仁在堂全稿》《柽华馆试帖》悉心揣摩。[1]38
曾国藩不止一次地跟纪泽、纪鸿谈到畅行于清代的一部家训——《聪训斋语》。《聪训斋语》作者是乾隆时期大学士张英。“家训”中对子弟的教育培养主要体现在立品、读书、养身和择友四端,在此仅就“读书”方面的内容略加述之。张英认为,好读书、精举业是一个人乃至一个家族振兴的契机所在。“读书因所以取科名,继家声,然亦使人敬重。”“读书者不贱,不专为场屋进退而言也。”对举业来说,时文的写作当然是十分重要的。《聪训斋语》认为“时文以多作为主,则工拙自知,才思自出,蹊径自熟,气体自纯”。选精纯条畅、有气局词华者数十篇至百篇,熟读涵蕴,揣摩其作文之精妙,日久则神明自与浑化。那么,什么样的时文才能算作好的时文?张英认为惟有那些理明词畅、气足机圆的时文才值得一再吟诵、揣摩。“揣摩”之道,在于文章的思路、结构、格局、词藻等方面。[3]328
在诫子家书中,曾国藩也屡屡提及文章和诗歌的“气”。《聪训斋语》也提到制艺时文的“气”。那么,什么是“气”呢?简单来说,“气”即是文章的气势。曾国藩认为“气”乃是为文的第一要义:“尔问文中雄奇之道。雄奇以行气为上,造句次之,选字又次之。然未有字不古雅而句能古雅,句不古雅而气能古雅者。亦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句不雄奇而气能雄奇者。是文章之雄奇,其精处在行气。”[1]65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曾氏与纪泽谈作诗:“尔七古诗,气清而词亦称,余阅之欣慰。凡作诗最讲究声调……尔欲作五古七古,须熟读五古七古各数十篇,先之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为诗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1]2此处讲的是诗歌之“气”。同治四年七月初三日,曾氏又谕二子:“尔当兼在气势上用功,无徒在揣摩上用功。大约偶句多,单句少,段落多,分股少。莫拘场屋之格式,短或三五百字,长或八九百字千馀字,皆无不可。虽系《四书》题,或用后世之史事,或论目今之时务,亦无不可。总须将气势展得开,笔仗使得强,乃不至于束缚拘滞,愈紧愈呆。”[1]144此处讲的是八股制艺文之“气”。无论作诗作文,均应在“气”上下功夫。
曾氏认为文章的雄奇,其“精处”体现在“行气”的奥妙,其“粗处”则全在造句选字。他自言自己好古人雄奇之文,以韩愈为第一,扬雄次之,“二公之行气,本之天授。至于人事之精能,昌黎则造句工夫极多,子云则选字功夫居多。”[1]65韩愈诗歌文章中的奇崛之气,“皆光如皎日,响如春霖”,“于奇崛中迸出声光”,原因即在于意义层出、笔仗雄拔。“气”首先在于作者气质个性的养成,当然,胸中之学识与丘壑也非常重要。同治元年八月初四,曾氏信谕纪泽:
余近年颇识古人文章门径,而在军鲜暇,未尝偶作,一吐胸中之奇。尔若能解《汉书》之训诂,参以《庄子》之诙诡,则余愿偿矣。至行气为文章第一义,卿、云之跌宕,昌黎之倔强,尤为行气不易之法,尔宜先于韩公倔强处揣摩一番。[1]105
这里仍说到“揣摩”的方法。不过入门既高,途径正确,所得效果也不会太差。曾氏认为无论是赋,还是古文,抑或时文,文章的雄奇之气可归源于“造句选字”。曾氏认为这方面同样可以训练以达致,分类摘钞作文词藻即是最直接简易的方法:
尔作时文,宜先讲词藻。欲求词藻富丽,不可不分类钞撮体面话头。近世文人如袁简斋、赵瓯北、吴谷人,皆有手钞词藻小本。此众人所共知者……昌黎之记事提要,纂言钩玄,亦系分类手钞小册也。[1]41此段话乃是咸丰九年五月初四日针对纪泽去岁乡试落败的主要原因所发。
文章“选词造句”可分类钞录;其他方面的知识储备,如经籍典章类,亦可通过“分大纲子目”的方式将其条分楼析,以便于记忆考核:
尔此次复信,即将所分之类开列目录,附禀寄来。分大纲子目,如伦纪类为大纲,则君臣、父子、兄弟为子目;王道类为大纲,则井田、学校为子目。此外各门可以类推。尔曾看过《说文》、《经义述闻》,二书中可钞者多。此外如江慎修之《类腋》及《子史精华》《渊鉴类函》,则可钞者尤多矣,尔试为之。[1]41
勤奋攻读自是一义,学习仍有技巧可寻。这种“分类钞撮”法,将学习内容进行有效分类,比起塞耳闭目一味死用功者,学习效率自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曾氏将其比为“科名之要道,学问之捷径”。对于好的时文范本(比如路德所编八股文),他也主张应手钞至能背诵。
除此外,曾氏非常重视对《文选》的学习。《文选》是一部综辑辞采,错比文华,讲究词藻华美、声律和谐,对偶用事切当的诗文总集,文学性很强。鉴于纪泽文笔的枯涩之弊,曾国藩建议他多读诵《文选》。他曾对纪泽说:“尔明春将胡刻《文选》细看一遍,一则含英咀华,可医尔笔下枯涩之弊;一则吾熟读此书,可常常教尔也。”[1]32又说:“尔于小学既粗有所见,正好从词章上用功。《说文》看毕之后,可将《文选》细读一过。一面细读,一面钞记,一面作文以仿效之。凡奇僻之字,雅故之訓,不手钞则不能记,不摹仿则不惯用。”[1]98并建议将《文选》中最惬意者,如《两都赋》《芜城赋》《九辨》《解嘲》《哀江南赋》等名篇,均可手钞、熟读,相互验视背诵。
方法要点全部了解后,曾氏对子侄的课业督责亦循序展开。纪泽年纪渐长,须习学八股文以应科考。曾国藩写信对他说:
沅叔及寅皆先生望尔作四书文,极为勤恳。余念尔庚申、辛酉两科场,文章亦不可太丑,惹人笑话。尔自明年正月起,每月作四书文三篇,俱由家信内封营中。此外或作得诗赋论策,亦即寄呈。[1]32
次年,曾氏又要求纪泽每月作一赋,一古文,一时文,交长夫带至营中检视。纪泽绝意科途后,曾氏对次子纪鸿的督责提上日程。同治五年正月二十四日,曾氏在徐州,信谕纪鸿:
尔出外二年有奇,诗文全无长进。明年乡试,不可不认真讲求八股试帖。……李申夫于八股试帖最善讲说,据渠论及,不过半年,即可使听者欢欣鼓舞,机趣洋溢而不能自已。尔到营后,弃去一切外事,即看鉴、临帖、算学等,皆当辍舍,专在八股试帖上讲求。[1]168
余所责尔之功课,并无多事,每日习字一百,阅《通鉴》五页,诵熟书一千字(或经书,或古文、古诗,或八股试帖,从前读书即为熟书,总以能背诵为止,总宜高声朗诵)。三、八日作一文一诗。此课极简,每日不过两个时辰,即可完毕,而看、读、写、作四者俱全,馀则听尔自为主张可也。[1]167
当纪鸿试帖诗作得不错时,曾国藩及时给予鼓励赞许:“鸿儿试帖,大方而有清气,易于造就。”[1]115纪鸿能够读出表奏中的结构章法,曾国藩称赞他善于领会。曾氏一直勉励子弟们作文章定须以气象峥嵘、蓬勃向上为贵。[1]143对子弟们的点滴进步,曾氏都予以热情的肯定;但对其不足之处,亦直言指出:“两人气象俱光昌,有发达之概。惟思路未开。作文以思路宏开为必发之品。意义层出不穷,宏开之谓也。”[1]180
三、如何书写
书写在科举考试中一直倍受重视。宋代就已经出现了方正、光洁、乌黑、大小等齐的官场用书体。明代永乐年间翰林学士沈度因其书法秀润华美,正雅圆融,深受成祖朱棣赏识,因而形成了盛极一时的“台阁体”书法。清代则更进一步发展为“馆阁体”,其特点是乌、方、光、大,突出的是楷书的共性,即规范、美观、整洁、大方,以体现博大的气象,笔势的恢弘。这势必要求读书士子从小就必须苦练“基本功”,以达到字体的光圆方正。曾国藩除要求自己每天习字,对子侄的督促也从未放松过。虽大部分时间身在军营,但他要求子侄辈须将每日习字读书的课业交人带至营中,亲自批阅检视,并加以圈点评语。他建议练字须由欧、虞、颜、柳四家入手,入门须正,才有可能取得一定的成就。最好的书家笔划结构,一定要“珠圆玉润”,方能显其气象。[1]59他叮嘱纪泽看、读、写、作每日都须做,习字无论真行篆隶,切不可间断一日,努力达到既“好”又“快”的效果。[1]19
曾氏告诫子弟们写字须先求圆润匀整,次求敏捷。习惯了既“匀”又“捷”的书写,可以有无穷的受用:以之为学可手钞群书,以之从政则可案无留牍。[1]176习字时,“临”是为了求其神气,“摹”则重在仿其间架结构。为克服纪泽写字笔力太弱的缺点,他建议纪泽可以常摹柳帖,如《玄秘塔》《琅琊碑》《西平碑》各种,或颜体的《郭家庙》等,日临百字,摹百字,以药其病。并要求纪泽将自己每日习字托人夫带至营中。[1]67
曾国藩还具体指导练字时的运笔。咸丰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家书中,他与纪泽论说书写之“中锋”和“偏锋”:“写字之中锋者,用笔尖着纸,古人谓之‘蹲锋,如狮蹲虎蹲犬蹲之象。偏锋者,用笔毫之腹着纸,不倒于左,则倒于右;当将倒未倒之际,一提笔则成蹲锋。”[1]166咸丰九年八月十二日的家书,更是细致入微地对具体笔划运笔进行了切实讲解。
习学书法与其他任何事一样,都会有“瓶颈期”。纪鸿习练柳帖《琅玡碑》,旬日未见长进,心生急躁。曾国藩以自己的经验告诉他,此乃学习成长中必然会经历的过程,不必焦躁;熬过此段时期,便可大有长进:
以后每日习柳字百个,单日以生纸临之,双日以油纸摹之。临帖宜徐,摹帖宜疾,专学其开张处。数月之后,手愈拙,字愈丑,意兴愈低,所谓“困”也。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习字,凡事皆有极困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1]166
这不仅是从书法习字上对子侄的勉励,同时也是对后辈的一种人格力量的培养。张英在《聪训斋语》中,也是毫不例外地对字的间架结构、持恒练习等方面进行了强调。如应择古人之佳帖或时人墨迹与己笔路相近者专心学之;楷书虽以端庄严肃为尚,然须去矜束拘迫之态,方有雍容和愉之象;建议子孙后辈“每日明窗净几,笔墨精良,以白奏本纸临四五百字,持恒练习,必能收效甚著”;习字须戒除急躁,“学字忌飞动草率,大小不匀,而妄言奇古磊落,终无进步矣”等等,诸多事项,不一而足。
从以上可见出,在曾氏对子侄后辈的教育训导中,科举教育始终是其应有之义。这正如曾氏自己所言:“世家子弟既为秀才,断无不应科场之理。既入科场,恐诗文为同人所笑,断不可不切实用功。”这明白地表达了曾氏对科举考试的态度。当然,他诫敕子弟科试前与州县来往,更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1]130并反复诫斥纪泽、纪鸿在外须以“谦”、“謹”二字为主。“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瞩。临行时教以三戒之首末二条及力去‘傲‘惰二弊,当已牢记之矣。”对即将参加科考的纪鸿(同治三年七月二十四日),曾氏嘱其“十六日出闱,十七、八拜客,十九日即可回家”等等细事,可谓谆谆教诲,尽显慈父之?犊情深。
综观曾国藩教子之书,由咸丰二年(1853)始至同治十年(1871)近二十年间,从未间断。而晚清中国此时正由平定太平天国之乱而渐趋中兴。同治元年(1862),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朝廷封疆大吏已然意识到世界政局给晚清中国所带来的渐趋深远的变化,改变中国人才的知识结构已渐渐成为大势所趋。于是朝廷内以奕?、文祥为代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为代表,开始了以洋务强国的变革。江南制造总局专设了一个译印西学书籍的翻译馆,聘请一些外国传教士,翻译军事、船舶、机械制造等自然科学类书籍,也兼译医学、历史地理、国际公法等方面的著作。在容闳的倡议下,第一批官费出洋生童也开始在欧、美等先进国家学习先进技艺,以“夷”为师,“师夷长技”以富国强兵。然而,传统文化的积习仍以巨大的惯性昭示着它难以改变的力量。即便如先觉先行者曾国藩,在教导子弟时,也仍是秉持着传统儒家观点,希望子孙能由正途出身,做具有通才特质的“君子儒”,而非学有专长的“小人儒”。或许这更能代表传统中国文化教育在那个时代的真实情形。曾氏最后平定洪秀全乱,也几乎全出自于传统思想之功。1864年11月,太平天国之乱平定,曾国藩给朝廷上了一道《粗陈善后事宜折》,其主旨中极其重要的一项,即是在两江范围内全面恢复科举,进行甲子科乡试。曾国藩节省下修建两江总督衙门、江宁布政司、江宁知府等官衙的经费,重修江南贡院,以待读书士子能够顺利参加科举考试。这当然不仅可以笼络江南士子,还可以稳定时局。然而这同时也表明,科举改革的浪潮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远远没有到来。
注 释:
[1](清)曾国藩著、钟叔河选辑:《曾国藩教子书》,岳麓书社,2002年。
[2]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
[3](清)张英《聪训斋语》:“一题入手,先讲求书理极透澈,然后布格遣词,须语语有着落。勿作影响语,勿作艰涩语,勿作累赘语,勿作雷同语。凡文中鲜亮出色之句,谓之调,调有高低。疏密相间,繁简得宜处,谓之格。此等处最宜理会。”“所谓理会者,读一篇则先看其一篇之格,再味其一股之格,出落 之次第,讲题之发挥,前后竖义之浅深,词调之华美,诵之极其熟,味之极其精。”徐寒主编:《中华传世家训》,中国书店,2010年。
责任编辑:杨军会
文字校对:郭 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