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纸砚
●停 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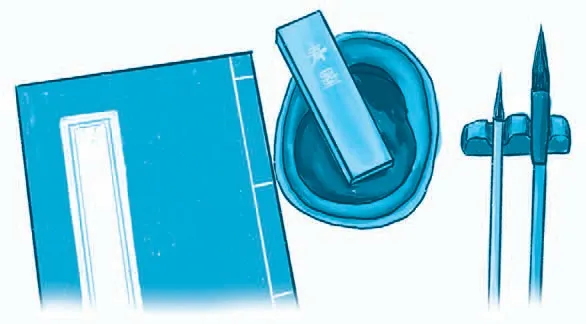
笔
入冬之后,进山林,选一竹子,削削剪剪。又收取雏兔几许毫毛,捆实,沾湿,接续。初见之时,笔的样子也不过和兔子尾巴,相差无几。
我想最开始的笔该是这样制作出来的吧!
陡然间,置于诗人之手,便成了江南诗句里的蝇头小字,跳跃着蹦跶着,徐徐流淌着诗人胸中之沟壑,骨骼之间亦然是风骨,肌肉之内横亘着风华。
挥就挥个刀光剑影,运就运个千里快哉风!
张旭估计是最懂笔的,习狂草,笔是最重要的。狂要狂的有格调,手中利剑“笔”要刚柔并济,稳要稳得刚劲有力,柔要柔情似水。
下笔之后,笔尖流淌似游龙戏凤,手握笔杆若绝顶剑客,人剑合一,忘我形于天地。
一阵风吹过,竹林微漾,谁的前世?谁的今生?笑也长歌,悲也长歌。
墨
也不知道是怎样的一株松,才烧出那样黑的烟,且如此浓,浓得秋风都托不动了,所幸还留有黏性,结成串,匍匐着。
黑呀,真黑,黑得黑白分明。遇到水,倒是水墨丹青,遇到江南倒是水墨江南,瞬间“近墨者黑”之意也抛到九霄云之外。
胸壑极白之人,爱墨亦极深。东坡爱浓墨,几经漂泊,依然是“明月夜、短松冈,千里孤坟……”浓墨一书,即使千里江山,倾盆瓢泼,依然冲不淡。颜真卿爱墨,铁马冰河终是胜不过墨迹之涓涓细流。
人言,魏晋有风骨。若是没有了陶渊明之采菊东篱,七贤在竹林饮醉,还剩下的也就是王家那一潭黑乎乎的水了。
溶于水而黑得惊起,似《兰亭集序》遇上了“未若柳絮因风起”,尔然间“风骨”二字显得那么透亮,深彻。
终是东风吹皱一池春水,如江南,水墨丹青的成色,美到极致。
纸
借松竹之间的空儿,偷那么浮生一日闲,世间的意外惊奇,就那么偶然撞上你。初时发现纸的蔡伦,估计就是这样的。
夫其为物,厥美可珍。于诗人,纸乃世间尤物,可珍极了。似江南墙的白,丝丝温情如窈窕之女。
宣纸一张,白的色,开启了几千年的诗画文墨。无龟壳背之拙劣,也无骨头上划刻的沉重,竹简已然成为谈笑光阴的物什。
可挂可书可卷,袖口一开,就是一个盛世的繁华。想必王羲之该是深得力透纸背的意味。留一点白,一笔一画,一词一句承载了一个书法史,够诗人膜拜千年。
满怀惆怅时,少年嫩绿,可供涂鸦,兴尽而书。纸,是该有傲气的,每一句绝美愁肠都有着它的温度。纸,该是悲绝着深沉,每一帧历史的血雨腥风,都用它沾着,承载着。
山高水长,决绝而后纸也苍老了。
砚
文房四宝里要数“砚”是最笨拙的摆设,其余各宝各显本色,风飞色舞,挥舞、浸没、舒展,不需巧言令色,即可使人颔首掳须。殊不知,美存在无言,陪衬亦然是美的景致。
东坡藏有砚,甚爱研墨于砚滑行中的样子,其余皆不足为道。古今文人墨客,习书法,好笔墨,没有一个不爱寻一好砚,观之,赏之。此时,方砚即是天地万物,妙境云间,霞飞孤鹭。
世人所好者甚多,有味蕾,有山川行迹,有铜声银臭,唯有爱砚的人,甚是别致。米芾算是很极致之人,爱得有狂悖,消管王侯将相、墨浸华裳,得砚便胜却世间无数。
日月星斗,山河旋转之后,笔毛褪却。风吹日晒之后,墨也变了当初颜色。雨打雷鸣之后,纸也会消磨消散。唯有砚,千锤百炼,风采依旧。
或许,这就是砚的哲学,质坚而细腻,莹润可沉。
——落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