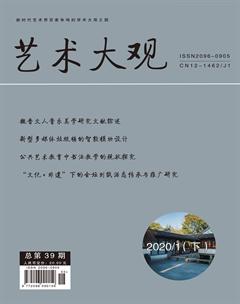贾樟柯电影中空间的审美追求
王鹏凯
摘 要:本文以贾樟柯《三峡好人》《山河故人》《江湖儿女》三部影片为主要解读对象,借助福柯的“异托邦”理论和结构主义性质的文本分析方法,试图论证贾樟柯电影中故乡世界的成熟过程正是心中“异托邦”的建构。
关键词:故乡;异托邦;纪录片;剧情片;真实化
中图分类号:J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0905(2020)03-00-03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并非单纯指一个具体的容器、物理意义上的抽象概念,或是故事发展的场景或背景,而是带有社会属性、文化属性和历史属性。”现代社会的乡土在现代空间中与权力活动的主要空间——城市空间,构成了异质而同在的关系,乡土中的人物在这两个空间中流动,他们的生活事件又打通了乡土与城市的空间和时间限制,或松动了城市活动空间,或在相互属性的碰撞中定义了人物的特性,贾樟柯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表达着他对当今电影表达方式的思考以及城市转型中下层空间与权力空间的关系。[1]
本文选择三部贾樟柯后期相对成熟的三部作品,《三峡好人》(2006年)《山河故人》(2015年)《江湖儿女》(2018年)。这三部作品中贾氏电影已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写实和对人物的塑造已与早期的单纯纪实有所差别,但仍保留一以贯穿的情感底色,这三部影片也仍然以边缘人物为描写对象,以追寻为主题,都体现着回归的线索,通过多种镜头语言,故乡在人物的离去、归来中,表达出贾对乡土与人性之间的独特理解。
为了更好地分析影片,本文将援引米歇尔·福柯的“异托邦”概念,“异托邦,又称为‘异质空间,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差异性、他性,以及由此而生的批判性。”[2]异托邦概念虽然应归属于社会学理论,但各种空间事件或相邻事件连接方式的多种可能性同样对二十世纪的科学、哲学、艺术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尚杰在《空间的哲学:福柯的“异托邦”概念》中从权利与秩序的角度总结了福柯“异托邦”的几个特征:一是那些被社会主流的秩序所排斥的偏离性异质空间;二是从文化层面来说,异质空间和城市中的其他空间在位置上会发生不断的变化;三是基于乌托邦来说,异托邦可以将相互之间不能存在的几个空间并置为一个真实的场所;四是打破传统的时间经验,在新的层面上使空间和时间重新分配、交叉;五是在这样的空间中存在的是具有群体意识和空间化仪式的人;六是这样的空间相对于外部空间来说具有幻觉性和补偿性。这些论述启发研究者将电影与现实相联系,电影并非对现实的简单复制,他通过独具特色的镜头语言重新看待现实空间,并生发出新的意义,从这一点来说,异托邦理论尤其具有代入价值。
在借用异托邦理论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对贾樟柯电影空间架构的论证,分析故乡世界与其他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将人物作为带动空间交互影响的连接点,说明人物和空间之间是互动的,空间之间语境的碰撞在人性上体现出,美学风格的成熟是与故乡世界的建构紧密相连的,其中也体现着贾氏电影的真实化追求。
一、乡土的异托邦特征
(一)边缘化空间的张力
异托邦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它“常常预设了一个既开放又关闭的系统使它与其他空间既相区隔又相沟通”。[3]
首先,贾氏电影中的乡土世界,是具有“异托邦”性质的边缘化空间,三峡大坝工程的建设使奉节面临被淹没的命运。
在《三峡好人》当中,也通过两条平行发展的故事线表现出这种特征。全篇没有明确的表明韩三明和护士沈红所生活的山西的乡土环境,但却通过他们所活动的现有空间反映出了乡土的底色,这种映衬是通过“回归”的主题表现出来的,韩三明从山西不远万里来到奉节,是为了找寻他被公安“解救”回故乡的妻女,他一再固执地向马老大询问,以及寻找工作在当地扎根打算长久等待的举动,都表明他是相信自己能给妻子一个安稳的生活,在表现韩三明的镜头中,电影多采用广角镜头,库区环境占领了画面的大部分,人物似乎只是环境的点缀,而这种环境也是韩三明眼中的世界,这种表达使韩三明所要回归的乡土世界自然显明,奉节的空间映衬了韩三明的乡土空间。
沈红在找到丈夫郭斌时,郭斌已是资本横流中的一位逐利商人,沈红在抢挖古墓的工地上找到郭斌的朋友,同样是广角镜头,即将淹没的库区旧城环境通过沈红和东明的行迹呈现出来,而两人又只在画面中占据很小的一个角落,这种表达很好的映衬了人物与时代的关系,人物的边缘化状态正是通过这样的对比在影像语言中表达出来,沈红最终与郭斌分手,这个叙事结局也可以通过库区废墟环境加以暗示,而沈红的最终回归故土让故土空间在不出场中自然对比出自身的边缘地位,而关于贾樟柯电影的研究认为,贾樟柯电影一直是连贯的,于是,在《江湖儿女》中,郭斌虽然抛弃了巧巧进入资本阶层,但最终却并未成功,成为残疾人归来,依然是巧巧收纳了她,乡土的情意价值也借以凸显。[4]
其次,作为被社会主流话语空间排斥的乡土下层社会,在贾氏电影的早期作品中,也通过纪录片的方式来加以现实呈现,在《无用》中,时尚服装设计师通过设计一套名为“无用”的服装款式,而服装的颜色要靠泥土来装点,然后镜头就切换到山西一间矿区小裁缝店里,那里的裁缝也拥有熟练的技术,但来往顾客多是一些简单的缝补要求,不能设计自己喜欢的样式,贾也通过其中人物的活动状态,例如他对一位曾经是裁缝的矿区工人的采访,以及几个青年骑着摩托在矿区中高喊着呼啸而过,环境的贫穷和边缘群体,尤其在其中的活泼的人群,不同于那些木讷的在大工厂中被异化的人群,这样的镜头表现也沿用在《三峡好人》中,纯纪实地对四川奉节将要被淹没地区的长镜头拍摄。[5]
(二)不能共存的空间并置为真实的地方
這里主要体现出不同群体人群的不断涌入,而他们又相对形成独立或隔绝的群体,主要在其纪实性的作品中突出,《三峡好人》中的奉节较明显地体现了这个特征。由于三峡大坝库区的建设,奉节成为即将消失的城市,这座“末日之城”集结了多方群体,而构造出一个个不同的小型空间,民工们日复一日地推到一间间房屋,废墟和残骸一日日堆积,民工们的涌入正昭示着这座城市的末日底色,但就在技术专家爆破一栋栋大楼时,考古团队却在抢挖文物,保存这片地域的历史,城市通过另一种方式达到继续存在,而对于来来往往讨生活的原住民和边缘人群,他们几乎不再保有对这座城市的记忆,大部分生活地区已被库区淹没,他们对于每个群体的语境几乎是无感的状态,生活在这里最久的人们确切很大程度上需要远走才能继续生存,资本家们在简陋的楼房上举办舞会,在这座即将不再的城市中不断开发他的资源,通过改造旧状态产生新的城市样貌,而这种样貌对于他们来说也更多是资源而不会保有更多记忆,不同空间的并置,充分显明了权力和秩序在与传统的时间彻底决裂时,多种语境的并置是可以实存的。[6]
这种并置可以清晰地勾勒出城市记忆的流变过程,并通过纪实性的拍摄加以强调,原著民是不受打扰的,他们保有着地域历史,而建设规划提出以后,资本逐渐占有这片空间,原著民成为边缘人物,负责将奉节变为废墟的资本群体暂时成为主角,组成了一系列不同的生活空间,而拆迁大军成为打造废墟的基础力量,但也是边缘群体,他们有着另一个生活空间,这样的景观并置体现着异托邦的第二个特征。[7]
(三)具有异质空间化仪式的人
信仰往往是仪式化人物的重要底色,在宗教中,一种固定的信仰常常和仪式化的动作相配套,这种信仰既代表着追寻者的价值观,又代表着他们坚守的方式。有固定信仰追求的人,往往在行动上都会带有仪式化的底色。韩三明外表朴拙,老老实实,内里却有属于自己的一份坚硬,他脸上的表情多是固定的,没有过多的肢体语言,多数时候是木讷的,他的寻妻之路如一场圣徒之旅一般,他向马老大赠酒时的坚持,寻找工作安定下来,宁愿过着清贫的生活,韩三明是乡土世界中走来的最具仪式化的人物。
护士沈红也有同样的特征,她找到“正山红叶”时独自品茶;找到郭斌时的平静;离开时从容地与郭斌共舞。在三部作品中,仪式化在每个人物身上都有不同体现,郭斌作为江湖大哥,行事时一贯果断老练,他教巧巧用枪时的一段对话:“火山灰是最干净的”,归来后不甘失败又悄悄离去;沈涛在听到最喜欢的歌曲时熟练的舞蹈;经常包麦穗饺子寄托对儿子的思念;到乐胸前一直戴着母亲的家门钥匙等等,他们的仪式化是因为他者而有情意价值,希望回归重组一个更好的家庭,坚韧更带有宽广品德的性格,使他们在自己活动的群体中往往较受欢迎,较易被他人理解,他们的追寻由此而被赋予群体的色彩。[8]
正因为这样的性格底色,使他们得以带着自己的追寻而在并置的不同空间中活动,在每个空间中,他们又不是主流群体,是相对边缘的人物,即使如张晋生那样的资本家,移民之后,也依然是异国他乡的边缘人物。
(四)幻觉性、补偿性在人物情感中的体现
人物作为空间转换的链接点,空间的压力在情感中表现往往具有幻觉性以及由此凸显空间的补偿性,电影虽然是影像艺术,但它并非是影像的纯粹客观呈现。电影借由独特的影像语言,建构自成一体的独立景观。总体来说,贾樟柯的几部作品所构筑的乡土世界与现实世界存在着差异,但其所反映的城乡位置关系是确实存在的。《三峡好人》表现出乡土为城市建设提供大量劳动力,但他们只是暂时的停留者,在《山河故人》当中,根对人的牵绊是化入血液的东西,乡土中走来的张晋生,始终抹不去他山西人的个性,根在山西的到乐,始终在生命中潜藏着对母亲的思念。而这种思念在他的中文教师身上得到幻觉性的释放。幻觉性的表现尤其在于电影中的超现实意象。韩三明拿着钞票对比家乡与库区环境,寄托他对妻女的追寻;沈红看到飞碟在天空飞过,加深了她的爱情终将破灭的色彩,郭斌在教巧巧打枪时,两人面向不同方向,且用火山灰代表郭斌的追逐最终要化为乌有,惨痛归来。《山河故人》中的迪厅,坠毁的飞机,都从侧面暗示着人物的追寻结局。[9]
乡土中家庭的缺失,韩三明来到了新的空间,奉节;乡土中地位的坠落,郭斌来到了四川;乡土中资本的危险,张晋生移民到澳大利亚,物质的追寻来自空间的不断迁移,而精神的补偿却始终来自乡土。
“异托邦”作为一种主要对空间的审视方式,其自然地把活动于空间中的要素做空间化考虑,基于节制性的表达方式,贾樟柯主要通过视像和意象呈现价值观冲突。贾樟柯提出的观点主要表现在,故乡为外部空间输送着人物基以立足的价值观;追寻最终要通过回归才能达到人性的恢复。巧巧、韩三明等人物集中体现着这一点,物质支配的主流空间中,人性最终要通过寻根才能达到精神归宿。
二、结束语
在城乡转型的大背景下,日益严重分化的阶层成就了地理上的空间区隔,乡土世界日益成为异质化空间,贾氏电影以独特的影像语言表达自己的独特理解,其中确实体现着空间的“异托邦”特征。表现着自己对于乡土与人性之间的理解,从多个层面探索着“乡土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复杂张力。
在电影市场走向“作者化”之时,这种电影追求对于国内电影素材的选择和处理方式都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提示电影作者在追求技术和艺术的同时,不应忘怀电影介入现实的力量。同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多种阶层和多种群体的交织关系,是复杂的,需要导演用独特的角度挖掘出来,站在主流和边缘的双重视角来审视社会关系之间的微妙多元的对话。
参考文献:
[1]王弋璇.列斐伏尔与福柯在空间维度的思想对话[J].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10(02):352-363.
[2]霍胜侠.全球化语境下的香港“异托邦”空间再现[J].文化研究,2018(02):79-92.
[3]尚杰.空間的哲学:福柯的“异托邦”概念[J].同济大学学报,2014(7).18:24.
[4]张陆.贾樟柯电影中的农村人物的嬗变——以《山河故人》为例[J].西部广播电视,2018(24):137-146.
[5]王丽.现实主义视域下的《江湖儿女》[J].电影文学,2018(24):130-132.
[6]张纪尧.《山河故人》的美学创作及艺术风格[J].电影文学,2017(24):116-117.
[7]孙丽珍,侯东晓.从《山河故人》看贾樟柯电影的空间演变[J].四川戏剧,2018(4):122-125.
[8]韩阳.贾樟柯电影空间叙事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8.
[9][法]米歇尔·福柯著.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学术文库,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