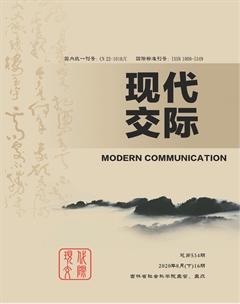论《弃猫》中的原罪意识与自我疗愈
孟辰 段雨霖
摘要:战争记忆是村上春树小说创作的一大主题,作者通过作品揭露战争真相,体现了鲜明的原罪意识。在《弃猫》一文中,作者首次回忆了父亲参与侵华战争的往事,披露了自己的战争记忆来源以及战争影响下传承记忆对自身的重大影响。对此村上试图进行自我疗愈,反思历史,达成和解。村上的历史反思和精神疗愈有助于唤醒读者对战争的集体记忆,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意义。
关键词:村上春树 战争记忆 原罪意识 自我疗愈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20)16-0125-02
2019年5月,村上春树在日本《文艺春秋》杂志上发表《弃猫,提起父亲时我想说的话》(以下简称为《弃猫》)一文,文章讲述了村上春树和父亲村上千秋海边弃猫的轶事,首次披露了父亲不为人知的身世及参与战争的经历,回忆了自己与父亲相处的过往,与父亲的矛盾以及最终的和解。在写作方面,作者延续以往的风格:表面上文风轻盈,但涉及战争历史的回忆又让人陷入沉思。这篇数万字的文章不仅是村上个人的回忆录,也反映了作家反对战争、正视历史的社会责任感,表现出鲜明的原罪意识和自我疗愈精神。
一、战争记忆中的原罪意识
村上作品中的原罪意识主要表现在对战争记忆的书写中。战争记忆是关于战争的历史记忆,既包含个体记忆,又包含集体记忆。两者相互联系,互相建构:个体记忆是构成集体记忆的单位,没有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就无从谈起;集体记忆赋予个体记忆意义,个体记忆只有放在集体记忆中才能被理解。在小说中村上试图用人物的个人情感体验或者具体的历史事件来唤醒读者的集体历史记忆。在早期短篇小说《去中国的船》中,作者直言“死使我想起中国人”,借“我”与三个中国人的故事,表现“我”对中国人的愧疚感,同时也隐喻了日本侵华战争;小说《奇鸟行状录》的情节直接以诺门坎战役和长春动物园虐杀事件为历史依托,讲述了日军在中国的战争罪行;《海边的卡夫卡》的主人公被两个“二战”日本逃兵带领走入森林,借逃兵之口对日本侵略史进行批判;《刺杀骑士团长》中有关南京大屠杀惨案,作者在小说中进行了直接陈述:“有无数(南京)市民受到战斗牵连而被杀害则是难以否定的事实。”[1]村上以文本为载体,传递极具争议性的历史记忆,反思战争,对“他这一代及其后代所背负的精神负担的重要部分加以表现”[2],反映出作者的原罪意识。而这种原罪意识又与村上春树的家庭背景密不可分。
村上对战争的个体记忆源于他的家庭生活,尤其受到父亲经历的深刻影响。在《弃猫》中,作者罕见地披露了父亲村上千秋被强制征兵参加侵华战争的诸多细节。村上千秋生活在战争时代,曾经先后三次被迫走上战场,年轻岁月基本都在战场度过。虽然战争结束后得以平安返回家乡,却产生了巨大的心结与终身的遗憾。文中提到,父亲每天都会面对佛龛投入地念经,以此来悼念战争中死去的战友和中国士兵。在战争中保留性命无疑是幸运的,但是父亲并没有因为逃脱死亡而感到轻松,战争的惨烈场面在父亲心中留下了巨大的阴影,这种记忆的传承也影响了村上春树。父亲曾向年幼的村上亲口讲述杀害被俘虏的中国士兵的经历,“不管怎样,父亲回忆的用军刀砍掉人头的残忍光景,很明显被强烈地烙印在我幼小的心灵里”[3],这显然给村上春树本人带来了严重的心灵创伤。另外,从父亲身上继承下来的战争记忆也成为他作品中原罪意识的重要来源。面对终日虔诚念经的生父,作为侵华战争参与者的后代,村上不得不继承父辈的战争记忆并把它作为自己个人经历的重要部分来接受与消化。而这份沉痛的记忆也是村上与父亲之间长年疏远的原因之一,以至于村上在父亲去世五年后才下定决心调查他年轻时期的军队履历,试图了解当年真相并探寻父亲在战争中经历的心灵创伤。当得知父亲入营时间与南京大屠杀相差一年,父亲并没有参与南京大屠杀战争时,村上春树如释重负。
原罪意识下加害者的后代这一特殊身份使得村上春树对待战争问题显得更为思辨:村上并不认同日本人也是战争受害者,他指出:“日本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战争结束后没能把那种压倒式的暴力相对化,好像大家都成了受害者,大家都用一种‘这样的错误决不能犯第二次的非常暧昧的措辞置换了战争暴力,谁也没为暴力的装置负责任。”[4]出于历史责任感与原罪意识,他在《弃猫》结尾呼吁:“一滴雨水也有一滴雨水相应的思考,也有一滴雨水的历史,也应该继承一滴雨水的责任。这是我们所不能忘记的。”这里所强调的正是个体记忆的作用:每个个体都需要承担历史责任,以求还原真实的历史记忆。
村上以书写个体记忆方式促進集体战争记忆的继承,这在日本右翼势力试图否认侵略而选择性“失忆”的当下显得尤为珍贵。村上春树在年号更迭、新天皇即位的举国欢庆时刻发表这样一篇文章,显然是为了提醒人们不能忘记历史,要保持对战争的清醒认识。
二、从心灵创伤到自我疗愈
“疗愈”原本是一个心理学术语,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日本社会的关键词。“疗愈”的流行表明民众存在一定程度的心理创伤,渴望得到精神救赎。它同样是村上文学创作的关键词之一,作家一直试图在文本中编织自我疗愈的故事,渗透和解的理念。例如《海边的卡夫卡》的主人公踏上找寻自我、破除诅咒的旅程,最终在各种经历和奇遇后逐渐成长;《刺杀骑士团长》中“我”为解救少女秋川真理惠进入“隐喻”的地下洞穴,在黑暗和死亡中挣扎,最终少女得救,“我”也回归日常生活,实现了精神疗愈。
在《弃猫》里作者记述了两段从被遗弃到和解,从创伤到治愈的亲身经历,指明了历史记忆的出路所在。文章开篇村上回忆起自己随父亲扔掉小猫的故事:某个夏日的午后,父亲骑车载着村上,把装有猫的箱子留在离家两公里的防风林里。可两人回家却发现,本应被扔掉的猫在亲昵地叫着迎接父子两人。面对这一情景父亲顿时愣住了,表情由吃惊变为安心、释然。父亲表情的变化深深印在村上脑海里,以至于和扔掉猫这件事重叠在一起。根据作家分析,小时候曾经离家为僧、寄人篱下后来回到家里的父亲目睹了丢弃而复归的猫,不禁联想到昔日的自己,少年时期的心伤就在这一刻得到了安慰和治愈。文章名为《弃猫》,实际暗示了父亲被遗弃的人生经历与心灵创伤,“把猫丢弃”隐喻了对历史记忆的逃避和遗忘。在村上看来,“弃猫”无疑是行不通的,被刻意隐藏的记忆终究会以不经意的方式复归,唯一的出路是正视历史,敢于面对,进行自我疗愈。
《弃猫》还讲述了村上与父亲两人之间矛盾化解的过程。由于种种原因,村上父子之间产生了很多矛盾和纠葛。而在村上成为作家后,两人关系降到冰点:彼此断绝了往来,二十几年不见面,几乎不联络。在父亲村上千秋临终前情况终于好转:当时村上探望了身患重病的父亲,两人开始笨拙地交谈,在血浓于水的亲子关系连接下,二人终于实现了和解。村上春树也深刻体会到了父子之间的牵绊之情。无论是因“弃猫”父亲得到治愈,抑或村上父子重归于好,这些往事都给读者以安慰感。
村上清醒地认识到个体的原罪感源于集体对于战争认知态度。集体记忆影响着个人的命运走向及精神世界。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只有还原真实的个体记忆才能恢复真实的集体记忆。
三、历史反思的社会意义
村上春树在《弃猫》的结尾表达了对猫的最终命运的担忧。小猫擅长爬树,却不擅长下树。一只爬到树上下不来的猫是在枝头慢慢化成了白骨,是彻底消失不见了?抑或是像没有彻底消失的记忆一样,猫仍在树上紧紧抱着树?作者在自问的同时,也给读者留下了思考的余地。这段描写看似与回忆父亲的主题无关,却暗示了作者的真实写作意图。村上在与父亲和解后仍旧挂念这只猫,这只猫是植根于父亲与村上脑海中的共同记忆,但猫的命运始终不得而知,让村上春树不能释怀。村上试图透过弃猫来思考死亡,呼吁读者更多地关注那些被遗弃的孤独灵魂,以及战争与暴力下的个体命运。对于猫的担忧,暗示了村上对于历史记忆的担忧。猫被人遗弃、遗忘,但是我们很难忽视猫的存在,内心的矛盾无法化解。个体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淡化,而承载着历史责任的集体记忆并不完整。对于个体而言,战争带来的创伤是不容易一下子被消化的,因此村上春树力图通过作品找到暴力的源头,并与之抗争,最终获得新的动力,帮助更多的人解开心灵的枷锁。这体现了村上春树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
村上有关战争的言说对历史的反思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作家敢于书写战争记忆,表现历史的真相,揭露战争中的罪恶;另一方面,积极抚慰记忆深处的精神创伤,在自我疗愈的同时也把治愈之感带给读者。村上从个人主义出发,挖掘自我意识的深处,通过个体记忆书写对战争创伤进行慰藉和安抚;用隐喻象征等后现代主义手法,传达反对战争、正视历史、重识自我的主张,正如东京大学藤田省三教授所言“表现出了现代日本人的良知”[5],对推动日本文坛乃至日本社会对战争问题进行深度思考,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意义。
四、结语
在人类历史名为“战争”的阴影中,出现了许多加害者与被害者,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没有获胜者。不仅仅因为无数生命在战争中消逝、经济社会受到重大打击,更重要的是个体的精神世界得不到安宁,产生难以弥合的心灵创伤。村上春树作为战争亲历者的后代,拥有强烈的原罪意识;他深知战争的歷史遗留问题是个体心灵创伤产生的重要原因,而选择遗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村上希望透过作品唤醒当代人对于战争的反思,努力寻求暴力源头,以恢复个人的灵魂尊严。可见村上春树渴望觉醒的强烈愿望,体现出他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在未来,作家追寻历史真相、拯救个体灵魂世界、治愈心灵创伤的努力仍会继续下去。
参考文献:
[1] 村上春树.刺杀骑士团长[M].林少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55.
[2] 鲁宾.倾听村上春树[M].冯涛,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198.
[3] 村上春樹.猫を棄てる:父親について語るときに僕の語ること[J].東京:文藝春秋,2019.
[4] 刘岩.村上春树可以作为东亚的“斗士”吗:《奇鸟行状录》战争叙事论[J].外国文学评论,2010(1):9.
[5] 尚一鸥.村上春树的战争书写:读《刺杀骑士团长》[J].读书,2018(7):113.
责任编辑:杨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