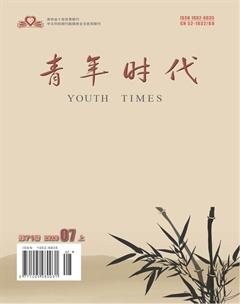敦煌艺术哲学形态载体浅论
李骅 王屹
摘 要:敦煌艺术是敦煌哲学的现实载体,具有现实追问的哲学基因。敦煌艺术哲学在艺术认知层面上具有艺术哲学的一般性,在艺术表现形态上则具有艺术哲学的独特性。整体性哲学思维特征与现实追问性是敦煌艺术哲学的形态载体。哲学意义上的“相”与“象”在敦煌艺术的认知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是敦煌艺术哲学的重要理论思维与方法之一。敦煌艺术哲学载体的清晰化有利于进一步回答敦煌艺术何为的哲学追问。
关键词:敦煌;艺术哲学;形态载体;哲学追问
一、对敦煌艺术哲学的初步描述
对何为艺术哲学进行界定是困难的,因为这一命题隐含着“艺术是什么”与“哲学是什么”的双重诘难。在哲学视域中,如同康德对于“人是什么”的追问一样,其意义不在于答案,而在于话题指向的终极维度。就此而言,“艺术哲学”是两种追问叠加从而最大推理可能答案的形而上学,是主体对自我存在意义的不断确证与具有“类”特征的价值判断不断观照与回溯的哲学样式。如果说敦煌艺术是敦煌的灵魂,那么敦煌艺术哲学就是对何为敦煌艺术的相续反思。敦煌艺术哲学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是一个由“意象的敦煌”与“具象的敦煌”所体现出的“敦煌完整有机体”。在此意义上,敦煌艺术哲学不能脱离具体的敦煌石窟藝术、出土文物、文化史料遗存等客观实存。而是主体通过敦煌具体元素,如文献、建筑、洞窟、壁画、塑像等客体进行儒佛道哲学思想和外来哲学思想分析并指向哲学反思所形成的“艺术哲学”,是对“人类敦煌”艺术性的整体性认知与确证,是建立在既有敦煌学研究基础上的艺术理论的哲学反思与追问。
毋庸置疑,一切敦煌艺术都是敦煌艺术哲学的现实载体。以石窟艺术为例,敦煌石窟艺术在漫长历史中为不同时代的人们提供了精神追求与对人生存在意义的回答,这种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对人生价值与意义的不断询问其本身就是哲学的智慧。例如,北周第296窟出自大乘经典的“五百强盗成佛因缘”通过绘画艺术展现人人都具有成佛的可能。而“福田经变画”则进一步劝导人们通过多多行善、广种福田的方式最终成就佛果。敦煌诸如此类具有哲学意蕴的石窟壁画比比皆是,将善与恶、生与死、平凡与超越等充满矛盾对立的两组概念进行了具有高度艺术化的、充满智慧的哲学阐释,这种将理想的光芒从应然世界投射到实然世界的表现方式体现出思想之源与现实之果二者之间必然的哲学意味。
二、敦煌艺术哲学形态载体的基本判断
对敦煌艺术哲学的哲学形态认知是建立在既往哲学认知基础上的。敦煌艺术所具有的哲学内涵并非不同于其他艺术所具备的哲学内涵,从艺术认知层面上具有哲学的一般性,从艺术表现形态上则具有不同于其他艺术哲学的独特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敦煌艺术哲学是一般性的哲学认知构成,而其表现形式则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因此,对敦煌艺术哲学的认知是一般性哲学思维认知与中国哲学思维认知在敦煌艺术上的综合。敦煌艺术哲学存在于这种哲学认知的综合的过程中,而并非是一味追寻这种哲学认识的结果,其艺术载体的多样性与千年历史积淀是这种哲学认知的突出特点,表现出非闭合的无限趋近特性。《道德经·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1]“无”与“有”均可以作为“观”的对象存在,“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主体探查活动的总体表现,而其“妙”与“徼”则是具有主体能动性的创造体现,“徼”与人思维认知的边界有关,“董思靖说‘徼,边际也(《道德真经解》)”[1]这种具有主体能动性的指向认知边际的哲学认知是敦煌艺术哲学所自然存在的哲学认知路径之一。在对敦煌艺术的哲学认知过程中,所需要秉持的是这种具有主体能动性的“不知”的精神,所继承的是对知识的敬畏与尊重、对未知的惊异与探索,是一种对存在已知经验的再经验、再趋近,其吸引来自于“无”的不确定性与不知性,是以敦煌“有形之相”探触敦煌“无形之象”的哲学实践。
敦煌艺术显然具有现实追问的哲学基因,整体性哲学思维特征与现实追问性就是敦煌艺术哲学的形态载体。敦煌艺术哲学同时具有思维与文化的抽象性,其抽象性是“具体的抽象”,因此,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共同价值认同不会是脱离了历史与时代现实的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因为有了敦煌,才可能有敦煌艺术哲学,无论是“形而上”的敦煌艺术哲学,还是“形而下”的敦煌艺术,都应当首先具有“敦煌之形”而后“上下”。敦煌艺术哲学的这种抽象性与思辨性因此而具有整体性思维特征,体现的是敦煌文化与时代的相谐进,而不是敦煌文化艺术的孤立悬置。
哲学意义上的“相”与“象”在敦煌艺术的认知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是敦煌艺术哲学的重要理论思维与方法之一。有学者指出“一切艺术都无法脱离象的构成问题,因此《周易》关于象的理论也就具有了重要的美学意义。”[2]《易传·系辞上》“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凡此种种,均说明哲学意义的“相”与“象”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故此,二者之间必然存在着相互转换的具体路径。例如,由敦煌洞窟营造之“相”体现的敦煌外在之“象”,敦煌壁画表现之“相”体现敦煌绘画艺术之“象”,敦煌历代塑像所体现的时代发展之“象”等。从更为具体的敦煌艺术元素层面来看,敦煌壁画乐舞元素的体现可以看作是敦煌艺术哲学的重要标志之一。通过大量对“相”的描摹,从哲学意义上实现某种具有超越人类局限性的升华,即“象”的整体突破。如对由“反弹琵琶”的相状进入到“飞天乐舞”的意象,实现了整体意义上的认知边际突破,使艺术与哲学思维的共在,这是一种对自由与希望无限向往的直观表达,不存在时代与地域的限制。客观而言,敦煌乐舞存在着从艺术美学升华为艺术哲学的历史必然,这不仅是由敦煌石窟自身的属性所决定的,而且,敦煌乐舞不是单一的审美对象,而是兼具承载人类终极问题的哲学审思对象,是视觉审美、听觉审美之后所呈现的心灵沉思。事实上,真正的艺术都在表现对生命和生命奥秘的追寻,所描绘的都是一种审美的宇宙镜像和人生境界,恰恰在这点上,艺术本质上和哲学是相通的,敦煌艺术概莫能外。
敦煌艺术哲学的“形而上学”不是沉浸在大脑中的“哲思”及其“抽象”。艺术是抽象的,艺术的表现则是具体的,没有载体的“艺术”是令人困惑的。敦煌艺术哲学应具有可见的形态载体,其哲学的迸发是建立在艺术载体可见性与表现性的基础之上,这种载体是具象的,体现在三个层次。首先是敦煌整体性的具象化存在层面,其次是敦煌整体性的意象化存在层面,最后是敦煌元素化存在层面。
从敦煌整体性的具象化存在層面来看,敦煌整体性是指敦煌的客观存在,是自然敦煌与人文敦煌的统一,这是一种不可复制的、独一无二的客观存在,是时空延续与当下自在的形态显现。这种整体性的客观存在是一种具有生命力的有机体存在形态,体现为一个从产生到发展的线性动态历程,任何剥离敦煌既有元素与敦煌整体性存在的过程都将导致敦煌有机体的缺损,而改变敦煌整体性的任何损益同样将导致敦煌有机体的面目全非;从敦煌整体性的意象化存在层面来看,敦煌的整体性客观存在即敦煌有机体是敦煌意象存在的前置条件,“敦煌意象”是一种具有整体感的、在客观敦煌完整性基础上的主体对象的感知升华,“敦煌意象”通过地域环境、建筑、雕塑、壁画、人文等各个层面互为流转,完整呈现“敦煌有机体”,是敦煌艺术哲学形态的灵魂载体之一;从敦煌元素化存在层面来看,元素化实质上是敦煌艺术的一种具体的表达方式,而敦煌艺术哲学则在这种具体的表达方式中完成其哲学存在。如敦煌洞窟营造与敦煌壁画雕塑之间的具体关系,通过对空间的独特分割,实现壁画、塑像、空间、光影与观察者的融合,通过敦煌具体元素的协调,构成具有哲学特征的主体认知活动,从而实现可能对认知边际进行触碰的哲学体验。再如敦煌飞天,“老庄哲学、玄学、般若学、禅宗学说的精义,使敦煌飞天一步步抽象化、哲学化,使之成为中国人精神自由的象征”[3]。飞天作为最具特点的敦煌元素,其形象在哲学视域中完成了艺术表达,实现了艺术升华。
三、敦煌艺术哲学载体的哲学追问
哲学性反思是确定敦煌艺术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之一,敦煌的存在与对这种存在何以存在的追问体现的是文化艺术与历史的对话。思维对象的确定性与认同性是建立共同哲学思维的基本所在,也是确认敦煌艺术哲学的基石。敦煌艺术具有显著的“追问式”特征,大量直观的洞窟壁画充满了对存在与灭亡、现实与理想、入世与出世、个人与群体等具有矛盾统一性命题的展现与思索,充满了对人与世界关系的疑问、询问与探索,同时又强烈体现出一种思维方法论,即试图对对象世界给予符合自身实际与时代背景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哲学式解答。敦煌艺术风格的形成首先应当是敦煌艺术哲学形态的风格确立,这是敦煌艺术“象”的哲学思维,而这种“象”是一种对存在着表达困境的“无”的无限否定性趋近,其本身就是一种具有高度能动性的哲学驱动。
敦煌艺术哲学是体现人与世界相统一又具有能动关系的哲学构架,这是对敦煌“是什么”和敦煌文化“为什么”的哲学思维与价值追问,这种具有价值性特质的哲学追问是对传统敦煌学研究的理性思索与哲学实践。敦煌的存在本身就是不同历史时代具有朴素哲学形态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具体显现,在宏大叙述的背后营造一个超越的意义世界,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中华民族气质的,具有哲学形态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因此,敦煌艺术哲学的目的性是统一的、发展的、具体的艺术价值实践活动。
传统意义上对敦煌文化的研究在极大丰富了对敦煌“是什么”认识的基础上仍然需要通过哲学的主体性思维阐释具有现代哲学特征的价值性判断。敦煌艺术哲学载体的清晰化有利于进一步回答敦煌艺术“为什么”的哲学追问,而哲学开放性与对认知边际的冲击指向的是未知的“无”,这是敦煌艺术产生创新动力的哲学来源之一。
参考文献:
[1]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73,76.
[2]刘纲继.周易美学[M].长沙:湖南教育版社,1992:279.
[3]穆纪光.敦煌艺术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