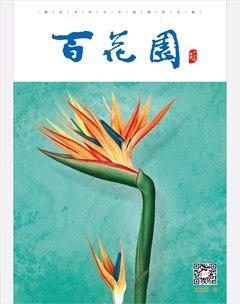死亡练习
侯峰岩
养老院的廊厅下,方明躺在一个灯芯绒的沙发上,扶手上的棕色漆面斑驳陆离,两只搭在扶手上的手,像裸露在地面的老树根。早晨的太阳照在他微闭的双眼上,他感觉眼前一团橘红色的温暖。
旁边陆续多了几张模样相似的灯芯绒沙发,沙发上的人不尽相同,他们互相打着招呼,寒暄着。
方明没搭理他们——没空,他在想他自己的事情。
这辈子他能想明白很多事,唯独死亡这件事毫无头绪。死亡到底是什么?人死的那一瞬间是什么感受,人死之后是什么感受,那个存在的我到哪里去了……
他不是没想过。他问过孔子,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他认认真真地学习如何生,指望有朝一日醍醐灌顶,顿悟什么是死,但最终还是没找到其中的关联。
他问过坐在旁边沙发上的李老太。李老太乐呵呵地说:“从来没想过。听说超市的鸡蛋星期六打折,告诉你儿子赶紧去买。”方明重新闭目养神。
他问过坐在旁边沙发上的老张。老张一生经历丰富,做过官,经过商,挣过大钱。老张先是黯然地说:“死是无法避免的事实,花精力想它干吗?趁活着干点儿有意思的事。”然后老张满脸挤着笑问方明:“我说老兄,这辈子和几个女人上过床啊?哈哈。”方明措手不及,没吱声。老张一撇嘴:“哎呀,白活了。”
方明还问过曾经坐在旁边沙发上的老崔。老崔比自己小几岁,瘦高,看着身体没啥毛病,能长寿的样子。老崔说他没想明白死,但是他想明白了活,想明白了活的荒谬和毫无意义,他说如果死很可怕的话,那么活着就是另外一种死。老崔现在已经不在养老院了,前段时间他吃安眠药自杀了。说起来老崔,方明现在有点儿想他了。
方明睁开眼,摸出手机,想给儿子打个电话,俄而,又放回手机。儿子最近埋怨他太悲观,说他总是提死什么的,不吉利。儿子让他别害怕,说他一定能活一百岁。
护士小李向他走来。小李人不错,照顾他日常生活,就是话太少,说得最多的就两句:“老方把这药吃了。”“老方吃药了吗?”
“老方把这药吃了。”小李塞到方明手里一个药包。
方明低眼看着手里的药包,想,我为什么要吃药?是不想见到死亡吗?我不就是想了解它吗?不见怎么能了解?他环视了一周,李老太、老张和缺席的老崔。他想,了解死亡还得靠自己。
方明搓了搓药包,又想,不过,我可做不到像老崔那样,我就是想了解一下死,不是真想死。不如这样,这包藥就先不吃。一包药不吃要不了命,但估计可以接近死亡,可以看清点儿死亡的模样。
方明把药包攥在手里。
他眯起眼睛,眼前一团橘红色的温暖。
不知什么时候,他想起了父亲。他想让父亲原谅他。父亲弥留之际,说想去北京看看,那是父亲第一次对他提要求。他果断地拒绝了。他恨父亲,认为他没尽到父亲的责任,他不可能原谅他。父亲带着遗憾死掉的时候,他很解气。没承想,这记恨和报复却成了内疚,这么多年像一块巨石压在他的胸口。现在他很想拉着父亲的手说一句他愿意带他去看看北京。
他想起了老婆。他想让老婆原谅他。这辈子她和他在一起没享到什么福。福不是荣华富贵,是对她好,他对她不够好。他三十五岁那年,瞒着妻子和一个陌生女子过了夜。那短暂的快感,像苍蝇屎一样长在他的心里,一直扑打不去。如果回到那一天,他想待在家里,给老婆做顿饭。
他又想起了自己。他想让自己原谅他。小时候他想成为一个演员,他确信自己喜欢那行当,这辈子没几件事让他那么确信。可是后来他做了一辈子小职员,即使凭此有了两套房,衣食无忧,但那不是他想要的。有个东西一直待在心里,刀一般割着他。那个东西叫梦想。他曾埋怨没有天时地利,埋怨那些暗示他是痴心妄想的人、规劝他客观务实的人。现在,他怪他自己。快要死了才知道,死是自己的事,怎么活也应当是自己的事,与世界和他人无关。如果时光能够倒流的话,哪怕是回到去年,或者昨天,或者是刚才吧,他都要不顾一切地努力一把,活成他想要的样子,无论结果怎样。
方明忽然意识到他看到了死亡的样子,原来死是留恋生,是不知死焉知生,是原以为明白的事其实不明白。
方明觉得死亡练习起作用了,他感到一阵心潮澎湃。
隐隐约约听见小李的声音,然后又听不见了,眼前那片橘红色的温暖渐渐地消失了。
“老方,你吃药了吗?”小李问方明。
方明没搭理她。
小李伸手拉方明攥着药的手,药包掉在地上,圆形小药片滚落一地。
方明死了,死于地球照转的某个时候。
[责任编辑 徐小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