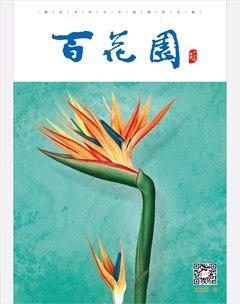南京往事
刘兆亮
那年,在西南一座城市里,我认识了老段。
老段并不过于老,1975年出生,但长相比实际岁数往前赶了十多年,像是1957年出生的。在那座城市里,我们都是异乡人,偶尔朋友带朋友,赶一个并不重要的饭局,认识了,就成了重要朋友。
其实,我与老段一年也没约过几次饭,可能四次吧,但第一次吃饭,连了两场。
第一次见老段,是一年初夏,在一个叫黄泥岭的中餐厅。我坐在一张13个人的大桌边,记得是贴着左手边,来了一个戴着眼镜、胖乎乎、头发根根竖起、可爱型的中年人。他的短袖白衬衫扎进牛皮裤带里,脖子V领处趴着几颗豆大的汗珠子。
当时,这个中年男子来得不算早,也并不迟。从他脖下的汗珠可以判断,他想准时,不知是在路上还是在楼梯里,赶了一阵猛路。不然,哪里会有那么大的汗珠子——滴水藏海,汗里识人,他该是一个会尊重别人时间的人。
饭局里尊重别人时间,还包括,你端起或放下酒杯所说的话、所讲的故事,要是不好听,像老太婆的裹脚布,那就是耽误人家了。一顿饭,两三个钟头,人又多,每一句话,或者每一个段子,都要精彩,这样才让人觉得时间过得值得。
我很快就认识的老段,就是这样的人,把话省着说,说一句算一句,大家都觉得很合适。比如,相互敬酒,我们两个杯子碰到一起,他说:“听口音,你不是这里人。来,为了能在异乡相聚,干。”
一桌13个人,一多半都是外地的,老段这句话,说得他们有了碰杯的理由,说得那个城市的人也有了借口喝酒:“我们这个城市很包容,你们都会混得很好。来,敬你们!”
再和老段的杯子碰到一起,他又找了个理由:“你是江苏人,我在你们省会南京念大学,你小,算是师弟。——来,师弟,再干一杯,等会儿加个微信。”
三个小时一晃而过,桌子大,对面说话都不方便,算起来,我和老段话说最多。
散场后,有几个人提议,大家认识还不够,到新牌坊大排档,再整几瓶啤的。
老段呢,说自己喝得眼睛发直了,还没喝啤酒呢,脑细胞一个个都像啤酒花正在往上冒,有股神经好像也在传递信号,它在跳,“多了”“多了”“多了”,这样,在跳。
老段这句半醉的话,真像个单口相声啊,大家都听乐了。
对了,老段是西南大医院的神经内科医生,博士。他把大脑里每一根神经当成高速公路网那样去研究,怎么能不堵、堵了怎么修,说白了,是让神经都舒舒畅畅的,精精神神的。
当晚,我们三五个人又去了大排档,是在一个朋友住的小区后门,也就是坐着吹吹风。
每人只要一杯扎啤、几根串串,顺便也等一个朋友的老婆下夜班。
我们才喝到半杯时,老段来了。他跳下出租车说:“好了好了,不跳了,稳住后我觉得还是得找大家,特别是师弟,喝点儿啤酒漱漱口。”
虽是初次见面,老段说的那些话,原来都不是“酒桌话”,而是真性情的心里话啊!
他刚坐下,又站起来说:“这样,我先去买几根冰棍,下到啤酒里,这样高端大气。”
我赶紧起身陪老段,到路对面小卖部。老段站在冰柜前,犹豫了一小会儿,是冰棍还是雪糕呢?最后他来了一句:“软的那种。”老段不晓得这里叫什么,老家是叫雪糕的,像雪那样柔软,还有奶油,比雪白,比花甜。
他先剥开两根雪糕,递给我一根先吃起来,再抱着五根,慢慢回到大排档。
老段说:“小时候,家里穷,哪里吃过软雪糕啊!都是五分钱一根的硬冰糕。上了大学更穷,连一根硬的也舍不得吃了。”
那个雪糕冰镇啤酒的夜晚,真的很高兴。我们等到一个朋友的老婆下夜班才散。老段跟那个朋友说:“兄弟,你等你老婆,是放着岗让她查,还是脚踏实地的爱?”我那朋友说了一句话:“兼有。”老段笑了一下说:“单线条比较好,不交叉,不然容易堵。”
告别时,老段拉着我抒情:“师弟,我对南京有感情啊!虽然,我没有在那个城市吃过一根雪糕,软的硬的都没吃过。”
中间,我们用微信联系了几次,老段很不“单线条”,说他除了给人看病,还在攻课题。老段嫌微信上打字慢,干脆电话拨过来说,课题一弄,人就兴奋起来,睡不着觉了,这些东西啊,真是好玩儿。“神经系统是一个比高速公路网复杂一亿倍的东西,我的脑细胞就是在头皮上、脸上给这些课题弄死的,小炮弹一样,炸得脸上坑坑洼洼,显老。”
一些大大小小的节日,我们也会互致问候。有一次,他用错了一个标点,可能他还在研究人的神经为什么会有迟钝反应,为什么有犯错意识吧。总之,他的短信原文是:“师弟,端午快乐?”
看到了这个问号,我心底漾笑,这真是一个欢乐的错误、欢乐的祝福。不信,你琢磨一下,特别有老段的意蕴,可以换成这么一句:“端午了,你是快乐还是不快乐呢?”
又一年冬季,老段约我到南滨路吃“顺风188”。又是一桌人,有男有女,算是事业有成的人,是在旅游大巴上或一次偶然的问诊中认识的。还有的是夫妻档,老婆在南京念过书,他一定让人家把老公带着,说不然会误会,会堵的。
第四次吃饭,就在前不久,我约的老段,到“加州花园”吃老火锅。老段又是穿短袖衬衫,脖子下解开双扣,又是趴满豆大汗珠,他总是那么努力地准时。
我们喝得满桌底凌乱的啤酒瓶,老段说,他得去个厕所,歪歪斜斜的,很像个醉样。
他竟是伪装去买了单。
我狠狠地怪他,老段来了一句:“我对南京有感情,谁买不一样啊!”我笑着问:“师兄呀,你是不是曾经有一段很美好的感情,搁在南京?”老段认真地说:“没有,没有,不然多堵啊!其实,我跟你说呀,要不是去南京念大学,可能留在山西老家挖煤了。我就是觉得,人不能忘记自己改变命运的时光。”
看来,老段没有醉,或者说,他真的醉了。
如今,我早已離开了那座城市,来到南京附近的一座城市打拼,还常跟老段联系。老段最深情最有诗意的话,也是在一次喝完酒之后的夜里说的。他说:“师弟啊,我又是帮人看病,又是研究神经高速公路课题,比较忙。等你有空了,帮我踩一脚油门,到南京地界,帮我看一看,南京……往事!”
[责任编辑 吴万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