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罗宗强先生印象
高克勤

罗宗强先生(1932-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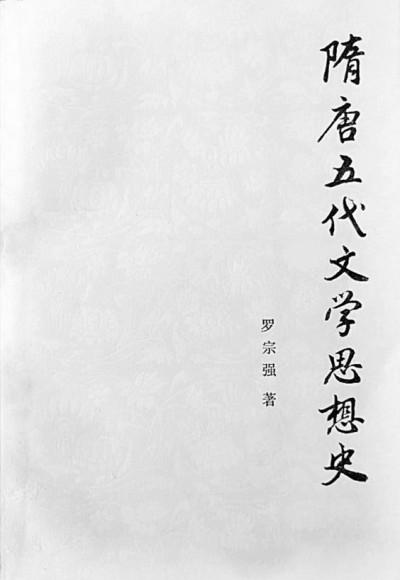
上古版《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
对于编辑来说,工作中最快乐的事莫过于发现一部好书稿、一位好作者,以及书出版后得到好的反响、作者成了知交。对于我工作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和我来说,已故的罗宗强先生(1931—2020)和他的著作《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就是这样的好作者和好书。
《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出版前后
记不得是什么时候、什么场合第一次见到罗宗强先生的,但知道他的名字、读他的著作很早。1983年9月,我开始随王水照先生研读唐宋文学,有了研究生助学金,像贫儿暴富似的,开始买我曾经想读想藏的书,其中就有罗宗强的处女作《李杜论略》。该书1980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买的是1982年第二次印刷的版本。这部不到20万字的著作是拨乱反正后第一部全面客观地比较李白与杜甫的专著,表现出作者对李白、杜甫作品的深刻领悟,其中“李白与杜甫文学思想之比较”已是作者首开文学思想史研究之先河的牛刀小试。
1986年7月,我研究生毕业后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不久就读到了次月本社出版的罗著《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本35万字的书开拓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在学界对这本书已有定评的今天,有必要回顾这本书的出版经过。
据罗宗强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所述,他在1982年完成这本书的初稿,而起念则在1979年。写这本书的由来是,他“有感于我国古代文论中一些基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不易确切理解,便想来做一点释义的工作,考其原始,释其内涵,辨其演变。于是选了二十来个常用的概念,如兴寄、兴象、意象、意境、气、风骨、势、体、调、神韵等等,多方收集资料,仔细辨认思索。但深入下去之后,便发现这实在是一件不自量力的工作。其中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基本概念的产生,都和一定时期的创作风貌、文学思想潮流有关。不弄清文学创作的历史发展,不弄清文学思想潮流的演变,就不可能确切解释这些基本概念为什么产生以及它们产生的最初含义是什么。因此,只好中止了这一工作,而同时却动了先来搞文学思想史的念头。这又是一件很吃力的工作,只好从比较熟悉的隋唐五代开始”。
1982年3月28日,罗宗强致信上海古籍出版社副总编辑汪贤度(1930—2017),信中说:“赐示多所鼓励,至为感谢。拙著《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正在撰写过程中,殊无把握,蒙关心,并嘱完稿后送贵社,更觉不安,故迟迟未奉复。撰《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为愚思虑再三之后之选题,有生之年,当努力完成此一选题,更无力他顾。而工程甚大,故拟分阶段进行。第一册即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现已至由盛而中转折时期,观点大抵与他人异,盖或亦因着眼点在文学思想之发展,而不在某一人上,出发点不同,评价亦异之故。此册明年上半年当可脱稿。脱稿之后,当奉上求教,非敢望一稿成功,意在求得教正,以便修改而已。届时如或尚有可取之处,而蒙接受出版,则当大出所望也。明年下半年当转入魏晋六朝文学思想史之撰写。此段甚为重要,而愚于此段比较熟识,可能会较顺利些。将来费力之处,当在先秦两汉部分。但此是后话,届时再说吧。”汪贤度1958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一直从事编辑工作,当时分管以古典文学典籍整理出版为主的第一编辑室。他将此信收文后,当时分管以古典文学论著出版为主的第二编辑室的副总编辑魏同贤(1930—2015)即批示:“此选题好,作者亦有相当水平,请二编室研究可否列入规划?”魏同贤1953年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也长期从事编辑工作,曾负责上海古籍出版社《陈寅恪文集》的编辑出版。二编室即发信给罗宗强,请他完稿后寄来。
1984年3月28日,罗宗强致信上海古籍出版社,告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书稿事。同日,他有一信致好友杭州大学中文系郭在贻(1939—1989),谈到寄书稿事:“拙著已于本月24日寄出,寄上海古籍二室。并给汪贤度同志一信(有一般通信关系,未见过面),此外该社无一熟人。兄有可能,望代为推荐扶持。此书以文学创作倾向与理论批评相印证,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之发展,不以人为纲,而以文学思想发展中自然形成之时间段落立章。就弟所知,此种写法之断代中国文学思想专史,国内外至今均未见。水平虽不高,但写时是认真的,力求做到凡言必有据。另有两家出版社想出,但考虑到上海古籍的学术地位,弟还是冒昧送上海古籍。兄若能推荐,当于该社审稿时有影响。”(《郭在贻文集》第四卷,中华书局,2002)郭在贻此时已有论文集《训诂丛稿》为上海古籍出版社接受(次年出版),故罗宗强信中有“望代为推荐扶持”之语。
《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书稿到后,编辑室安排王勉(1916—2014)审稿。王勉是一位资深编辑,上世纪三十年代就读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对中西文论都有精深的了解。他审稿后,提出了翔实的意见,除了肯定书稿的独创性价值外,也对书稿的不足和体例提出了修改意见,主要有如下三点:“1.全部目录改写,删除空泛提法,突出论述的内容。2.增加引言一篇,阐明本书主旨,最好能扼要地把本书论点的轮廓勾勒出来。3.对于诗歌部分,过多的作品介绍作适当的删节。”罗宗强接受了修改意见,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后记中写道:“出版前,又承上海古籍出版社同志提了很好的意见,‘引言就是接受他们的建议而写的,同时,改动了一些章节的标题,作了一些删节,使全书眉目更加清楚,这是我所衷心感谢的。”三十多年以后,他还铭记在心:“我的一本《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1986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因考虑到这是准备编写的《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中的一册,为了以后与编辑部联系方便,希望就近转到中华(书局)来出。我征求了傅(璇琮)先生的意见,也征求上海古籍出版社方面的意见。蒙上海古籍的领导和编辑给了很大的照顾,同意了。他们为此书付出了许多心血,要把此书转走,我真是有些不好意思。”(《学人的学术家园》,《中华读书报》,2012年03月28日)
值得一提的是,几年前,我去四川大学拜访项楚先生,说起出版往事,他说当年是他向罗宗强建议投稿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因为该社编辑有眼光。项楚当时已在《中华文史论丛》发表有关敦煌学的论文,在学界崭露头角。他与罗宗强是南开大学中文系系友,他1962年毕业,比罗宗强低一届。他大学毕业后考取四川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从庞石帚先生治六朝唐宋文学。罗宗强大学毕业后则考取本系研究生,从王达津先生治中国文学批评史。就在罗宗强寄上海古籍出版社《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书稿的同时,上海古籍出版社也约项楚撰著《王梵志诗校注》。《王梵志诗校注》经过作者和编者长达八年的打磨,于1991年底出版。这部著作在校勘和注释中将语言、文学、宗教融会贯通,开创了大量利用佛教文献进行中古汉语词汇诠释的先河,成为这一研究领域杰出的创新之作。《王梵志诗校注》的责任编辑是年长项楚二十岁的资深编辑陈振鹏(1920—2005)。有意味的是,二十多年后,项楚《王梵志诗校注》和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先后获得第一届和第二届思勉原创奖。
佳作迭出
《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完成后,罗宗强紧接着又花了八年时间撰写了近35万字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1996)。这书真是写得他“心力交瘁”(《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后记》)。因为他觉得“魏晋南北朝这一个时间段落,实在是我国文学思想史上异样的,又是十分重要的时期,许多的问题,如何认识、如何评价,似都需要重新回答。尤其是《文心雕龙》,既艰深复杂而又隐约朦胧,把握不易”。他“有三四年时间,就在《文心雕龙》上徘徊,一遍一遍地读,一遍一遍地想,把它放到当时的文学创作实际中考察,把它与当时的其他批评家比较,当然也读已有的研究成果。终于慢慢地有了一点看法,觉得这《文心雕龙》所表述的文学思想,并非如学界所曾经认为的那样,与其时之文学主潮异趣,它们之间,其实是一致的。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才逐步梳理它的理论的脉络,写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同上)后来,他把研读《文心雕龙》的十几篇札记集为《读文心雕龙手记》(三联书店,2007)一书。
在写《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时,罗宗强感到,有一个问题是他无法回避的,“这就是魏晋士人心态的巨大变化。魏晋文学的新思想潮流,说到底,都与士人心态的此种巨大变化有关”(《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后记》)。于是,在写文学思想史的同时,他又断断续续花了四年时间写了近30万字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一书。他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魏晋和晚明,似乎是两个有些异样的时期。士(或者说是那些引领潮流的士人)的行为有些出圈,似乎是要背离习以为常的传统了。而此种异样,于文学观念的变动究有何种之关系,则黯而不明。于是产生了来探讨魏晋士人心态的想法,目的只是为撰写《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做一点准备。”(《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再版后记》)这本作者自谦为“副产品”“准备之作”的书写得真是精彩,对士人心态的分析鞭辟入里,正如傅璇琮在本书序中所说:“读着读着,感到极大的满足,既有一种艺术享受的美感,又得到思辨清晰所引起的理性的愉悦。”年近八十的程千帆先生1991年7月14日致罗宗强信,谈读这本书的感受:“顷奉论魏晋士人新著,弟比岁以来,已若枯木朽株,诚所谓不知有汉,遑论魏晋者。今得大著启沃之。亦庶几死井中起微澜乎! 尊著精妙,多有昔儒今彦屐齿未及之境。如此著书,不特有益于今人,且有恩于古人也。”(《闲堂书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这本书为历代士人心态研究开了先河。
此后,罗宗强又花了12年时间撰写出版了六十余万字的《明代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2013),以及四十余万字的《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在《明代文学思想史·后记》中,他感叹道:“终于把这个题目做完了。十二年,日日夜夜。其间为这题目的研究做准备,写了《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但大量的精力,还是耗在了材料的阅读上。即以别集为例,不读不放心,读了与研究题目有关的十不得一。十个别集有九个属于白读。我研究的是文学思潮的发展,总想了解其时之文学思潮究为何种之面貌,与该面貌无关的创作与理论批评,一律舍弃。大量的理论批评,多属陈词滥调,前人已反复言说,明人再说一遍,并无新意,亦无理论价值。当然,经过大量的阅读,对于明代文学思潮发展的环境氛围,还是有一个感性的认知,还是有益的。”由此可见作者治学的踏实和艰辛。这时他已年过八旬了,他还感叹道:“已到风烛残年,像这样的研究,以后是不会做了。回顾一生,感慨万端。一个人的一生,所能做到的毕竟极其有限,何况其中又有十几年时光在莫明所以中虚度。……可自慰的是,我此生努力了,勤勤谨谨,不敢丝毫懈怠。”确实,罗宗强是勤奋的,仅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三十多年间,他就奉献出如此多的足以传世的佳作,这在当代学人中是不多见的。
同道相应
我与罗宗强先生开始交往是在2004年。2004年2月3日,罗先生写信给我:“奉上千帆先生信函三件,请审处,看能否编入程先生书信集中。去年陶先生曾来示征集千帆先生信函,其时弟因搬家,杂乱不堪,不少师友信件均已遗失,无法应征奉寄。近日忽从积稿中发现程先生信三件,喜出望外,重读这些信件,先生之音容笑貌又如在目前,思念之情,不可已已。程先生来信不止此三件,但其余均无法找到了。记得一九八九年有一长信,感人至深,至今只存记忆了。”2月16日,他又给我一信:“近日又从杂书中发现程先生信函三件,现奉上。当已无法编入,只是请先生便中一读,知有此事。其中第一封是程先生赠我一册‘程千帆沈祖棻学记,弟以为此书乃先生治学之精华所在,程先生就此复信者,中言及他之所重亦在于此,从中可以看出程先生之学术思想之倾向。”先一年,为纪念程千帆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程先生夫人陶芸编了程千帆书信集《闲堂书简》,由程千帆先生弟子程章灿教授与我联系。罗先生寄来程千帆信时,这本书已出校样,于是我将程千帆信寄给程章灿编入书中,赶上了这本2004年7月出版的书。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到程千帆与罗宗强的同道相应。
程千帆1986年12月30日致罗宗强信:“承赐新书,拜读感佩。仓卒不能尽其妙,然致广大尽精微兼而有之,则校然矣。居尝窃念文学批评史之研究方法,今日似已入穷途,即有从理论与理论之间架设空中桥梁,居然自成框架与体系,而其来源自创作之变化、在文化背景之差别,则弃置不一探索,诚可惜可叹也。先生之书,诚所谓独辟蹊径,扫空凡俗者。”这是程千帆对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的高度评价。
程千帆1998年1月6日致罗宗强信:“《学记》承奖饰为愧,然亦深叹公之知我。盖平居最慕能开风气主持风会之前辈,然心有余而力不逮。惟先生能道破其所祈向,此所以特为心折也。”对罗宗强能领会自己的学术祈向,程千帆由衷地表达了欣喜之情。
与罗先生通信之后,他接连寄赠其著作给我,当月寄赠的就有旧作《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和新版《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此后又陆续寄赠新作《因缘集:罗宗强自选集》《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读文心雕龙手记》《晚学集》《明代文学思想史》。
2006年9月20日,罗先生给我一信,信中说:“弟因急需《全明文》与《全明诗》,令人惊异的是二书南开图书馆竟然都未购进,弟从杭州天目山书店邮购得全明文第一册,其余各册与全明诗均遍访不得。今日汇款三百元至贵社发行部,求购全明文第二册(弟不知已出至几册)和全明诗第一、二册(未知出至几册),并购近出之《明代驿站考》。全明诗与全明文极难觅,先生能否请库房想法找出一、二册。”他还告诉我:“(天津)古籍书店离学校远,购书者不多,因之贵社书常购不到。”当时,罗先生正在系统阅读明代文学资料,撰写《明代文学思想史》。《全明诗》已出版三册,是1990、1993、1994年先后出版的;《全明文》已出版二册,是1992、1993年先后出版的,都是十多年前的老书了,社里已无库存。于是,我将自藏的《全明诗》三册和《全明文》第二册寄赠罗先生。能为作者提供一点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也很高兴。
2006年9月,我将拙著《王安石与北宋文学研究》寄罗先生求正。先生收到后,回信鼓励道:“先生研究从实处着手,扎实细致,非虚空立论者可比。”又言:“以前学界有海派与京派之说。以弟观之,年来海上学人治学,严谨扎实,海派实从前京派作风;而京派几成数十年前之海派矣,一笑。”
罗先生工书善画。他早年在家乡广东揭阳师从岭南派画家陈文希、黄独峰习画,有扎实的笔墨功底,有很强的艺术领悟能力。这对他后来研究文学作品应该有很大的帮助。晚年他重拾丹青,又将大半辈子研究文学作品的心得融入绘画的艺术境界。读他的画,在色彩斑斓绚丽的岭南画派风格中,更洋溢着盎然诗意。2009年,罗先生寄赠他和夫人王曾丽合著的《罗宗强王曾丽画作》。王曾丽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长期从事中学教学工作。此后不久,他又应我之请,寄我一幅他画的荷花图,还题诗道:“一自斜风细雨后,淡香入水亦婆娑。”
我知道,罗宗强先生对我的关爱,不是纯然出于私谊,而主要是出于对上海古籍出版社及其编辑工作的肯定和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