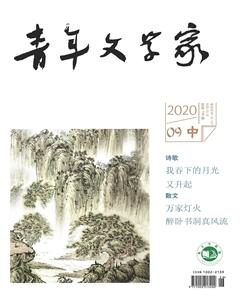《界》与《尘埃落定》家族叙事中互文关系阐释
摘 要:通过考察《界》与《尘埃落定》家族叙事的异质性缘起,发现人物在形象塑造、悲剧起源、行为意志上呈现出一致性,构成小说文本的显性互文特征。本文采用戏仿、隐喻、拼贴等互文手法,解构经典人物,探析藏族家族史中痴愚者对诗性精神的追溯、人被权力物化的命运以及女性悲剧的深层根源。
关键词:《界》;《尘埃落定》;互文性
作者简介:范佳(1995.6-),女,汉族,宁夏吴忠市人,北方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2018级研究生,研究方向:多民族文学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6-00-03
克里斯蒂娃在其著作《符号学,语意分析研究》中提出“互文性”概念,任何文本都是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改编[1](P36)。其内涵是说每个文本都与其他文本处在相互吸收和转化中,事件、人物、话语、感觉的重复出现,构成了文本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的互文性指涉关系。互文性理论至今,各国学者做过不同的阐释与补充,逐渐形成广义到狭义两种方向的变化,广义互文性即解构批评方向,代表人物主要有德里达、米勒等人,主要关心如何通过互文性手段破坏文本的既定结构和认知范式,使所有文本解读无限地指向边缘;狭义互文性即诗学方向,代表人物有热奈特,趋向于对互文性概念做出精确的界定,使其成为可操作性的描述工具,分析一个文本对其他文本的引用、戏仿、改写、抄袭、套用等互文策略[2]。《尘埃落定》与《界》作为书写藏族家族历史的经典小说,以三代人的生活面貌,反观藏族社会结构与民族心理。本文从狭义互文性入手,为阐释《尘埃落定》与《界》中经典人物形象的反叛与重构提供可能,促进人物精神内涵的深层挖掘。
一、戏仿:痴愚者的归宿
在后现代语境中,戏仿通过戏谑的方式对前文本进行摹仿,以颠覆了神灵和英雄人物的崇高化呈现开始。故事中的荒诞性与虚幻性,以及结局的超脱,都呼应了痴愚者对新生事物的追随,实现了对传统英雄人物的戏拟与反写。
《尘埃落定》中“傻子”少爷,在权力关系中颠覆了英雄人物应具备的力量与雄壮,凸显出“智与愚”的辩证精神,是在当代文学史上极具成功的典型形象。在《界》中,身份上和“傻子”少爷匹配的是“格日旺久”少爷,其形象延伸了“傻子”少爷的世俗性,腿有点罗圈,身上长满虱子,在拉萨为权力欲望谋个官职,侵占仆人查斯的身体,在拉萨嫖妓等。相同的身份,次仁罗布并没有在他的身上花太多心思,挖掘其内在精神的缺失和被物化的命运,而是在和他有亲密联系的管家、查斯的独语中,侧面描写他的行为意志和心理失落。但这样两个人物,意外让我们看到了藏族传统文化中对“智与愚”的辩证观。所谓“智”并非追求权力关系的绝对拥有,“傻”也并非是生理上的缺陷。次仁罗布有意将傻子少爷“神性”的一面遮蔽,做出“修改”和“误读”,主要表现在政治层面上,格日旺久被塑造为一个愚者,他没有像“傻子”少爷一样,能在边境建立自由贸易区,获得百姓的爱戴;也没能在拉萨政府青云直上,获得高官。相反他很狼狈,甚至被作者逼到了道德谴责高地,用权力倾轧查斯,加深查斯的仇恨和生活的苦难。同时他也是个软弱的人,无力反抗岑啦老太太的控制,官场失意就整天在喝酒嫖妓,道德意识上呈现出为富不仁的麻木状态。
次仁罗布和阿来对“智”的审美追求应该是诗性思维的培养,强调内心世界的纯正自由。人类早期认识世界的起点是从感性出发,将一种自然、理想的状态投入社会生活中,“傻子”少爷心思单纯,能超然物外看到被世俗生活拖累的人们,也能发掘出人性善的一面。更为深刻的精神联系应该是格日旺久与仆人查斯的儿子多佩。多佩自小随母亲查斯、驼背父亲罗丹在娘村生活,七岁时被老太太岑啦送到寺院剃度,相较于母亲的仇恨,他是在看到人间的疾苦,自愿待在寺院的,最后在预见母亲想要毒死自己的时候,依然选择接受死亡,劝母亲放弃仇恨。“傻子”少爷也是一样的命运,受家族间权力相争所迫,最后平静的等待仇人儿子的刺杀。他们都为置身历史的洪流无能为力,看到世间物欲对人性的扭曲和精神冲击,想要回归灵魂的安稳之乡,追求内心世界的平和與宁静。作者以文化视角介入,“傻子”少爷、多佩与格日旺久形成对立,消解了权力对人生的决定作用,揭示了“傻子”少爷之所以受民众爱戴,能在生活中处处展现过人的才能,并非是权力的获得,而是对诗意生活的有意追寻。
反观“傻子”少爷与多佩的结局,无论是被仇杀还是被毒杀,施加伤害的他者都很耐人寻味,一个是酒馆里的朋友,一个是自己的母亲。他者被仇恨蒙蔽,在传统观念的桎梏中无法获得出路,以极为荒诞的理由和扭曲的形式为自己寻找到得以发泄的方式。而被杀害者总是理想、自由的殉难者,以唤醒负重前行的劳苦大众。作者用他们的毁灭孕育新生事物的诞生,而痴愚的扮相正是为解构英雄人物的固定形态做出的戏仿,目的是重塑精神世界在物质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呼唤人性的回归,恢复人与人之间最本真的和谐关系。
二、隐喻:无形的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尘埃落定》和《界》中,无论是弄权者还是下层百姓,都有种无形的力在推动着每个人的命运,龙扎谿卡庄园里的“弄权”者,代表人物有噶厦政府的老爷们、德忠府的老爷和夫人、老太太岑啦、格日旺久少爷等,老太太为在拉萨帮格日旺久少爷谋个职位,花大量的钱去贿赂德中府和噶厦政府的老爷们,德忠夫人怕失去岑啦每年提供的食物对少爷照顾有加,他们在权力关系中各取所需,维系着你来我往的平衡。龙扎谿卡庄园还存在着生存空间“被挤压”者,代表人物有管家桑杰、女仆查斯、驼背罗丹等,桑杰跟着格日旺久一起长大,见惯了少爷邋遢的样子,这让他对少爷莫名有一丝好感,时不时捉弄他一下。这里和《尘埃落定》中“傻子”少爷的玩伴索朗泽郎对应,桑杰似乎更为聪明一些,在权力的夹缝中生存,听从老太太的指示,怂恿少爷和查斯来往,又帮罗丹争取到在娘村永久生活的机会,他似乎在满足所有人的要求,力求事情办得妥帖,因而能在家境窘况的情况下,还能得到老太太的庇护,做了管家。而索朗泽郎是性格执着,但缺乏独立思考的英雄,他可以不问缘由帮“傻子”少爷追杀敌人,内心的认知让他必须这么做,这是他的命运。
面对这种无形的力,阿来将其放置在历史意味中,描绘痴愚者的画像,社会的群像被固定化,上层社会总是无形的压迫下层,无论是土司还是下层百姓,都作为一种权力符号被定义,其能指背后的所指是经济、社会、文化的畸形发展。次仁罗布以文化意味进行“改写”,以力的反作用,变形出特定历史主体、文化主体不同的人生选择,如果说《尘埃落定》里的人物被定型化和抽空化,集中展现了人物符码的唯一面目和标示,《界》对人物的“改写”则是将人物的“血肉”还原成人本来的样子。下层社会并非被冲淡,而是作为参与者解构历史的展开方式。政治身份与文化身份的人物同形异构,被赋予不同的内涵相互指涉。《界》中岑啦送礼打通关系时,管家插入这样一段自语:“新春丰收,按老太太的吩咐,我把粮食换成了大洋,再把沉甸甸的大洋哗啦啦地倒进牛皮袋里。那脆亮的声音让我心怦怦地跳,眼里荡满泪花。当时我还在想,花这么多钱去贿赂那些老爷干什么?龙扎谿卡和积攒的钱够少爷一辈子享用的”[3](P78)。次仁罗布用“界”这一经典意象使力的双方进入文化象征的层面,文本主题“界”的隐喻性延伸,化为有形和无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存在着“界感”。次仁罗布从龙扎谿谷息息相关的管家视角介入,借管家自语道出上层社会群体的生存面貌,借“力”的同时也被“力”支配。有形的界即人的层级划分,每个人的活动范围在一个框内,想要突破“界”需要打破既定的生态环境。当然,有形的“界”是具备弹性的,想要强行融入打破界限,权力、金钱就会在此野蛮生长;无形的界最难分明,也最容易形成习惯,不合理也会因为时间而变得合理。所以管家在多年后再见到少爷,有这样一段自白:“少爷见到我时只提及关于老太太的事,从不重温龙扎谿卡的那段岁月,我是仆,少爷是主,这界线我是很清楚的”[3](P79)。长期以来由权力和财富堆积的界线提醒着人有奴与主之分,无形的“界”可以将儿时亲密的友好关系变得有了屏障,格日旺久少爷也不再有儿时屙屎屙尿的单纯和自由。次仁罗布用“界”的隐喻性呈现,打破了权力结构的矛盾冲突,其目的是在思想疆域的不断扩充,主张情感力量的回归,呼唤人性的自然朴素美。
三、拼贴:女性悲剧的续写
《尘埃落定》与《界》中女性形象因历史文化语境的相似,在人物设置上呈现出顺应性互文关系,即互文的双方本质一致,意见相似。主人公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成为他们悲惨结局的基础。《界》中杰出的女性形象查斯,仇恨的一生都在重复自己母亲的悲剧。查斯的母亲跟着商队里的康巴人私奔到拉萨,后由于商队赶着去印度,就将生病的母亲留在了德忠府,商队再没有回来,母亲也一步步沦为德忠老爷的性欲工具,直到怀有查斯,马上把她许配给了厨师单增。查斯重复了母亲的悲剧,长期受到岑啦太太、德忠夫人的虐待和屈辱,被压抑的人性将希望寄托在了儿子多佩身上,希望能做主将多佩从咤日寺带回去,可造化弄人,多佩一心向佛,查斯如失智般毒死了多佩。追溯其原型,与《尘埃落定》里“傻子”少爷的汉人母亲身世背景上尤为相似,不同的只是身份地位,或者说“傻子”少爷的母亲更为幸运,在麦琪土司家生存了下来,为“傻子”少爷挣得了接触权力的机会。而查斯却没那么幸运,她的遭遇跟《尘埃落定》中女仆塔娜、桑吉卓玛一样,不会因为母亲和德忠府老爷的关系发生改变。相似的命运悲剧暴露了父权制关系的本质,被边缘化的女性长期处于失语的状态,被支配、被交换是他们普遍性遭遇。这种压迫性力量并非是一段关系造成,女性往往是刚摆脱牢笼又进虎穴,连起来是女性拼贴式的悲剧呈现,大致模式可以总结为“追求恋爱自由——被抛弃——仇恨挣扎——顺从命运”,三代人以拼贴手法并置在一起,互相独立又相互关联,记录了女性成长的精神历程。
纵观两位男性作家笔下对女性的描写,往往是父权统治下对女性身体和情欲的张扬。《尘埃落定》中麦琪土司看上了喳喳头人的女人央宗,以牺牲忠心耿耿的下属的方式霸占了她,将其作为征服欲的符号。在这之前罂粟花的种植让麦琪土司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原始的男子汉气概需要女性作为发泄工具,展现男性的魅力。央宗没有其他的选择,逆来顺受让她成为矢之众地,精神上的极度紧张使她承受不了压力疯了,她的出现对土司来说如昙花一现,在土司意识到自己不应该被女人裹挟之后,所有的狂热也就结束了。女性的价值和尊严得不到体现的状态下,作为弱势群体在阿来的笔下并没有展开其完整的面貌,她是央宗也是千千万万个父权社会下女性的生存群像。同样,次仁罗布在展现女性生存状态时也并没有脱离这一范围,算是对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完整记录,没有夸大也没有刻意回避。
不同的是,由于次仁罗布与阿来所采用的历史意识的不同,开始出现了早期女性追求自由恋爱,反抗生活的意愿。次仁罗布采用新历史主义视角,在文化思想領域对社会制度所存在的政治思想加以质疑,这种“小历史”意识颠覆了阿来“宏大历史”意识,在文化碎片的夹缝中互文于女性被遮蔽的历史。《尘埃落定》中女性在被长期挤压的生存环境中,展现出对权力的狂热追逐,想要在男性话语中寻找自身存在的意义。“傻子”少爷的妻子塔娜,是美与爱情的象征,良好的家世和动人的相貌是男性追求的目标。她在茸贡家族遇难的时候和“傻子”少爷联姻,带着政治性任务而来,为的是获得更多利益,男性成为她生存的对象和阶梯,可以随时背叛。这样的女性悲剧性是无法改变社会力量的制约,也没有认识到自身主体性的缺失。《界》中的女性从查斯妈妈到查斯,为了爱情和自由“出走”,寻找女性理想生存的方式,查斯妈妈一直等商队回来救赎她,逃离苦难的生活;查斯在娘村等待格日旺久少爷能带她回去,没有结果后又等待自己的儿子多佩能从寺庙回来照顾她,等待贯穿了她的一生。两代人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也没有走出女性“乌托邦式的幻想”。因此,他们虽已初具追求独立自主的意识,却缺乏个体生命本位意识的彻底性。一代代女性悲剧的现实铺就了女性成长的艰难道路。
本文从互文性批评视角入手,研究当代藏族作家阿来与次仁罗布民族文学创作,具体阐释文本在消解传统中对传统的发现。当文本进入更为广阔的文化空间,文本本身对其他文本的借鉴与转化,构成了本文《界》对于《尘埃落定》新的意义阐释,同样的家族历史兴衰过程,不同的话语建构对历史的解读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样态,通过互文性策略中戏仿、隐喻、拼贴等手法的运用,主要是为了还原了历史进程中人物的本来面貌,打破定型人物的固定形态,将血肉丰满的人物相互补充完整。
参考文献:
[1]Julia kristeva.“Word,Dialogue and novel”,in The kristeva Reader,Toril moied,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 Ltd,1966.
[2]王瑾.互文性[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次仁罗布.界[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1.
[4]阿来.尘埃落定[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