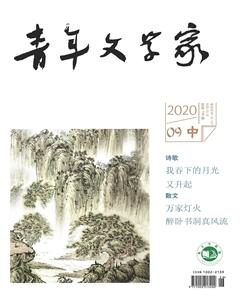万家灯火
王凤
醋坊
最近,我时常会做一个梦。梦里,我看见一间红砖堆砌成的石棉瓦房,房门口立着一块木牌,木牌上工工整整的写着几个毛笔字:老张醋坊。
这间醋坊是一个老头开的,镇上的人都叫他老张。在我心里,老张是小镇上最有学问的人,街坊邻居办红白喜事的时候,必然会找他帮忙挂簿子。每一次,我远远地就能看见,老张穿着一件青色中山装,戴着老花镜,用一支细毛笔专心致志的做礼金登记。老张是左撇子,他的肩膀一只高一只低。小的时候,看到老张用左手写字,我常常问,为什么他跟我们常人不一样。每一次,老张都闭口不谈,只是轻轻地微笑,一如既往地塞给我两颗珠珠糖。后来,我听镇上老一辈的人说,老张的右手啊,在他年轻的时候,被他亲生弟弟用猎枪打残了。如今,那个位置,依然还有一个触目心驚的凹坑。
小时候,我特别爱去老张家的醋坊。每次一去,老张一边捣鼓着用来制醋的谷物,一边给我讲故事。他会给我讲《西游记》,讲《割肝救母》,偶尔还会给我唱两句《四郎探母》,闲暇的时候,他会教我写写毛笔字。老张一生无儿无女,他的老伴儿几年前死于一场疾病。有一次,老张挽起袖子酿醋的时候,我又看到了他手上的凹坑。我好奇的戳着那个伤口说,老张老张,你给我讲讲这个凹坑的故事吧!这一次,老张依然没有开口。他拿起酿醋的酒药小心翼翼地放在我手里,我听见他在我耳边说,每个人呀,都有自己的一个小秘密。
我唯一一次见到老张哭,是在我十四岁的时候。那天是重阳节,妈妈让我给老张送去一碗腊肉。推开他家门的时候,我看见老张蜷缩着身子掩面哭泣。如果说,人生在世非要记住点什么,我觉得,老张哭泣的样子,足够我记一辈子。老张抽泣着对我说,我梦到他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终于梦到他了。之后,老张告诉我,他想去一个地方。那时已是黄昏,夕阳散发出釜底抽薪的红光。老张在前走,我一步一步踩着脚印跟着他。走到小镇上的一个湾潭时,老张停下了脚步。他自顾自地说,就是这里,就是这里了。
那个黄昏,我知道了老张手臂上凹坑的故事。在老张二十多岁的年纪,他的亲生弟弟用猎枪打伤了他。当他那只手臂永远失去知觉的时候,他咆哮着对弟弟说,他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今生今世都不想再见他。他的弟弟痛哭着给他下跪,之后摔门而去。第二天,人们在湾潭发现了他弟弟的尸体。所有人都说,老张的弟弟是溺水而亡,可是只有老张知道,他的弟弟遇水就会变成一条鱼。这条鱼啊,能游得很远很远,游向大海,游向天边,游向一望无垠的星际,游到他清澈而温润的眼睛里。
写到这里,我揉了揉湿润的眼角。兴许,是我太想老张了。他死后,老张醋坊被重新翻修了,如今,那儿变成了一个宽敞明亮的小超市。太久了,关于醋坊,关于老张,关于他所有的事,都已经在我记忆里开始泛黄了。我开始越来越想不起他的模样,我真怕我会忘记他。翻修老张醋坊的时候,我把那块木牌带走了。上面那几个字,写满了老张的毕生。我突然好想回到过去,我想回到小镇,我想闻闻酒药混合着谷物发酵的味道,我想摸摸醋坊陈旧、积满醋垢、黏糊糊的柜台,我想再听老张讲一遍他年轻时候的故事,以及,我想看他再酿一次醋。
我把一部分的自己留在了那间醋坊里,坊外立了碑,碑上刻了我的名字。
我忘不了也不能够忘记。
七里
第一次见到七里,是在我回家的路上。透过车窗,我远远地就看见一只圆鼓鼓的小黑球。二叔把车停靠在路边后,我走近一看,呀!居然是只小狗。当我和七里对视的时候,透过它的眼睛,我仿佛能看见一汪清泉。那种干净、那种纯澈、那种空灵,都是我从未见过的。于是,我对着它,轻轻张开了双臂。我想,我永远也忘不了,七里奔进我怀里时的样子。它迈着小短腿,吃力却又那么努力地跑向我。它舔着我的手心,发出微小而软腻的叫声。我摸着它的小脑袋心疼的说,别怕,我带你回家。
七里是只雌性德牧。它是在离我家大约七十公里的地方捡到的,所以我们都叫它七里。刚到我家的七里,没有表现出半点不适应,我给它什么,它就吃什么。晚上,我妈用纸箱给七里做了一个窝。我指着纸箱告诉它,以后啊,你就睡这里吧!七里像是听得懂一样,我把它抱进纸箱里,它不闹也不叫,乖乖地就躺下了。可是,当我家熄灯的时候,七里就开始呜咽。我知道这种声音意味着什么,七里害怕,它没有半点安全感,它害怕再次被抛弃。打开房门的时候,七里就坐在我的房门口,我小心地抱起它。我说,七里别怕,以后我就是你的家。
一到放学这个点,七里总是乖巧地守在门口。我一进门,它就开心地摇着尾巴往我身上跳。外婆说,这狗啊,是有灵性的,谁对它好,谁对它不好,它都知道,而且它会记得清清楚楚。我刚带七里回家的时候,我爸其实是不同意养的。他说,七里稍微恢复一点,就把它送走。我抱着七里哭,我说,七里走,我也走。现在想来,那时自己浑身散发的勇气,是我如今可望而不可求的。七里懂事,每次爸爸回来,它都会欢快地跑过去,亲昵地蹭着爸爸的腿。一开始,我爸会把它推开,可是时间久了,次数多了,他反而接受了七里。你看呀,无论你的心里曾经多么冰天雪地,总有人、总有个生命会慢慢将它温暖、融化。我始终相信,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一匹骏马,无数黑暗过后,它才会姗姗来迟。所以,他一定会来,你一定要等。
十八岁那年,我来到了昭通。要走的那天晚上,我紧紧地抱住七里。我说,七里,我很想带你走。七里,你会不会想我。七里,你要好好陪着我爸妈。七里,下次见面时,你一定要长得更大些。我自顾自地说话,自顾自地流泪。七里伸出舌头,舔干我脸颊上的泪水,像是在安慰我一样。车发动的时候,七里发了疯的一阵狂叫。我爸用链子拉着它,让我赶快走。那是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听到七里叫得那么伤心。我强忍住泪水告诉自己,所有的分离都是为了下一次相遇。七里啊,你不用送我,我一个人走。
大二那年,我爸欣喜地告诉我,七里要做妈妈了。我想象着七里的孩子,它们一定和七里长得很像。有着七里好看的眼睛,挺立的双耳上有几根卷毛,背上是那种纯净的墨黑,胸前有一撮黄色。我盘算着放寒假回去,我要给七里买许多好吃的,还要给她的孩子买很多玩具。然而我说过,未来,真的不能一眼看到头。接到我妈电话的时候,昭通已经进入了十一月份。我妈说,七里死了。我裹了裹身上的大衣,语气坚定地说,我不信。电话那头,我妈哭得歇嘶底里。良久,她缓缓地说,真的,七里难产死了。无论过了多少年,我永远记得听到这句话时,我是什么感受。眼前突然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整个世界与我无关。心口处,我找不到出路,我的灵魂,找不到出口。那种感觉,就像被巨大的空洞,正在一点一点地吞噬了一样。就连泪水,都是苦的。就连呼吸,都感觉是痛的。
其实,我一直想知道,七里死的那一刻,究竟有没有想我。想起我刚遇到它的那一天,想起我抱它回家的时候,想起我们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七里啊,你有没有遗憾,我们没有见到最后一面?其实,我心里早已经有了答案。如今啊,我总是会想起第一次见到七里时的样子,它那么小,身体那么温暖。它爱舔我的手,最爱吃面包和香蕉。那时,我才开始明白,真正的离开是没有道别的。
可是,我还没来得及好好看你一眼,跟你认真道个别,说声下辈子见。
七里,我会等到你吗?
七里,我一定会等到你。
枯井
十八岁那年,我孑然一身来到昭通。一个上午,我坐上4路公交车从学校出发,在清官亭下车后,一个人走完了罗炳辉广场、夜市、抚镇门以及洋人街。之后在一家没有人的小店,读完了半本《包法利夫人》。回学校的时候,昭通的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这才想起角落里那把坏掉的格子伞。走到行政楼对面时,我看到一个被风吹倒的宣传栏,我慢慢走近,小心翼翼地将宣传栏扶了起来。看着宣传栏上一个个闪耀而跳跃的字,我深吸一口气,思绪飘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初中的时候,我是一个心理极度不健康的孩子,不喜欢人群,不喜欢鲜艳的颜色,不喜欢说话。那时候的我,喜欢黑色与灰色,喜欢衣柜等拥有狭小空间的物体。由于长期的自闭,我只能把自己镶嵌在文字的世界里,因为我总能在文字里看到自己的影子。无论过了多少年,我永远记得,初三的一次语文课,我的语文老师让我起来念自己的作文。他说,看了这么多届学生的文章,唯独我的这一篇让他记忆深刻。我在课堂上用标准的普通话,轻柔地念着我的作文,念到一半时,我突然声音哽咽,一时之间失声痛哭起来。面对九十多双眼睛对我的投射,老师为我打了圆场。他说,你们看,真正好的作文,不仅能感动到别人,最重要的是能感动自己。
好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那个瘦瘦高高的男老师。他其实不知道,我当时突然失声痛哭,是因为,从我懂事开始,就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坚定的认可我、肯定我、选择我。他用他的手掌,呵护了一个敏感而脆弱的少女,强烈的自尊心。
昭通的风把我拉回了现实,我抱紧双臂从宣传栏的旁边走过。我在心里问自己,是有多久没提起笔写字了。回到宿舍后,我拿出信签纸,无比认真地写下了,我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散文——《惜光》。事到如今,我依然能记起,一个长发齐腰的女子,在三食堂门口,垫着脚尖,把几页写满正楷字的信签纸,慎重的投进信箱里。那天,微风恰好吹起她烟熏色的棉麻长裙。
《惜光》讲的是我和一个回族女孩的故事。里面有句话,就像是我手心里的一枚软刺。这句话是,我知道没有人肯把感情,倾注在一口常年不见光的枯井里。
如今,我的内里依然匮乏,生活依旧困顿杂乱且停滞不前。我深知往后的路荆棘遍布,林深处一眼看不到头。虽然,我依然在同生活为难自己,但最后还是选择看尽人间冷暖,历经人情世故。于是我告诉自己,黑暗是为了提醒有光的存在。我相信,一定会有人带我平抚所有失控的时刻,我会有真正的快乐,不是因为喝多。很多人来到世上,免不了摸滚打爬,免不了伤痕累累。但如果能尝尽酸甜苦辣,看尽人间百态,那也不枉世上走一遭。
你看,這万家灯火,每一盏都像射进枯井里的一束光,明亮灿烂且充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