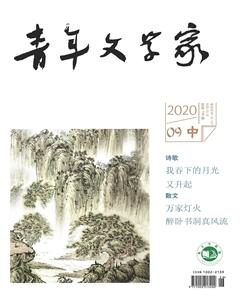萧红小说中的母性书写意蕴
摘 要:萧红通过母性形象在传统性别权力话语下的自我表现和内在生命经验展开母性书写,以此窥探母性个体的常规化状态和母性群体的普遍性遭遇,深入地探究母性身份自身的心理情结及生存选择。萧红生命经验的丰富性、创伤记忆的疼痛感和对人性思考的深度性使其小说同时存在对母性身份传统语境的接纳与反叛思想,呈现出悖论性书写趋向和独特性意蕴,具有超性别的书写视点和书写高度。
关键词:萧红;母性书写;权力话语;独特意蕴
作者简介:唐阳(1996.11-),女,汉族,四川遂宁人,西南交通大学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6-0-02
传统概念中,母性身份多是在纲常伦理下被建构出来的“他者”,并在家庭范畴中出现直接的指代性意味:女性=母性=家庭[1]2。女性的母性身份被剥离出主体性之外,仅成为家庭伦理化下具有普遍性意味的存在。
萧红小说中同时存在着对传统母性身份的延续性、发展性和颠覆性书写,将母性形象放置在传统话语范畴之下,以其在性别权力话语下的自我表现和内在生命经验为切入点展开自己的母性书写,直达母性麻木、畸形形象的文化寓意,完成整体社会观照。
一、丧失主体性的母性形象:延续性书写
在《生死场》中,萧红多处将人与动物同置,进行一种超人性和超性别视点的书写。萧红从女性性别经验出发上升到整个人类的生存层面,揭示出较为宽泛的生存寓意:
“房后草堆上,狗在那里生产。大狗四肢在颤动,全身抖擞着。”[2]52
“赤身的女人,她一点不能爬动,她不能为生死再挣扎最后的一刻。天渐亮了。恐怖仿佛是僵尸,直伸在家里。”[3]53
母性身份的确立是潜在母性(女儿身份)发展成具体母性(母亲身份)的过程,婚姻和生育各自起着名义身份认证和实际身份认证的作用。萧红将人与动物的生产联结起来,疼痛与潜在死亡使得人的生育丧失了愉悦的情感体验和为母的认知,仅隐约彰显出动物的繁衍本能与传宗接代的伦理要求。为人为母自觉性的丧失让生育这一母性身份的实际认证被动物本能化,并以男女都处在对“生死轮回”的无知状态来道出人生存的极致悲哀和苦痛,流露着“对穷人和妇女等弱势群体的灵魂的皈依”[4]106。在细处,萧红的笔墨更多放在为母的女性个体身上,通过母性的缺失来影射这种宏大书写。
“一个孩子三岁了,我把她摔死……把她丢到草堆上,血尽是向草堆上流呀……孩子死,不算一回事……可是我一看见麦田在我眼前时,我一点都不后悔,我一滴眼泪都没淌下。”[5]8-9
王婆母性意识的缺乏是建立在生存危机之上的,只有等到粮食丰裕、生存境地良好的时候,王婆才会想起死去的女儿。但物质因素的匮乏不能掩盖王婆母性自觉意识的缺失,王婆送老马走进屠场的不忍和悲痛与这段自白形成对比。王婆对动物的关怀在一定意义上超出了对亲人的怜爱,王婆不是在“生死轮回”中麻痹了人性,她只是缺乏母性身份的自觉。
萧红对这类母性形象进行塑造时有承续性也有超越性。承续性体现在对传统夫权话语建构的挖掘;超越性表露在摆脱外部权力建构的批判描写而着眼于女性自身的接纳过程,并以一种关注整个生存境地的眼光来书写。在《刑罚的日子》中,萧红描写五姑姑姐姐的丈夫对妻子的残暴行为,五姑姑姐姐“仿佛是在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男人”[6]53-54。主体性缺失的母性形象不是体会不到权力施加的痕迹,只是将其视为理所当然。
庙上娘娘因传说故事受到女性的生育崇拜,但除去世人求子之愿后,娘娘像世人一样,逃不出传统“男尊女卑”的藩篱。“娘娘还得怕老爷打呢”[7]57成为女性对自己在夫权话语下处境的自慰,对娘娘的戏谑心态表露出对自身“他者”身份的接纳与自觉。娘娘的遭遇不单是作为孤立的母性形象存在,而且预示了主体性丧失的母性实体无法摆脱的传统命运。
二、具有反面特征的母性形象:发展性与颠覆性书写
与主体性缺失的母性形象书写不同,萧红对具有反面特征的母性形象的书写颠覆了夫权话语规训下的“慈母”形象,将笔触抵达畸形内心和荒诞人性。这一母性书写在某种程度上与张爱玲的“恶母”书写有着相似性,但萧红的书写更囿于传统家庭权力意识之下,缺乏一定的都市病态心理观照。
“那家的团圆媳妇不受气……虽然說我打的狠了一点……不打得狠一点,她是不能够中用的……全身都打青了,也还出了点血。可是立刻就打了鸡蛋清给她擦上了。”[8]121-122
萧红在此将施暴者形象从男性发展为女性同类。婆婆对小团圆媳妇的施暴在自身看来是家庭权力的合理行使,是“管教”行为,但仅从家庭权力的角度去阐释这种施暴现象并未触及母性的心理情结。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对母亲的受虐——施虐狂心理进行分析,认为“因为早年的家庭生活带来了精神上的深刻创伤,她们抚养孩子时,以情结和受挫的形式作为交流的方式,并且这一不幸的锁链将永远延续下去。”[9]204婆婆的施暴行为或多或少是在她作为“女儿”身份的原生家庭中生成的,婆婆对施暴者身份的无意识心理在一定意义上是对自身以往的被施暴身份的接纳,是对传统话语的顺从。
小团圆媳妇的死不单是暴力导致的,闲言碎语、“跳大神”和各种“偏方”带来的精神恐惧远大于肉体伤害,而给予这些精神抨击的人是“好心”的街坊邻居,譬如周三奶奶、杨老太太。此类形象具有一些共性:一是都具有母性身份,母性身份的拥有是一系列行为的前提;二是都表现出无意识的压迫感,小团圆媳妇最初的被施暴就是在这些人的闲言碎语中展开的,周三奶奶们的言语与行为实质上与婆婆的打骂无异。萧红对周遭母性形象的书写透露出母性群体心理异化的普泛性。
文本中有个极具讽刺意味的人物安排,即行骗的云游真人。无论他数落婆婆的罪行是出于打抱不平还是金钱利益,但他的确是唯一一个正面苛责过婆婆施暴行为的人。传统而言,男性才是施暴者形象的传统渊源,云游真人反施暴形象的塑造更反衬出母性实体内部的扭曲心态和不自知的荒诞感。
萧红反面母性形象的书写是其整个女性书写中最具有深度性和讽刺性的地方。萧红没有从外部的男性权力来展开这段描写,而是从女性家庭权力的内部去挖掘潜藏在母性身份下的荒诞感。一方面,母性的受虐——施虐狂心理书写是母性形象对夫权/父权话语的自我接纳,是对传统话语的发展;另一方面,母性形象的心理扭曲所造成的悲剧是萧红对权力话语建构出来的“慈母”形象的颠覆。
三、极具母爱的母性形象:追求性书写
萧红小说中对极具母爱的母性形象塑造相对较少,但这一类母性形象的分析对于解读萧红的母性书写极为重要。
《生死场》中,母性意识多是麻木不自知的,金枝是少数具有母性关怀意识和本能母爱的形象。但小金枝的遭遇与“女儿”身份的原罪性相关,金枝的母爱表达受制于传统话语,带有明显妥协色彩。
发展到《呼兰河传》中,萧红有意识地摆脱了母爱的建构性书写,仅以纯粹的为母身份来书写母性意识。卖豆芽菜的王寡妇因独子淹死而发疯,生存意义随着独子的逝去而消失。王大姑娘坐在门前给孩子“绣着花兜肚子”,丈夫冯歪嘴子“在磨房打着梆子看管着小驴拉着磨”[10]201。冯歪嘴子不同于传统父权社会下的父亲形象,传统建构性并未显现在王大姑娘身上,王大姑娘的母爱表达是本能、平淡和真实的,是萧红想要追求的。
萧红在对前两类母性形象进行塑造时,个人的母性意识影响着母性书写,书写的矛盾性凸显在文本之中;但是对母爱进行刻画时,萧红透露出一种为“女儿”的意识,力图打破母爱的传统建构性,表达出对母爱本能性的追求。
四、独特性书写
萧红的个人生命经验包含了从潜在母性身份走向具体母性身份的过程,但萧红的母性身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获得,她有生产的经验而缺乏为母的经验,为母权力的自我放弃内化为心理的疼痛点,通过《弃儿》中的芹能够窥探出萧红放弃为母权力的挣扎和无奈之感。可以肯定的是,萧红内心的隐痛和生产的疼痛经验使她的母性书写成为她文本写作中的重要一环,正是这种独特的感受使她更关注母性的内在经验,并将其转为母性书写的切入点。萧红的母性书写在三四十年代具有鲜明的独特性,体现在她的疼痛感书写、权力话语建构的内部性书写和矛盾性书写中。
生产的疼痛是母性独有的经验,这一经验影响到母亲对孩子的态度选择,《第二性》中将母性生育过程与母亲心理过程紧密相连。生育标志着分离,胎儿试图脱离母体的蠕动给母亲带来极度疼痛,随之胎儿完全听任于母亲的境地被打破,在一部分母亲眼中完成生育就意味着母亲不能完全控制孩子的思想。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失落往往会激发母性潜在的偏见和恶意,并在養育孩子的过程中表现出来,就像小团圆媳妇婆婆对小团圆媳妇的“管教”。这种家庭权力又常常涉及到社会体制下整个权力话语的运行。
在这种挖掘中,萧红看到了母性身份中可能具有的狭隘性,并真实地把这种人性表现出来,这是她对以“慈母”形象为依托的权力建构的抵触,也是对夫权/父权所造成的母性悲剧性的反叛。尽管萧红看到这种悲剧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母性形象自身的选择结果,但她并没有排除权力话语机制对母性群体的摧残性。对母性群体自我接受建构化和心理异化的内在点的探讨,说明了其母性书写中仍然保持对传统母性身份社会建构的接纳观点。这种矛盾性是复杂的,它不光存在于萧红的母性书写中,也恰恰存在于传统社会下的大多数母亲身份中。萧红母性书写中矛盾的地方正好是能够反映时代和社会真实的地方。
五、结语
萧红的整体书写极度关注个体的生存困境和人的整体异化,对人性做出深刻的探究。萧红的母性书写没有脱离她一贯的自觉,反而母性这一具有普遍意义而又意义非凡的书写主题能够使萧红更加关注女性内部经验和人性的荒诞感。萧红的疼痛感书写、话语建构的内部性书写和矛盾性书写是她有别于同时代和后代母性写作的关键点。萧红的矛盾性书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母性书写中主题思想不成熟的表征,但是更应该看到,这种矛盾性来源于传统社会下女性的真实存在状况和心理偏见,萧红的母性书写因此也具有了一种超性别的社会意义。
参考文献:
[1]卢升淑.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与母性[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0.
[2][3][5][6]萧红.生死场[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
[4]林贤治.山之民[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年.
[7][8][10]萧红.呼兰河传[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9][法]西蒙·波伏娃.第二性,李强选译[M].北京:西苑出版社,2004年.
——一本能够让你对人生有另一种认知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