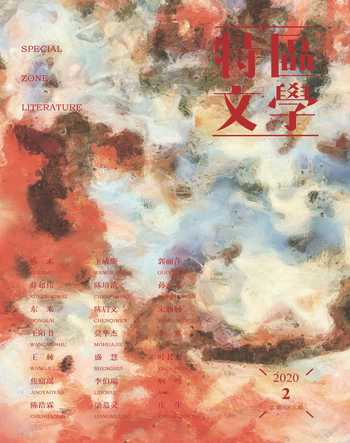洼地上的文学观望
陈启文 莫华杰
莫华杰:陈老师,您好!作为您的入室弟子,文学早已是我们之间的日常话题,但如此正式地谈文学,并且是围绕东莞这一独特的地域文学展开,还是头一次。我还真是有些诚惶诚恐,生怕一不小心谈出什么偏见和谬论来。
陈启文:文学就是自由谈,文学创作就是从心所欲,一切从心灵出发又以生命为依归。心灵世界往往比现实世界更丰富、更复杂,也有更多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这正是文学的可为空间。我倒很想听听你的偏见或谬论,说不定能打破我的习惯思维,在碰撞中又发现什么新的可能性。
莫华杰:那我就大胆地谈谈个人对东莞文学的一些印象。我2004年来东莞打工,如今已有十六年了。东莞是“打工文学”的重镇,我读得最多的就是“打工文学”作品,我们厂区门口就摆满了《佛山文艺》《江门文艺》之类的打工文学杂志,还有东莞本土的《东莞文艺》和《南飞燕》,这就是离我最近的文学,写的也是离我最近的生活。读得多了,我也跃跃欲试,我也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写出来啊。我的“文学创作”就这样懵懵懂懂地起步了,但我觉得自己真正懂得什么是文学,已是2008年岁末。在东莞市的一次文学交流会上,东莞文学艺术院的曾明了老师把您的长篇小说《河床》极力推荐给我们在场的所有人。她是一位很有个性的优秀小说家,在我的印象中她的眼界是很高的。我读过她的中篇小说《黑嘎》,那匹“像一团燃烧着黑色火焰”的骏马,带着我在大漠戈壁上进行了一次精神上的游历。而她竟如此推崇您的《河床》,说这是中国当代小说史上写得最棒的小说之一。我立马就买了一本,那还是我第一次拜读您的作品,我震撼了。那是源自生命的震撼,那种力量源自属于生命的最深刻的体验。我理解了,贺绍俊先生为什么要把《河床》推为“中国第一部生命小说”,“从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无不引导我们重视生命、思索生命,通过生命现象去追问永恒。其实,新时期文学以来在深化人性方面的重要表现之一便是生命意识的觉悟。如莫言在《红高粱》中所表现的对生命的原始状态的崇拜,余华在《活着》中对生命的生存方式的追问,史铁生在《我与天坛》中对生命所做的哲理式的沉思,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尽管如此,这些作品更多的还是依重于社会人生的内容,惟有《河床》让生命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最直接地感受到生命的气息。”
陈启文:曾明了老师不仅是东莞的一位优秀小说家,也是东莞小说創作的一位开拓者,《黑嘎》堪称是她的代表作。她在新疆度过长达八年的“女知青”生活,这让她在大漠孤烟中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特而深刻的生命体验。同样,《河床》也源自我最深刻的一段生命体验,在故乡那片孕育了我的河床上,我体验到了成长、死亡、屈辱、疼痛,还有那种人类在时空中的偶然、短暂、渺小和孤独感。这也是我迄今仍无法超越自己的一部小说,一个写作者要超越自己其实很难。
莫华杰:您和曾老师都是从外省引进的东莞作家,而在东莞本土成长起来的作家,大多是在东莞打工的外来工,有的甚至是流水线工人,如王十月、郑小琼,都是从东莞走出来的,贴上了“打工文学”或“打工作家”的标签。那时《东莞文学》和《南飞燕》每年都会举行“打工征文”或“打工文学擂台大赛”,我还得过一等奖,高兴了许久。现在回过头来看,我都感到脸红,实在太浅薄了,我都不好意思拿给您看。
陈启文:对于“打工文学”我从来没有看轻过,但最初的“打工文学”更多是从生活经验出发,甚至是在经验的表面上滑行。有一个事实是必须正视的,打工作家最初都是一些低学历的写作者和流水线工人,普遍存在文化积累的单薄和阅读经验的缺乏的问题,他们首先要保障自己的基本生存,也难以集中精力阅读和写作。然而,随着王十月、郑小琼、塞壬等“打工作家”的出现,从生活经验逐渐转向了生命体验,他们都是从东莞走出来的。王十月的散文代表作之一的《总有微光照亮》,还是我在《文学界》当特约编辑时责编的,这也是我作为责编一直备感荣幸的。很多人都只关注他的小说,他的散文有可能被低估了又是绝对不可低估的,如《寻亲记》《小民安家》《关卡》《声音》等,既源于扎扎实实的生活经验,又超越了生活经验,我在一篇文章中把他称之为中国的高尔基。他以打工的方式上完了“我的大学”,而他现在的阅读远远超过了多少科班出身的作家。从生活经验、生命体验到转化为文学创作的精神资源,我一直觉得他有着超凡的灵性与悟性。
莫华杰:一个人一旦被贴上了“打工作家”标签,仿佛就成了终身胎记,仿佛天生低人一等。如今评论界也越来越多不认同“打工文学”“打工作家”的叫法,觉得这带有歧视意味,现在又发明了一个新名词:“劳动者文学”。您觉得有必要吗?
陈启文:所谓文学标签,都带有时代烙印,如此前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等,其实都无法对文学进行准确定义,真正的文学是没有边界的,对那些外在的标签没有必要在乎。以郑小琼为例,她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打工诗人”,有人称她是一个对“时间”非常有感觉的诗人,但她的“时间”不是经验上的时间,而是具有内在生命的。从《流水线》到《完整的黑暗》,这是她在不同时段抒写的两首代表作,也代表了她从生活、生命到精神的转化过程。她在《流水线》呈现了一个世界工厂的现实世界:“在流动的人与流动的产品间穿行着/她们是鱼,不分昼夜地拉动着/订单,利润,GDP,青春,眺望,美梦/拉动着工业时代的繁荣……”而在《完整的黑暗》中她已经超越了现实:“三条鱼驮着黎明、诗歌、屈原奔跑/对称的雪沿着长安的酒融进了李白的骨头/列队前进的唐三彩、飞天、兵马俑/化着尘土的人手持红色的经幡演讲/达摩圆寂,天生四象,六合断臂/死亡是另一种醒来/时间的鸟只抖落了皇帝的羽毛……”如果撕下郑小琼这个标签,你感觉这还是一个打工诗人的手笔吗?著名评论家张清华对此发出了震叹:“这是何等境界和气势,整首诗一气呵成,气势贯通,绝无叠加拼凑的痕迹。称得上是对一个时代的整体俯瞰!”
莫华杰:除了王十月、郑小琼,在东莞还有一些颇有代表性的作家,譬如说塞壬,多年来一直在南方打工,其散文也大多取材于打工生活,这让她也被贴上了“打工作家” 的标签,但她对这一标签是不认可的。还有丁燕,她的报告文学《工厂男孩》和《工厂女孩》也被视为“打工文学”,这是否意味着,只要是写打工题材的文学作品,都可以纳入“打工文学”的范畴?
陈启文:不能说是范畴,在严谨的分类学中,范畴指种类的本质,而所谓“打工文学”原本就不具备这种严谨的界定,只能说是个大概的范围吧。塞壬是一位个性鲜明的散文家,如她的散文集《下落不明的生活》《匿名者》《奔跑者》等,其文学辨识度不在外在的标签,而在于其独特的精神姿态和有锋芒甚或有些偏激的的文本,她也不只是写打工题材。丁燕则是一位擅长各种文体的写作者,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小说乃至评论无不涉猎,把她的《工厂男孩》和《工厂女孩》纳入“打工文学”也未尝不可,但把她定义为一位“打工作家”则过于狭隘了。
莫华杰:您到东莞来后也写了不少打工题材的作品,如系列散文“谁正与你擦肩而过”,中短篇小说《虚掩的门》《南方经验》《回南天》等,也被各种“打工文学”作品集纳入其中,很多评论家也把它们作为“打工文学”作品予以评论,有评论家称《南方经验》是近年来最好的一部“打工文学”作品,但也有评论家对此不以为然。我还记得,在东莞的一次“打工文学”作品研讨会上,郭小东先生直爽说:“若把陈启文看成是一个打工作家,把他的作品看作打工文学,简直是一个笑话!”
陈启文:我对给我贴上“打工文学”或“打工作家”的标签还真是挺高兴的,从更宽广的意义上讲,我没有在工厂打过工,但也在一些单位打过工,无论你在哪里工作,都是打工啊。而我来东莞十多年了,接触了形形色色的打工者,自然也会涉及这一类的题材。至于别人怎么看怎么评论,都是他者的视角和言说,一个写作者无论写什么,一切都只能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切入,这一切都必须转化为自己的精神资源。其实,一个真正的作家从来都不会为什么标签所绑架。
莫华杰:如此看来,将东莞视为一个“打工文学”重镇也是狭隘的。那么,若把东莞作为一个“地域文学”的概念进行整体观察,怎样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呢?
陈启文:首先我不否认,无论是从生活题材看,还是作者阵容看,东莞确实是一个“打工文学”重镇。但若要对东莞文学进行整体观察,我觉得按体裁分类则比按题材分类要较好把握。先梳理一下小说吧,东莞历经多年来的蕴积,已逐渐形成了一个由50后、60后、70后、80后组成的创作梯队。50后主要有曾明了、胡海洋、杨双奇、李泽光等小说家,他们依然笔耕不辍,充满了创作活力;60后主要有陈玺、汪晟、黄运生、黄应秋、邹萍、詹文格、吴向东、严泽等。陈玺近年来创作了《暮阳解套》《一抹沧桑》《塬上童年》等多部长篇小说,还在《十月》《中国作家》《北京文学》《作家》等刊发表了多篇小说,而他生长的渭北塬上既是他的生命底色,也是他的文学底色。吴向东则是我发现的一匹“黑马”,其文学创作起步较晚但起点很高,他的小说更多是从不确定性和可能性出发,这种探索让我充满了期待;70后、80后小说家主要有陶青林、寒郁、穆肃、皮佳佳、谢松良、陈月秋、杨信莲等,你也是80后小说家中的佼佼者。除此之外,还有陆续调离东莞的王十月、陈崇正、阿微木依萝、吴纯、陈柳金等,他们均为东莞小说创作做出了不能磨灭的贡献,这是不能遗忘的。
莫华杰:东莞散文创作的队伍也很整齐,如您,塞壬、丁燕,还有老一辈散文家詹谷丰老师,都是活跃在一线的散文家。尤其是詹谷丰老师,他原本是一位小说家,在天命之年他放弃了小说创作,专攻民国系列散文,这对于他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转型。近年来陆续推出了《义宁的源头》《书生的骨头》《骨头的姿势》等力作,有评论称他的散文以历史文化的双重叙事重塑了知识分子的灵魂。此外,还有詹文格、洪湖浪、周齐林、邝美艳、谢莲秀、侯山河等中青年散文家,也在全国各大刊名刊发表了不少佳作。
陈启文:东莞各文学门类的作者阵容都比较整齐,尤其是诗歌方阵可谓是众星朗朗。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东莞籍诗人筱敏就已在全国诗坛崭露头角,她也是我十分尊重的一位有良知而不同流俗的散文家。而后,東莞又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诗人,除了已调离东莞的郑小琼,目前活跃在东莞诗坛乃至全国诗坛的还有方舟、丁燕、柳冬妩、百定安、黎启天、林汉筠、蓝紫、池沐树、易翔、老兵(孙海涛)、彭争武、侯平章、莫寒等,其中有好几位东莞诗人参加了《诗刊》“青春诗会”。
莫华杰:是啊,东莞在报告文学、儿童文学、文学评论、网络文学等各方面都有代表性作家,如以您和丁燕为代表的报告文学作家,以曾小春为代表的儿童文学作家,以柳冬妩、胡磊为代表的文学评论家,还有以穆肃、王虹虹为代表的影视作家,都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
陈启文:无论是对一个人的文学创作进行评价,还是对一个地域的文学进行评价,从来没有绝对标准,但也有相对标准。从获奖看,王十月的中篇小说《国家订单》为东莞摘得了首个全国鲁迅文学奖,曾小春为东莞摘得了首个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杨双奇为东莞摘得了首个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我的长篇报告文学《共和国粮食报告》获国家图书奖,柳冬妩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等。另外,东莞还有三位作家入选全国鲁迅文学奖提名,先后有十多部作品获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文学类),二十多部作品获广东省有为文学奖(其中三部作品获得金奖)。东莞作家及作品还获得不少在全国有影响的文学奖和图书奖,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从创作队伍看,目前东莞有中国作协会员51名((未包括樟木头作家村的外地作家)、广东省作协会员有188人,市作协及各镇街分会会员近千名。
莫华杰:我听詹谷丰老师说,东莞作协成立之初,没有一名中国作协会员,那时在省级文学期刊发表一篇作品都是了不得的大事。如今东莞作家每年都要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十月》《花城》《北京文学》等全国核心期刊发表数以百计的作品,并在《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广为选载,还频频摘得《人民文学》年度奖、《小说选刊》双年奖、《北京文学》双年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这在三十年前简直是做梦啊。
陈启文:说到底,发表、出版、入会、获奖、评职称,都只是文学评价的相对标准。从相对标准看,东莞在文学上确实实现了自身的超越,甚至有一些广州和深圳的作家对东莞文学也不乏真诚的礼赞。但我们必须正视自己的局限,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一次文学论坛上,我就直言过,东莞正好处于广州和深圳的夹缝之中,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超越这两座大都市,在两强之间,东莞是一片文学洼地,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宿命。但我们可以不断超越自己,这种超越注定只是内在的超越。而文学创作就是一个出乎其外而入乎其内的过程,如果时空中真的存在永恒的生命意义,那么,永恒的文学抑或经典意义的文学必然是沿着对个体生命的体贴、沿着自我灵魂图腾的叙写。对于文学本身,一切的外在标签或标准都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