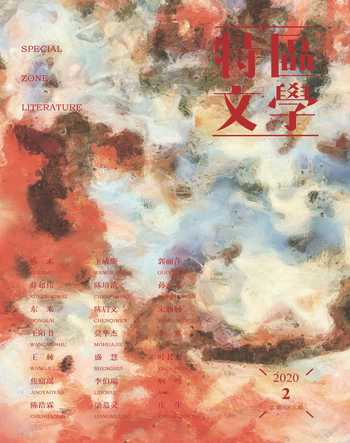老虎
和尚坐在蒲团上,拨动手中的念珠,默念佛经。
墙上挂着两个西洋钟,它们滴答响,可能是一个快了两分钟,可能是一个慢了两分钟,响声的频率不协调。和尚年纪二十左右,五官标致,头顶上的戒疤烫得不算久,一身青色袈裟散发出淡淡的熏香。
半开的木窗外,漆黑的夜消除了一切形状,演化成一种无脊椎生物。他打坐了一天,只进稀粥,像佛祖在菩提树下一般等待顿悟的一刻,但始终没有等到,不免觉得焦躁。眼睛布满血丝,嘴唇上干裂的死皮快要脱落,后背的汗水透过了袈裟,不过没有多久就蒸发了。
毫无疑问,他在努力隔绝一切干扰。在这深山中的小寺里,周围是丛簇的树林,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几乎被植物湮没,平日里极少访客。原本有四个和尚,现在还剩三个,其他两个是他师兄和住持收养的小沙弥。他的法号是惠信,师兄是惠远,小师弟是惠智。而法号觉敏的住持上周在澡间失踪了,只剩下几件衣服和一串挂珠,门是打开的,师兄说是被隐藏在水缸边的老虎叼走了。
可能是心理作用,他还是嫌不够清静。
门紧闭着,以免老虎拖沓着步伐穿门而入。窗框上的糊纸已经破破烂烂,天花板是有些年头的松木,一有人踩在上面,就发出嘎吱—嘎吱的噪音。人类的眼睛察觉不到危险,就像人类的耳朵察觉不到20Hz以下的声音,但是这里确实弥漫着一股死亡的气味。通过柜子上正在结网的蜘蛛的视角—它的八只眼睛看见门口处生锈的捕鼠器夹着一只褐家鼠,肠子都被挤了出来,这个啮齿动物死之前咬住一小块胡萝卜,那是诱饵,死之后还是不松口。桌子上放着一张贴纸,抹着一层棕黄色的粘稠糖浆,上面沾着许多不再挣扎的苍蝇,糖浆甚至把一些半透明的翅膀扯断。另外,和尚旁边放着一盘蚊香,正渐渐变成灰烬,周围散落着已经中毒的蚊子。
这里是一座停尸房,堆积着不同生物的尸体,而凶手—那个和尚似乎没有发觉任何异常。他为了屏蔽噪音消灭这些入侵者,却无法除去自己内心的杂念。脑海中闪现过女人的裸体,他胸中憋闷,只得在心中大声念起《楞严经》。
不久,他沉沉睡去。
他是一年前出家的,那是在五月,他先去了理发店。穿着白色T恤衫配黑色牛仔裤,鞋子是盗版耐克,大厅里两边墙壁上对称地安置了一排镜子,他看见镜中的自己在看着镜子,以此类推,真实在反射中不断凹陷,彼此之间互相拆穿。店里的收音机在播放Bee Gees的歌曲《Holiday》:“It’s something I thinks worthwhile. If the puppet makes you smile ……”他听着歌词,不由自主地跟着哼起来。
坐在沙发椅上,他看见地上堆积着其他人的头发,这些头发会收集起来做成戴在别人头上的假发。矮个理发师调低椅子的高度,再把白布系在他脖子上,往他头上喷芳香的发胶。他吐掉嘴巴里的口香糖,指了一下自己染成金黄色的头发:“全部剃掉。”
“全部剃掉?留这么长了,不可惜吗?”
“是的,我要去做和尚了。”
“那让和尚给你剃不就可以吗。”
“他们是用折叠剃刀,抹上植物油直接在头皮上刮,我讨厌那样,很容易割伤。”
“可不,他们没有电动推剪。”
“他们也不会剪鼻毛—不过他们会烫香疤,这个要是也不会就好了。”
“你怕疼?”
“当然怕,我的皮肤特别敏感。”
“教你一个办法,瞧见我的耳钉没?我用冰块敷在耳垂上十几分钟,那样打洞的时候就没什么感觉,你也可以在脑袋上敷冰袋。”
“不错的主意。”
接下来电动推剪一点点削去头发,他不能挪动腦袋,忍受着噪音,觉得那是割草机。这个空间仿佛刚刚洗过澡,洗发水、按摩油、染色素的气味混合在一起,汇聚成看不见的泡泡。
“话说回来,你这么潮的小伙,为什么要去做和尚?”理发师问。
“既然有这份职业,总得有人去做不是?”他回答。
次日醒来,旁边的蚊香已经燃尽,他察觉到异样可又说不出理由。等站了起来才意识到胯间一片潮湿,自己梦遗了。他屏住呼吸,压抑从体内漫出的羞耻感,从开水壶里倒出一杯热水,打开一个小瓶,数了几粒头孢拉定胶囊吞了下去。然后去澡间清理秽物,从水缸里舀出一瓢瓢水浇在自己瘦弱的裸体上,那是井水,冰凉的触感让他遗忘了不快。
在吃早饭的时候,他喝着稀饭,咬着韧劲十足的番薯干,听师兄说一位信士来请和尚去念佛,要念三天,管吃住,事后还有一封红包。大约十岁的小沙弥惠智在桌底下用米粒喂蚂蚁。惠远一只耳朵聋了,所以听力不是很好:“师父不在了,我得留在寺里,这次由你去吧。记着,来回的车费也要找他报销。以前就有人跟我赖账,说什么费用统统算在红包里了,为这个我跟他理论了一下午,哪有这样的规矩,一码归一码。”
“是祈福吗?”他佛经背得不牢,得提前准备。
“本来是的,他孙子周岁要祈福。但他孙子周岁前发高烧夭折了—阿弥托佛,所以是做超度。”师兄吹了吹稀粥上的热气,小口地喝了起来。
“那我得带《地藏菩萨本愿经》去。”他回答,停顿一下继续说:“师父被老虎叼着这么多天,林管站的人有没有找到老虎?他们不是带枪进山搜了好几天了吗?”
“没有,那大虫狡猾得很。”惠远低下头,瞪着桌底下的小沙弥,“惠智,最近不可出去乱逛,知道了吗?”
“知道了。”惠智显得畏畏缩缩。
“惠信,等下我把地址和联系人姓名抄给你,回来的时候记得买腐竹和薯粉干。”惠远夹住一块茄子。
“庙里的药王菩萨像被虫蛀了,是不是该请木匠做过一个。”他说。
“我已经找人定做了,六分米高,四分米宽,柏木质地。”惠远把茄子送进嘴里。
“你在找住持的钱箱吗?”他说。
“不错,那笔钱应该由我看管,毕竟我负责寺里的开销,不过一直没有找到。”惠远不想继续谈这个话题。
现在住持的遗体都还没有找到,师兄就忙着接住持衣钵的准备,让他很是厌恶。那天下大雨,没有找到动物脚印,但是在篱笆那里找到了一撮花色的毛发。一个活人凭空消失,警察实地调查找他们录口供,结果还是毫无进展。这附近的老虎在三十年前就几乎被有持枪证的猎户打光了,那应该是一种已经灭绝的生物,跟恐龙一样只能在博物馆看到骨架化石。现在的山里别说是老虎,连土狼或野猪都很少见。可是人们对山林总是感到陌生,这种隔阂容易滋生各种遐想。
吃过早饭,在佛祖木像前上过香,他收拾好旅行背包准备下山。跨过门槛的时候,藏在门后的惠智拉一下他的衣角,想说什么又住口了。以前他下山惠智会托他买点零食,软糖或者曲奇饼干都行,他以为惠智想说的是这个,摸一下惠智还未烫戒疤的头表示答应。想到没有带钱包,他又回到庙内,中途手臂似乎碰到了蜘蛛丝。
住持曾告诉过他,以前这里并非佛寺,而是一座基督教堂。当初洋人神父花了一百块银元,从一个道士手里买下这座建筑,所以侧壁上还留有三清四御的壁画。神父本来请了画匠想铲掉墙皮,重新画上创世纪为主题的壁画,但是还没等到开工,他便死于重感冒引起的肺炎。于是这座建筑又转手到当时还很年轻的住持手里。住持拆掉了屋顶的十字架,安置好佛像和经幡。其它的他没有改变,没有那么多钱。因此,这里残留着各种宗教的痕迹。
下山的路坑坑洼洼,有几段甚至被滑坡的泥石流掩埋,上面长着野麦子,穿过时会惊起一群麻雀。惠信路过一座废弃的泥瓦房,屋顶已经垮掉了一半,顶部寄生着蒲公英与苍耳,如果下雨,即便推开门进去也无法躲避。他坐在门口倒扣的陶瓮上休息,脚边是一丛野草。上一次经过的时候是冬天,屋顶的瓦片上堆积着落叶与污雪,偶尔有乌鸦在上面落脚,他也是坐在倒扣的陶瓮上,脚边是一堆生过篝火留下的木炭。一个地方,季节不同让他感觉那是两个地方。
第一次上山时,他跪在小庙青砖铺成的地面上,参差不齐的砖块硌得他膝盖很疼。住持坐在他前面的蒲团上,惠远在走廊上削萝卜皮,而惠智则站在门槛外玩捉到的螳螂。住持问:“年轻人,为什么出家?”
“有的人天生适合做屠夫,有的人天生适合做和尚。”
“这么多寺庙,为什么要来我这出家?”
“现在虽然不要度牒,可其它寺还是看文凭,香火鼎盛的大寺更是要佛学院毕业的高材生。”
“为了做比丘,早早就剃好头发,看来你有志于此。以前读过佛经吗?”
“没有,只知道佛祖是释迦摩尼。”
“能遵守五戒吗?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妄语,五不饮酒。”
“要是说能,我就犯了妄语戒。”
“也罢,寺里也缺个砍柴挑水的人,让我给你想个法号吧。”
就是这样,他变成了和尚。
大约过了五分钟他离开泥瓦房继续赶路,随着越来越接近山脚,温度渐渐升高。周围是寂静的群山,虽然经常去砍柴,他还是对这一切感到陌生。人与植物无法沟通,他在林中的自言自语无人倾听。他总是在埋怨,埋怨方丈太吝啬—连电话都不肯装,埋怨惠远把寺里的东西寄给出家前娶的老婆,埋怨自己要干的活太多……絮絮叨叨的牢骚在山林中飘荡,产生的回音反过来让他更确信自己的看法。
也想过还俗,但几番犹豫还是留了下来,倒不是说因为多么虔诚,只是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
等到了山下的候车点,他站在生锈的金属站牌旁边等车。这里的乘客很少,所以班车很不准时,等到下午他才看到那个长方形机器。期间,他吃了根洗过的生红薯,连皮一起津津有味地咽下去。把一个空矿泉水瓶从站牌那踢到电线杆那,再从电线杆那踢到站牌那。最后去旁边的草丛里小便时,还捡到了一枚硬币,他想,等待是极其无聊的事情。
随着一阵喷气声车门打开,可以闻见一股座椅皮革和汽油杂交出的臭味,让人想要呕吐。司机抽着卷烟,回过头一言不发地指了一下投币箱,车里没有其他乘客。在上车前他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条,那是惠远抄给自己的地址,上面没有写电话号码。然后踩上台阶,在司机警惕的注视下,将之前数好的硬币一枚枚投入透明的箱子里,当啷—当啷—当啷,每一次反弹都会让司机的眼睛发光,仿佛是被重复按下开关的电灯。
“到沁水镇去。”他走到最后面坐下。
“好—好。”司机把还在燃烧的烟头扔出窗外。
“该把烟头摁掉,不然烧起来要坐牢的。”他把旅行包放在旁边。
“事多。”司机走下车,踩灭烟头再回来,发动引擎。
“这车应该快退休了吧。”他感受着剧烈的晃动。
“还能将就开下去,发动机坏了换发动机,轮胎坏了换轮胎,方向盘坏了换方向盘。原则上所有部分都可以替换,所以原则上可以一直开下去。”司机抬起头看了一下后视镜,但是因为惠信坐的位置太靠后,根本看不到他。
窗外的风景开始加速流动,他看见被碾死在路上的野兔,然后遗忘;他看见扛着木头像扛着十字架的工人,然后遗忘;他看见路边生锈的废弃坦克,然后遗忘……在车上,感觉一切瞬息即逝。他不再跟司机没话找话,闭上眼睛休息,毕竟还要很久才能抵达终点。
几天后,同一辆班车上,同一个司机和同一个和尚在聊天,只是车的方向和上次相反。在给夭折的孩子做超度的几天里,惠信吃了不少三净肉,体重增加了几斤,这或许是他唯一的变化。他没有见到尸体,只见到骨灰坛和黑白遗照,是个圆脸的男孩。因为没有思考能力,男孩的死亡并不痛苦,他的一切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短暂的一生给家庭制造的创伤会持续到下一个孩子降生为止。男孩的祖父很是大方,除了红包和车费外,还把做法事用剩的供品全给了惠信。但是男孩的父亲不信佛教,对他嗤之以鼻,还提防他顺走什么贵重东西。他咿咿呀呀念了几天经,一直呼吸香烛的烟雾,嗓子坏了,现在嘴巴含着西瓜霜片。
“你跑这条线多久了?一年前,我第一次來这就是坐了你的车。”他用沙哑的声音说。
“二十年,过段时间你就不会坐这辆车了。”司机往左转动方向盘。
“为什么?。”他嚼碎快溶解的含片,撕开一条口香糖送进嘴里。
“这个站点乘客太少,没有收益,公司决定从下周开始裁撤。毕竟是商业社会,凡事都得讲究利润。”司机往右转动方向盘。
“那以后我们要坐车怎么办?”透过窗户,他看见上次看见的野兔尸体,在路上没有被清理。
“得走路去清河站了,离你那里半小时车程,那个站点人多一点。”司机看见前面有人招手,准备停车。
“阿弥托佛。”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他便如此说。
他在山下的金属站牌那里下车,拎着好几包东西,有信士送的供品,有惠远吩咐买的腐竹和薯粉干……这样上山肯定很吃力,幸运的是他碰到了也要上山的伐木工,可以顺路搭坐他们的驴车。那几个戴草帽的工人哼着下流的小曲,转轴有故障的轮胎吱呀—吱呀地叫唤,像是伴奏。
车上空荡荡的,等下山的时候才会装满松树的尸体。他去过伐木场,那里有着一堆堆码好的木头,它们分好类了,用粉笔画着不同记号,有的能用来盖房子,有的能用来生产家具,有的只能用来当柴火。不断有树木倒下,得当心不要被压着,虽然概率很低,但还是有工人被自己锯断的树压死。地上累积着积雪般的木屑,电锯持续磨损耳朵的听觉,每次停下,都能感觉到它发热的链条像刚做完爱的女人在颤抖。伐木场会迁徙的,当把一个地方的木头砍光,留下一些长牛肝菌的树桩,留下一堆生活垃圾,留下一个临时厕所,工人们就会搬走。去另一个地方做相同的事情。
谁也不会注意到,自然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在缓慢地修复这些破坏,树桩上新抽出的枝条就是证据。惠信不喜欢那些粗鲁的工人,他们身上有一股异味,像是流淌在地上的乳白色橡胶。他旁边的家伙握着烧酒瓶,往嘴巴里灌了一口后问他要不要,他摇了摇头。坑坑洼洼的山路让驴车很是颠簸,不过还没有到让他无法忍受选择下车步行的程度,他说:“最近,你们在山上见过老虎吗?”
“老虎?”旁边的伐木工A有些诧异,老虎对这些人来说是遥远和陌生的东西,跟已经灭绝的猛犸象无异,都是没有见过的生物。
“是的,老虎。像是巨大的猫,身上有花褐色条纹,眼睛很大,腹部雪白。额头上的条纹不一定像“王”字,舌头上有很多倒刺。”他尽可能详细地描绘自己在电视节目上见过的老虎。
“没有,我出生以后就没见过。”伐木工B说。
“现在山里哪有像样的野兽,能找到獐子就很难了,大点的家伙早打完了,现在山里最大的动物就是你们几个和尚。”伐木工C跳下驴车,去路边解开皮带小解。
“我们寺的住持可能就是被老虎叼走的,你们有没有注意过动物的粪堆,里面可能有住持手上戴的珠串。”他继续说。
“我爹倒是见过老虎,以前还闹虎灾哩,政府鼓励猎户去杀老虎,一张虎皮奖五十块钱,杀最多的还发了‘打虎英雄’的奖状去县里接受领导表扬。我爹小时候看见的是老虎幼崽,跟一只猫似的,他爹—就是我爷爷用镰刀剥了皮送去县里,但是他们说那是猫皮不肯给钱。最后吵了一架,打个对折给了二十五块。以后就没有谁见过了吧,可能那是最后一只老虎。”伐木工A嚼着草根。
“人不可能凭空消失吧。”他打开装供品的塑料袋,抓出一把红枣干请其他人吃,自己则剥开一个龙眼干的外壳,里面居然是空的,他诧异地把壳扔掉。
驴车走得很慢,伐木工C很快追了上来,嘲笑他说:“可能跟尼姑跑啦。”
“阿弥托佛。”他不想回应。
这些伐木工都是单身汉,都是过了一天算一天的人,周而复始地在林中锯断木头送去木料厂,领到工钱也很快挥霍。他们是现代的游牧人,随着公司要求而迁徙,扎下帐篷。惠信听人说过,为了解决性需求,伐木工们会跟山羊交媾。这实在骇人听闻,他想问他们是不是真的,但又不敢说出口。
到了破败的泥瓦房那里惠信下车,看着伐木工们摇摇晃晃地消失在树林深处,他没有道别。那一刻他倒有点期待,期待林中真的有一只老虎。泥瓦房门前有几个空的水果罐头,应该是昨天或者前天留下的,他没有在意,也没有稍作停留。
陈旧的寺门上长着杂草,不用叩响铜把手,橡木大门一推就开,他跨过掉漆的门槛进入种着蔬菜的庭院。棚架的影子倒映在他身上,是一横一竖的条纹,过几天他栽的丝瓜和西红柿就可以摘了。他喊惠智,然后喊惠远,但无人回应。于是去厨房放下腐竹和薯粉干,然后拎着给惠智买的奶昔面包走到前殿。到处都是空荡荡的,凝视没有表情的木头佛像,发现一只瓢虫落在佛祖的眼睑里,他突然觉得连续两次看到碾死的兔子是恶兆。他跟随听到的水声走去后院,看见惠远正从井里打水。
“叫你为什么不应?”惠信有些不快。
“没有听见。”惠远压着水泵的杠杆,井水从圆形铁嘴流出,正在填满一个木桶。
“腐竹和薯粉干都买了,不过听人说那家店的味道不是很好,老板很不老实。”惠信坐在缝隙处长着青苔的井口边。
“好—好,晚上就吃腐竹煮粉,加點笋干。”惠远点了点头。
“惠智上哪里去了?粘知了去了吗?我给他带了甜食。”惠远捏着袋子里的面包,一路下来,面包已经变形。
“他—前天晚上出去小便,被老虎叼走了。”惠远说,“当时很黑,我只听见声音,等我拿着煤油灯出去,他已经不见了。”
“老虎?又连尸体都没找到?”
“没有找到。”
“而你又什么都没有看清?”
“不能完全怪我,天那样黑,我手里又没有枪……”
惠信沉默了一会儿,目光在解剖惠远,似乎割开虚伪的表面就能从中找到一头凶残的老虎。他用力捏着面包,把它变成碎屑,再把碎屑挤压成一个整体,半液态的奶昔流到手上形成一股白色的血液,然后滴落到深深的井底,听不到回音。他在犹豫自己应该恐惧还是愤怒,在犹豫中,两种情感都如退潮般迅速消解了,最终剩下的是空白的茫然。
“住持说过有人偷他钱箱里的钱,所以他把钱箱转移了地方,而你说过你在外面欠了赌债……我想问问,钱箱现在在哪里?会不会是老虎吃掉了?”惠信说。
“他是个吝啬鬼,谁知道藏哪里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住持不见以后惠智一直怪怪的,是不是他看见了什么不该看见的事情,而你又告诫他不要说不该说的事情?”
“你到底什么意思?”
“没什么,只是在想要是我失踪了,你也会对别人说我被老虎叼走了。”
说完惠信回自己卧室,打开房门前就闻到了一股臭味,他想了起来,之前离开的时候并没有清理房间里的尸体。现在,他打开窗户通风,首先用火钳夹住捕鼠器上发臭的老鼠装进塑料袋,然后是把黏着密密麻麻的黑点苍蝇的粘纸对折,最后抓住扫帚扫掉蚊香灰烬旁的蚊子。很快的,这个凶杀现场的所有痕迹都消除了,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他怀疑是惠远为了钱杀害住持,又为了消灭人证杀害惠智,嫁祸给不知是否存在的老虎。这样的经过更加合理,人的恶意远比野兽的恶意可怕,但是他没有勇气去验证自己的推理,他是个懦夫。
他感觉头痛,撕开一包甘草颗粒冲泡,他看着颗粒在玻璃杯中先是翻腾,然后沉淀,最终溶化,他没有用汤匙来搅拌干预这一进程,目视透明的热水渐渐变成棕黄色。他啜饮起来,这种颗粒没有加蔗糖,他忍受着些许苦涩沿着喉咙入侵内脏。对于住持也好,对于惠智也好,他并没有多么深的感情,只是习惯了和他们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习惯了住持的唠唠叨叨,习惯了下山回来得给惠智带零食。他们消失让他感到不适。他是害怕变化的人,讨厭不确定的事情,热衷于一成不变的生活,也许这才是他选择出家的原因。
以前他没有单独去做过法事,都是跟随住持去的。他们曾经去为一家养鸡场做过超度法事,那时他连《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都不能背熟,通常是住持大声诵唱,他则模仿,有的地方听不清就不发声直接对嘴型。
那家养鸡场发现了禽流感,需要扑杀全部的禽类,老板觉得这样罪孽深重,于是请了住持去念经。他跟着住持,在满是羽毛和粪便的地面上,他看见工人们挖好的深坑旁边堆积着许多黑色塑料袋。几个穿着白色防疫,戴着纯棉口罩,蹬着橡胶雨靴的人站在那里,像是死神。他们的工作是从笼子里抓出一只鸡拧断脖子,装进塑料袋,等装满后用胶布封口,如此循环。那些禽类无助地鸣叫,空中飞舞着羽毛,总是有一两只从人的手里逃脱,扇动翅膀进行短距离的滑翔,然后又被抓住,咔——咔地拧断脖子。为了确保真的杀死了,工作人员握住脖子先往左三百六十度旋转,然后往右三百六十度旋转。
要扑杀的量不算很大,如果规模更大的话是没有时间把一只只鸡拧断脖子的,会把它们驱赶进深坑,在那些毛绒绒的生物簇拥着,互相践踏以至于分不清彼此时,浇上汽油直接点火燃烧。
消毒水的气味和粪便的臭味混合,在场的人都面无表情,所有的人都只是在工作罢了,包括两个和尚,念经是他们的工作。为了避免传染,他跟住持先是被喷上消毒水,然后在距离较远的地方,站在摆好的香案边开始诵经。他觉得忽冷忽热,身上的汗腺失去了作用,他颤抖起来,声音变得结结巴巴。在深坑旁边停放着一辆大型推土机。司机在驾驶室里偷偷摘掉口罩抽烟,他隔着窗户欣赏眼前的杀戮,产生一种刺激的快感。等他们杀掉全部禽类,司机要做的就是开动推土机把小山堆般的黑色塑料袋掩埋,让这里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不知道为什么,鸡群中混入了一只鹅,发出嘎—嘎的叫声,而工作人员是拧断脖子才注意到手感不一样的,不然根本没有发觉。像是流水线上的工人制造一件件没区别的模具,他们制造一次次没有区别的死亡。这个时候惠信才意识到自己置身于屠宰场,他知道诵经安抚的不是那些动物,安抚的是在场的人类,让他们克服因为道德产生的些许歉疚感。
当推土机填平深坑,巨大的轮胎来来回回夯实土地,留下重叠的条纹状车辙,一切结束了。惠信觉得恶心,想要呕吐,回去之后他发了高烧,住持还以为他染上了禽流感。他为自己冲泡了甘草颗粒,看着颗粒在玻璃杯中先是翻腾,然后沉淀,最终溶化。他没有用汤匙来搅拌干预这一进程,目视透明的热水渐渐变成棕黄色。每当遇到糟糕的事情他都会给自己冲泡甘草颗粒,而且每次他都会感觉到自己痊愈,这次也是如此。
几天之后他和惠远之间的尴尬得到了缓解,也许是他开始适应没有住持、没有惠智的生活了。警察照例来问话,进行现场调查,也照样没有得出什么结论。这次他们在林中的小溪旁找到了野兽的脚印,但是很模糊,不能确定是哪种动物。惠远一口咬定那是老虎:“没错的,肯定是大虫,我能感觉得到。”
而惠信只是看着他,没有质疑。
警察甲说:“如果能找到它的粪便送去化验,那一切就清楚了,说不定还能化验出小和尚残留的DNA。”
警察乙说:“你们自己得注意,实在不行先下山找地方暂住,拜佛在哪不是拜呢。”
惠远说:“是啊,我也有心卖掉这座小庙,再找乡亲募款,在山下盖过一座庙。这里实在是太过偏僻了,夏天蚊虫多,冬天又湿冷,我早就劝过住持的,可他总是不听,唉……”
惠远没有问过惠信就打算卖掉小庙,这让惠信很是不满,但他还是一言不发,嘴巴里咀嚼着野麦的根。惠远最近一直在找住持钱箱,找各种理由把他支开,甚至撬开地砖,挪动佛像。到了晚上,他给长明灯换灯芯,惠远又对他说:“明天去镇上取一下木像,已经做好了,订金早就给过了,只要付尾款就行。”
他隐约觉得小庙外面有一双眼睛在窥视,像两团零摄氏度的火焰。他告诉自己不过是心理作用。但是出于本能的恐惧,他无法否定这种可能。这样的情形或许发生在黑暗中,庞然大物的身躯钻过林丛,触碰横生的枝杈,那植物的骨骼被挤压得一根根断裂。悄无声息中走过自己的窗户下面,出现又消失,中间抽出片刻时间吃掉自己。
而他想不到办法阻止这种情形发生,只是睁着双眼等待黎明。他不知道它在哪里,只知道自己在这里,这是多数恐惧的根源,对方的不确定性和自身的确定性结合产生的怪胎。
第二天,惠远用斧头把旧的药王菩萨像劈作柴火,他则下山去镇上取定做的新药王菩萨像,他带着用来测量的卷尺,防止木匠偷工减料。现在的班车已经不到山脚下了,他是自己骑自行车去的。在清晨出发,到了下午,又骑着自行车回来,后面横绑着油漆还没有完全干的木像,油彩染到了他的袈裟上。
抬高自行车的轮胎,他跨过门槛再解开绑定的皮条,把木像放到庙里佛龛的空位上,双手合十。然后他走在青砖上呼喊惠远,像往常一样,聋了一只耳朵的惠远没有回应。已经是黄昏时分,外面的丝瓜藤上残留着碎片状的光斑,他孤身一人,徒劳地呼唤着一个讨厌的名字。突然,他开始自言自语:“难道你也被老虎叼走了吗?”
他看见被敲起的青砖,敞开的柜子,挪动的木床。思考一下,将这些场景用蒙太奇的手法并列,可以知道是惠远在找钱箱。
他看见后院的土地上有着几个新掘出的洞,在枇杷树下的洞旁边散落着几枚发出反光的硬币。是惠远终于找到了钱箱吗?他的脑海一片空白。在旁边有一只右耳残缺的老虎,它慵懒地躺在地面甩尾巴驱赶苍蝇,像是刚刚吃饱。周围的气候似乎一下子进入了酷暑,空气和糖浆一样粘稠,热得让人焦躁。除去屋檐夹缝里的蜘蛛卵,周围的生命只有他和它,但他和它属于两个物种,不能沟通。老虎终结了他之前的疑虑,惠远没有说谎,真的有老虎,可惠远不知所踪,跟住持、跟惠智一样消失了。毫无疑问,老虎在他之前跨过寺门的门槛,穿过小庙的青砖地板出现在庭院。惠远在别处被吃掉了吗?他的脑海一片空白。电视上说老虎会袭击背对自己的生物,他的眼睛凝视着老虎的眼睛,不敢转开。在他眼里,只有讨厌的和没那么讨厌的东西;在它眼里,只有可以吃的与不可以吃的东西。目光的粘结没有产生交集。可以清楚看见秒钟堆积出分钟,在他眼中时间有了形状,那是螺旋形的。接下来会怎么样?他的脑海一片空白。
也许住持和惠智真的是被老虎叼走的,也许惠远在找到钱箱的一刻碰上了老虎,他想了一下,然后思绪又卡住了。现在,一切发生在山上的问题,无论真假都可以归罪于这头野兽,它不会辩解。
一片片空白如一只只候鸟聚集在一起,他想说:“这不是你该待的地方,回林里去。”然而人与人都无法互相理解,何况人与老虎,他选择一言不发。是啊,这里不是丛林,老虎的花纹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终于,它在树下抬起一条后腿撒尿作为标记,浊色的液体在根部溅开,它慵懒地颤抖起来,粘在皮毛上的树叶纷纷落下。
王陌书,男,1997年6月生,写有长篇小说《我们的我们》《随机之歌》《幽灵备忘录》,小说集《新千年幻想》《草灯狐道中》《现代神话》《生存图鉴》。作品见于各文学杂志。曾获得2017林语堂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