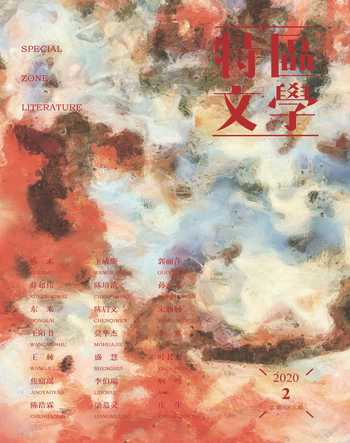文乔治
焦窈瑶,女,生于南京,南京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小说、诗歌见于各文学期刊。诗歌入选《2015中国诗歌年选》(花城版),《2017中国最佳诗歌》等。曾获“重唱诗歌奖”“千纤草女子诗歌大赛十佳诗作奖”等。已出版短篇小说集《暗夜魔术》。
我从来不知道他的真名,文乔治,这是我唯一知道的,对他的称呼。
初春的一个周末,我和一群诗人朋友去云上咖啡馆小坐。这个咖啡馆藏身闹市,隐匿在一爿民国建筑群里,上下两层,外带一个小院,房型结构曲折婉妙,前厅的光线幽暗,一个朋友走到门口的钢琴前面敲了几个音,突然从钢琴后面蹿出个黑影,把我们吓了一跳。丽莎小姐,老板娘的猫,飞快地从我们眼前掠过,眨眼就没了影。
后厅是做咖啡简餐的小厨房,吧台后面做咖啡的器具、杯盘碗碟都清冷冷地空着,也没有服务生在。正对着的后院,那几张带凉伞的小圆桌,几把靠椅也显得冷寂,被阳光清淡地照着,这让我想起这屋子热闹的时候,前后厅都挤满了人,服务生忙得脚不离地,欢声笑语夹杂着欢悦的乐曲,丽莎小姐在螺旋楼梯上爬上爬下。
那天,文乔治就出现在那楼梯之上,手里端着托盘,隐匿在一团稠密的暗影之中。我从来都无法清晰地忆起他的五官,或者说,它们从来是以抽象的方式在我的记忆中存在,连同他这个人本身。影影绰绰地,往那原先耀目的瓷白之上,泼洒了几滩粗凛的斑痕,这就是他,文乔治给我的感觉,在那扩散开去的杂乱之中,却又潜藏着某种狂野的,濒于毁灭之边缘的美感。尽管承认这点并不让人舒服。
在他给我们拼桌,挪移沙发,上茶水和小吃之时,我们有过几次目光接触,那种消失多年的感觉席卷重来,我依然无法辨清他的真实面目,只是裹挟了他周身的阴郁气质和从他脸上源源不断如线瀑般流泻而下的,狡黠的讽意,不断地往我身上飞溅,导致我根本无心听我那群朋友们的畅聊。有个朋友正说起他们家乡的打猎史,怎么打野猪和熊,说什么下大雪时最好打,又有个朋友说起在他老家怎么逮野兔,不知怎么,他们说得越兴奋,我就越发心惊。那个据说叫“文乔治”的人给我们端上了一罐罐啤酒,宝汀顿,英国货,向日葵色的长罐,上面印着酒筒和两只小蜜蜂,说是他朋友送的一箱,一直囤在老板娘这儿,再不喝就快过期了,正好有老板娘的朋友来,就招待一下。
这时小K,就是那个起头说打猎的朋友,开始热情地和文乔治搭话,他以为文乔治是个打零工的大学生(之前的服务生有好几个都是),但文乔治立即就表示他早已经不是学生,他只是在不上班的周末来这“和常来的作家们交流写作经验”,顺便赚些零花钱买酒喝。小K说,原来你也写东西啊,怎么也没听老板娘说起呢。文乔治做了个“嘘”的动作,有点神秘地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摊开写了密密麻麻的一页,在我们面前晃了晃,还没等我们看清就刷地收了回去。
小K指了指坐在角落里玩手机的一个染了黄发的男生:“你可以给他投稿啊。”
那男生是本市某家文学杂志的编辑,此时他显然心不在焉,只是稍稍抬了抬眼皮,但文乔治很干脆地说了一句:“我是不会投稿的。”
一时间屋子里的气氛变得十分尴尬,接下来文乔治的发问更是让这份尴尬转成了诡异。
“你们觉得写小说是道德的吗?比如……我在现实中杀一个人,和在小说里杀一群人比,哪个更不道德?我把自己的隐私,别人的隐私,扭曲、加工后发表出来,以满足一点点现实中得不到的快感和虛荣心,这样真的好吗?”
大家的视线突然不约而同地转向了我,在现场的一群人里,只有我除了写诗,还写小说。
我觉察到事态的可怖,硬着头皮将目光投向我不愿面对的那张脸,但就在话语滑落出我唇边的一瞬,我突然觉得,我面对的只是一个幻影,而此刻,他竟然比我更像我自己。
“那你为什么还要写?”
“为了审判自己。”
文乔治说完这句话就转身离开了,带着堆满瓜子壳、薯片袋、空玻璃杯的大托盘。
在那之后我们还待了多久,我记不清了,总之,那并不是个愉快的散场。等小K,还有所有人一个个消失之后,我独自坐在一排宝汀顿的空酒罐面前抽了一根爱喜薄荷。我平常不抽烟,但那天正好有人(我都不知道对方是谁)递了我一支,就稀里糊涂地抽了,我想着那位文乔治上楼来,我该和他说些什么,说些什么呢?但是等我抽完了烟,又坐了好一会,还是不见文乔治上来,我就下去了。吧台边依旧没有人,后院的椅子上坐了一个正在吞云吐雾的文乔治,丽莎小姐正蜷在他的脚边。
我和牟玛丽的初见也是在初春,在我实习的一家“文化公司”门口。那也是幢独门独户的两层小楼,紧挨着城南的一所私人古宅,老总盘租了下来,改造成几间办公室,地下还有厨房、餐厅和大活动室。牟玛丽比我晚来几周,因为老总想做圣经故事的选本,所以特别招了从香港学成归来的基督徒牟玛丽。
牟玛丽是本地人,身段修长却不单薄,深栗色的皮肤,长直的黑发,眼镜片后面像是轻点上去的两粒小黑钻,很爱笑,说话轻声柔语。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穿黑底红格子的外套,马丁靴,挎一只牛皮纸色的单肩包。不知为何,在我过去的人生经历中,凡是和基督徒打交道,我总是能隐约感知到他(她)的宗教气味,可能是从眼神、语调、姿势,抑或是从他们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宽慈气质之中所感受到的。我会很敏感地获悉对方的教徒身份,牟玛丽也不例外。在我还没有注意到她佩戴的小十字架之时,我就有了预感。
那会我上班总是到得很早,因为租的房子远,在城北,早上怕堵车。每天负责开门的是老总的亲信兼司机,我们都叫他老光,或者光哥。老光之名取自一头灯泡般发亮的青头皮,他生得悍实粗壮,膀臂隆起的肌肉上文了青龙,爱敞着青绿色的外套,脖子上一条金链子露在外面。就在那年春天,老光在离公司不远的大街边逮了个小偷,还负了伤,被光荣写上了报纸,老总召开全员大会,亲自颁发老光一笔见义勇为奖金。于是老光成功甩脱了自己的“混混”形象,那开门的架势都好像大英雄即将大干一场似的。老光总是很准时,唯独那天例外,我和第一天来上班的牟玛丽在门外聊了好久,同事们也陆陆续续地来了,还是不见老光的身影。
那天来开门的是公司的人事赵姐,赵姐说老光休假,这一个礼拜由她管钥匙。就在那一个星期里,我和牟玛丽总是默契地在早晨相会,我们彼此聊了些各自的经历。牟玛丽似乎不太想过多地提在香港的事,只说起在那里读完大学,又教了一年书,因家里人舍不得她一人在外,所以又回来找工作。她谈及家人倒是很大方,父母都是大学老师,每天开车送她上班。我们还未多熟,牟玛丽就热情地邀我去她家,“我家养了两只狗狗一只猫”,“我朋友经常过去玩,我家里房间多,够住,我妈就喜欢我带他们去住,她就喜欢热热闹闹的”。
我想,没有人会不喜欢牟玛丽,至少在我们那个公司,大家年纪都差不多,一多半都是“文艺青年”,容易聊得来。再加上牟玛丽温柔淑静,性格开朗,很快她就和那些同事处得很好,比我都要好。
老光回来后,我在早晨就很少碰到牟玛丽了,我还是踩着那个点到,牟玛丽却会晚很多,总是和一群同事说笑着进办公室。中午在食堂热饭、吃饭时,牟玛丽也不再只和我一个人面对面吃饭,而是坐在大家中间,掀开饭盒,把“我妈又给我带内脏了”说了一遍又一遍。猪肝猪心,鸡胗鸭胗,她把这些统统叫作内脏,我们都知道了牟玛丽有个特别爱吃内脏又想方设法逼着女儿吃内脏的妈妈。
我觉得有点失落,我自感牟玛丽是个需要我深入了解的人,她应该有很多故事,她和这些同事都不一样,因为她实在太爱笑了,言谈举止又太滴水不漏,她热情地邀请每一个同事去她家,可事实是并没有人真正去过。她闭口不谈自己在香港的经历,每每我们问起,她总是淡淡带过。而在女生们聊起明星八卦、护肤美容、减肥瘦身诸类话题时,她又是异常活跃的一个。可我总觉得最真實的牟玛丽是在她谈起每周去教堂做礼拜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她身心的放松和自洽。我相信她不是个会装的人,但我同样相信牟玛丽心里装了一些事,也许是她想弃又弃不掉的“内脏”。
机会来得突然,那天中午几个同事都去外边吃饭了,留在食堂里的只有我,牟玛丽和老光,还有一个专门给老总做饭的阿姨。老光在那头吃得狼吞虎咽,牟玛丽却没怎么动筷子,我问她怎么不吃,她露出招牌式的微笑,只说了三个字:“没胃口。”
老光迅速地朝我们瞄了一眼,牟玛丽突然站起来,将饭盒端到老光面前:“我妈做的内脏,要不要?”
腮帮子鼓鼓的老光重重一点头,目光直直地看着那盒内脏倒在了自己饭盒里,老光一般不笑,那日的笑更是尴尬到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他扒完了剩下的饭菜,说了声“谢了”,随手将塑料饭盒往垃圾桶一扔,就推门出去了。
“淼淼,你有没有男朋友?”
牟玛丽还坐在我对面,手指尖在桌面上轻磕着,身子往前倾了一点。
“以前有。”
我们都沉默了良久,我很奇怪自己的坦率,我并没有和公司里其他人聊过这个话题,当他们问起,我只会简单地回两个字“没有”。但不知怎么,面对牟玛丽,我似乎有点不太介意多谈几句。
“那为什么分手?他劈腿?”
“不,他没有。”
“那是你们家里反对?”
我突然有些后悔放出话来,我知道自己一连串的否定只会将这个追问逼向荒诞的无穷大,所有使我们自己信服的答案里必潜伏一种虚伪,对一段关系的盖棺论定都抹杀了博弈其中人性的复杂。
信神的牟玛丽没有再继续她的追问,她的一双手搭在饭盒上,手指上下摆动着。
“我男朋友啊,是被我从机场抓来的。”
牟玛丽抬了抬眼镜,笑着和我讲了一段她的罗曼史。两个十几年没再见面的小学同学,在香港的机场偶然重逢。“随便抓人帮自己抬行李”的牟玛丽一抓就抓到了故人。
“我真记不清他长什么样了,是他先认出的我。一聊才知道我家搬家前和他家只隔了一条马路,这么多年愣是没撞见过。”
“你男朋友现在做什么?”
“他啊,做生意。”牟玛丽又抬了抬眼镜,声音压得很低,“他不愿意去他老爸公司,跟朋友在外单干。”
“他怎么不留在香港?”
“他说他待烦了,本来想再出国待两年,这不遇到我了吗?”
我还想问问牟玛丽的男朋友到底做的是什么生意,但她已经捧着饭盒站了起来。
“其实我答应他,也是太烦我妈,一天到晚拉我去相亲。”
这时牟玛丽的手机响起来,她抓着瞄了一眼:“我妈。”随即朝我摆了摆手,推门出去接电话。
这日之后,牟玛丽存在心里的内脏,竟像是甩在案板上的生肉,赤裸裸地袒露在众人面前,很快公司上下就传遍了牟玛丽家“胖子”的献殷勤事迹(牟玛丽在食堂第一次剖开了自己,几乎每个同事都有一个机场罗曼史的版本)。很多女生喜欢称她们的男友“胖子”,一部台湾电影里享有“胖子”绰号的男友其实是个瘦削的文艺青年,最后杀了自己的情敌。从牟玛丽口中蹦出“胖子”这个词时,我脑中突然就莫名地闪过这个情节,这让我有些不安。但现在牟玛丽是向大家开放的了,我没有必要关心她的男友是胖是瘦,没有必要再从她身上挖掘出什么(或者说,我对她的兴趣突然有了减弱,就好像某个私人独享的藏宝地突然被向天下昭示了一样)。当他们围着牟玛丽男朋友送到公司的巨型玫瑰花盘尖叫拍照时,牟玛丽仍然保持着她一贯平淡的微笑。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在云上咖啡馆的后院,站在文乔治的正对面。丽莎小姐已经蹿上了墙头,在那些刚刚披绿的枝蔓间游走着,像一只雪白的糯米团滚来滚去。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
他的脸被烟雾轻笼着,他那么瘦,比我初次见他时瘦太多。他曾经真的是个胖子,我还记得那个夜晚,在距离市中心不远的金枫大剧院门口,牟玛丽奔向的那个倚在车门上的黑影。那晚公司为了给自己的产品上线打广告,特意请了一群演员来捧场,办了一场产品宣讲会。散会后已经夜深,由于没找到和我顺路打车的同事,牟玛丽主动邀我坐她男朋友的车,说可以把我直接送到市中心的公交车站。
“这是我男朋友,文乔治。这是淼淼,我跟你说过的。”
这是我第一次得知牟玛丽口中“胖子”的名字,我怀疑这不过是个昵称,就像牟玛丽的真名是牟琳琍,但所有人都叫她牟玛丽。
红玫瑰一大捧,紫色包花纸,递花的文乔治身量高壮,头发浓茂,他将嘴里的残烟拈出来往地上一弹,火星子被双脚重碾过去。
车门已在我眼前拉开,文乔治只是微微冲我点了点头,那种混杂了挑衅和调侃的眼神刺激了我,一路上我都故意装睡,将那俩人遮遮掩掩的卿卿我我拒于眼帘之外。牟玛丽略带粗哑的嗓音像沙子一样在我耳边旋搅着词语的颗粒,像“宾馆”“妈妈”“生日”“换衣服”“护照”“钱包”……这些搭配起来尴尬暧昧的词,能拼湊出什么秘密?每每当我觉得有点头绪之时,文乔治的笑声便如飓风压境,将我无聊的猜想击个粉碎,七零八落……渐渐地,我的意识在暴击之下悬浮起来,陷入了幽暗的梦境……很久之后我都不觉得那是个梦,那就是真实,我更没有向牟玛丽吐露过一丝半毫,虽然在“那件事”发生后我有很多次想开口,但我忍住了。牟玛丽遭遇的危险是不是我曾经遭遇过的?抑或是我移植了我自己的记忆,之于她的境地?总之那个晚上我坚信的是我被双手双脚紧紧绑住,口中被堵了布团,被困在车后座上不能动弹,而我眼前的那两个人,男人掐住了女人的喉管,正伏压在她的身上,女的苦苦挣扎,被男的狠命往车窗边缘撞去……
就在一声尖厉的嘶叫中我惊醒过来,我以为会看到满车鲜血飞溅,可实际上面前只有牟玛丽那张略显疲倦的脸,她摘了眼镜,显得温柔得不能再温柔:“淼淼,快到了吗?”
车子已经停了下来,文乔治的半只胳膊搭在车窗沿上,凉风和烟味刺激得我不停地咳嗽,我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尽快下车。文乔治不说话,也不回头,只是静静地吸他的烟,我朝侧前方指了指,文乔治很快发动了车子,牟玛丽还在温声软语:“淼淼,要不要我们送你到楼下?”
“不用了,谢谢。”
很奇怪,在脱口而出这几个字后,我突然预感到,我和牟玛丽的友谊也许就要终结了。是因为刚才的梦境?那到底预示着什么?说不清,一切都说不清,在亲眼见到“文乔治”之后,什么东西正在崩毁,往着无可救药的方向崩毁……人与人之间,有时候就是这么说不清道不明,有那么一个瞬间你知道,你们的关系该结束了,什么也无法挽回了。
“牟玛丽……我是说牟琳琍,她还好吗?”我在后院的一把靠椅上坐下来,紧盯着文乔治的脸。
话一出口,我就觉得荒诞,这是个根本不需要问的问题,可在当时的情境下,我根本就控制不了那些个字词蹦出口的意愿。
“我们早分手了。”文乔治喷着烟雾,眯起的眼睛像两道黑刀片,在阳光下反射着诡异的闪光。
我的眼前浮现出牟玛丽一张憔悴的脸。“文乔治失踪案”在当初那个公司闹得沸沸扬扬之时,我们都以为牟玛丽整个人会垮掉,但事实上牟玛丽的变化却是在另一个层面上凌空而起,在她依旧温柔的笑容和轻妙的举止背后,有什么过于敏感尖锐的东西正在挑破薄纱(那将牟玛丽整个人裹束在神秘的宗教氛围中的象征物),渗透出被稀释了的血珠。阴白与樱桃色的混合,这让牟玛丽作为一具真实的肉身更加真实,可也隐匿着一股不安的疯狂,表现在牟玛丽坐在食堂的餐桌边大嚼内脏时颤抖的手指上,表现在某个下着倾盆大雨的中午牟玛丽提着伞闯入办公室浑身湿透,一脸的失魂落魄中(他们都说她是故意跑出去淋雨的)。最令我们感到惊惧的一次,是在某个夏日的晚上。为了宣传公司推出的名著线上多媒体产品,老总搞了一次“读者俱乐部”的活动,召集了一群书友,几个人一组围坐在小楼前面的空地上,每组出一个朗诵或是表演节目,可以使用多媒体(那天下午我们就在那里布置,拉起了屏幕,摆放了音响,连接好了电脑等等),末了还有交流讨论的环节。这些书友有一大半是我们各自拉来的朋友,再就是几个从网上获悉讯息的网友,活动开始后吸引了一些饭后散步的老人和小孩,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嘈杂。老总在场时,我们还像是在搞活动,等他临时提前离开,整个场子就成了放飞自我的夏夜Party,几个同事开始起哄着拿话筒唱歌;喜欢小孩的女同事将钻进桌肚的小孩子抱起来,喂他们吃冰淇淋;还有一拨人竟然拿出了自带的啤酒,边喝边打起了扑克牌……
牟玛丽在那晚离奇地古怪。她到得很迟,大草帽,黑墨镜,一袭无袖素雅旗袍搭配白色高跟鞋,左右后方跟了三个年轻人,都是身材俊拔的帅小伙,各自穿了一身黄、白、黑色的运动衫裤,黄衣小伙戴眼镜,白衣小伙戴鸭舌帽,黑衣小伙是个光头。就在光头小伙为牟玛丽点烟之时,我注意到正在搬矿泉水箱子的老光,没错,就是老总的司机老光,那个经常在牟玛丽没胃口时吃掉她饭盒里的内脏的老光,眼睛直直地盯住了她。那整个晚上老光都坐在牟玛丽斜右方的座位上抽烟,他的眼神就没偏离过那四个人。老总离开时他跟着离开了一会儿,但很快就回来落座,开始不断地喝矿泉水,一直到牟玛丽离开,他没有再抽一根烟。那三个小伙跟牟玛丽围坐在一起,那是最小的一张桌子,正好只够围坐四个人,就这样他们聚在一起唧唧哝哝,吞云吐雾,自动隔绝在那晚的活动之外,直到那个叫周彤的女同事主动走近了他们。
周彤,一个看上去就很会“来事”的女孩儿,身材娇小、丰满,烫了一头焦糖色的长卷发,五官犹如熟透了的果子一般飘溢出肉欲的气息。他们都说文乔治“失踪”的事,就是周彤先传出来的,但牟玛丽似乎毫不介意,她不介意他们说“牟玛丽家的胖子骗色骗钱把她耍了”,也不介意他们说“那个渣男搭上了人命案跑路了”。当然,这有可能是牟玛丽根本就不知道这一切,我已经说了,当时她的变化是“在另一个层面上”发生的,和“文乔治失踪”这件事,可以说有关,也无关。
牟玛丽的午餐便当里,依旧有一盒卤过的动物内脏,但她突然就不吃了,回回都拨给了老光。老光呢,总是闷声不响地享用完毕,在他扔掉自己的塑料饭盒的同时,还会顺手拿过牟玛丽的饭盒帮她洗掉(这只是一些传闻,传闻还说老光和牟玛丽总是最后离开餐厅,他们会在一起聊一会,有几次牟玛丽情绪失控哭起来,老光还给她递纸巾)。这个传闻在我眼中成为变形的具象是在某个清晨,我走进公司大门,正撞见他们倚在二楼栏杆上聊天,不,他们也不像是在聊天,彼此隔着一段距离,手指间都夹着烟。那是我头一回看到牟玛丽吸烟,动作十分地娴熟优雅。牟玛丽勾住栏杆的姿势常常让我心惊,好像她一个前倾,就会跌落下来,但她只是无意识地撩着发丝,是一种空洞的撩,可她的眼神、表情一点儿也不空洞,她脖子上的十字架微微闪烁了一下,她的人就不见了,同时不见的还有老光。
谁也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或者,什么也没发生,但确实是有事情发生了。
那个晚上的事情也是,发生得若隐若现,若即若离。据说,向来和牟玛丽相熟的周彤先是夸赞了一番牟玛丽的新旗袍,然后就主动问起文乔治的事,就是那一刻牟玛丽透露给了周彤一个略显“惊人”的消息。据说,牟玛丽的语态很镇静,她说文乔治是在“玩失踪”,他一个人在外面躲债,连家里人都瞒过了,他现在急需一笔钱,牟玛丽问周彤有没有闲钱可以借她一点。据说,周彤听到此处脸色大变,她骂了文乔治“渣男”,还要牟玛丽“赶紧离开他”,在她说出这话时,那三个小伙子对她流露出不友好的(甚至带有某种威胁意味)眼神,于是周彤立马走了开来。在她后来的描述中,牟玛丽那时仍然戴着墨镜,看不清她脸上的神情,但她觉得“牟玛丽在哆嗦”,“她肯定得出事”,但周彤并没有再上前表示关心,周彤说她“觉得有点害怕”,“那三个男的,不知是什么来路”。
本来,那个晚上就要这么结束了,在一片无聊的闹哄哄之中。部门主任开始指挥几个男同事收拾场地,就在他们正准备撤下音响和话筒之时,宛若一阵隐秘的旋风一般,我们就看到一抹幽蓝从最后面的角落荡漾到了最前面,话筒被那个精灵般的人儿抢夺在手里,宽檐草帽轻轻抖落,跟随而来的某双手及时接住,重新旋进暗影之中,留下裸露了两条瓷白胳膊的牟玛丽,在夏夜暧昧的灯火中微颤的牟玛丽。牟玛丽开始唱歌,唱的是王菲的《红豆》。
我们都没有想到,牟玛丽唱歌会唱得那么动听,但也可能,是我们不得不觉得她唱得那么动听。他们说牟玛丽的墨镜下面流出了眼泪,但我离得实在太远了,没有看到。我看到的是唱到“有时候/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的高潮处突然崩溃了的牟玛丽,他们将瘫坐在地的她围了起来,那黄白黑三个小伙,一层又一层的人又将那三个小伙围了起来。
“看什么看,都散了都散了!”
将那一群人喝退了的,是老光。来接牟玛丽的是一辆奥迪车,将她抱上车的,是那个光头黑衣小伙,黄衣小伙和白衣小伙一左一右,一个戴着牟玛丽的草帽,一个戴着牟玛丽的墨镜。
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发出这句感叹的是周彤。
有好长一会儿,我和文乔治在云上咖啡馆的后院干坐着,谁都没有再说话。文乔治侧对着我,默默吸他的烟,丽莎小姐蹿进了他的怀里,他像个电影里的黑帮大佬一样摩挲着白猫的肉躯,突然朝我扭过头来:“你信教吗?”
“这与你有关吗?”
“牟琳琍没和你传教?”
“没有。”
“是吗?”文乔治额下的两道黑刀片再次出现,我的皮肤上竟然隐隐有了痛感,这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琳琍想让我信教,可我做不到。”
快垒满的烟灰缸里又被甩了一根烟蒂,文乔治晃了晃那個中南海的烟盒,从里面掉出仅剩的两根。
“来一根?”
“我不抽烟。”
“你刚才不是在抽?”
我瞪了他一眼,他耸耸肩,将丽莎小姐往地上一放,叼着烟站起来点火:“很早以前,我学的是哲学,后来我爸把我送到香港学金融,没意思透了,我就开始胡来,怎么开心怎么过,泡酒吧找女人抽大麻……总之到最后也烦透了,后来遇到琳琍……我没想到会在香港遇到她,小学时我们做过同桌……都是太久以前了……琳琍兴奋得不得了,她好像在香港过得也不是很开心……其实我对她的印象……真的是没什么印象,我喜欢的女孩不是她那样的,她是那种父母管得特严的乖乖女,我就觉得她们没劲透了……哈,突然想起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跟琳琍是一样的……”
“所以我也没劲透了?”
“我看过你的小说。”文乔治将没抽几口的香烟摁灭在烟灰缸里,因为前面来了客人,已经上了楼。他走到吧台后面捣鼓了一阵,端了盛了吃食饮料的盘碟走到我面前,摆了一杯果汁和一碟开心果,随即就上楼去了。
丽莎小姐又开始在我脚边绕来绕去,我觉得很烦,也想一走了之,但我有点不甘心,牟玛丽的故事还没有被填补上空缺的部分,现在机会来了,我不能就这么浪费掉。
那根孤零零的香烟被我捡起,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点上了。这是今天的第二根烟,我抽得依然很不爽,边抽边咳嗽,我平时根本就不抽烟,但我很喜欢在小说里写抽烟的女人,我笔下的女主人公几乎都是烟鬼。
“你抽烟是谁教的?你男朋友?”
站在吧台后面的文乔治一边洗手一边问,我这才注意到他已经下来了。
“没人教。”
“琳琍抽烟是我教的。”文乔治甩着手走过来,又蹲身抱起丽莎小姐逗弄了一会,放她去了。
“你刚才说,看过我的小说?”
“是啊。你的小说可比你这人有意思多啦。”文乔治那黑刀片似的眼睛显得柔软了一些,倒像成了黑巧克力的感觉,“你和琳琍……你们多少还是有点不同……琳琍不写小说,就这一点看,还是你比较危险。”
“我危险?”
“作家都是危险的,女作家尤其危险。”
“这么说你也是危险份子?”
“写小说这事,以前我是看不上的,我需要实打实的刺激,能让自己身体感受到冲击,渗入骨髓的痛苦……哲学更不适合我,我学哲学是因为我那时觉得人生太无聊了,我想知道人为什么要活着。”
“那你现在知道了吗?”
“和琳琍恋爱那会,我感觉我知道了,但后来……后来又不知道了,琳琍说,和她一样信教,信上帝就会知道,不但会知道人为什么要活着还会知道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所以你就去躲债了?”
刚刚软下来的黑巧克力瞬间又像黑刀片一样显出锋利的韧度,文乔治张大了嘴巴“啊”了一声,脸上的肌肉不自然地抽搐了几下:“啊,是啊,躲债……”他的手开始不停地摩挲着下巴,“是,我是有了点麻烦……我就是个混蛋……我想这回琳琍该死心了……她说她会帮我,帮我借钱……”
他整个人突然瘫软下来,双手往头上使劲拽着头发,骂出了一句脏话:“操!”
我将好不容易抽完的烟蒂甩在烟灰缸里转身要走,文乔治仰面朝我又开口道:“我去找过她,想还她钱,不敢去她家,就跑到你们公司……就是那个两层楼的……我被他打了,是我要他打的,我让他狠揍了一顿,揍得满脸是血……我说你揍我吧揍我吧,我想知道人为什么要活着你能告诉我吗?神经病,他骂我,他要我滚,再也不要让他看见。”
“他?他是谁?”
虽然在那个瞬间我已经知道了他是谁。
那个夏日夜晚过后的第二天,牟玛丽没有来上班,我们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她(那之后不久,周彤和我也相继离开了公司)。来办公室收拾她物品的,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子,脸型和牟玛丽相差无几,眉眼要妩媚得多,但很显然她不会是她的亲姐姐(我知道牟玛丽是独生子女)。她将一叠文件和零碎物品收掇进一个大包,旁边的部门主任提醒她,桌子下还有一只小冰箱。女子皱了皱眉说了声“不要了”,随即将桌上相框里的那张合影撕了个粉碎,连同相框一起扔进了垃圾箱。
那只小冰箱是文乔治当初开车亲自送来的,因为食堂的冰箱只能老总專用,我们平时只能自己冷藏带来的饭菜。牟玛丽主动请几个同事和她合用,现在这只无主冰箱就置身于一个尴尬的境地。我们都没有再打开它,到了午饭时间,就看到老光撸着袖子大步走进来,在牟玛丽空荡荡的座位上扫视了一圈,随即一把抱起了那只小冰箱。眼看着他那架势,我们以为他会将那东西“咚”地一下扔下楼去,但他只是抱着它走上了长廊,转眼就消失不见。
没人再见过那只冰箱,几天后老光代老总发话,说是食堂的冰箱大家可以随意使用了。我们有很久没见到老光,主任说他出差去了。
我们再次见到老光,他坐在食堂的餐桌边,大嚼着一盒内脏,嚼着嚼着,他突然奔到洗手池边,双手紧紧扒住池沿,垂下光溜溜的脑袋大口呕吐起来……
就是这个形象,这个场景,每每想起,还是令我感到痛苦,所以文乔治后来又和我说了什么,也许是真话,也许全都是他胡编乱造,这一切都无所谓了,我统统都记不清了,也许是我故意让自己记不清。但我记得我离开时文乔治的姿势,蜷缩在椅子上像只蜗牛,扳着自己的脚不知在看什么,丽莎小姐在他脚下蹿来蹿去,我觉得他很孤独,一个孤独的人突然写起了小说,他大概已经知道他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了?
那一天,我走出云上咖啡馆时还在想,文乔治是谁?老光又是谁?我都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名姓,就连牟玛丽,牟琳琍,还有那个周彤,我也不知道她们是谁,他们就像一阵风,来来去去,刮走了我生命里微薄得不能再微薄的一段时光,我真的有必要去关心他们的命运?
但我忍不住不关心,好像一个人在另一个人生命里的出现,一些人在另一些人生命里的来去,都是有缘由的,有因果的。有时候,我就是他们,他们就是我,我需要一些勇气去担当,是替他们去担当,担当他们所担当不了的,尽管这担当改变不了现实,改变不了所有人的命运。我不能让牟玛丽不崩溃,让老光不呕吐,我不知道上帝能不能做到,也许牟玛丽会觉得上帝做到了,她嫁了一个同样信基督教的男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老光打了文乔治,从此再也不碰动物内脏?
是这样吗?会是这样吗?也许我应该得知的是另一种结局,那是真实的,无奈的,任何人力都无法改变的……但我真的得知了吗?接受了吗?
文乔治,一个我仍然不知道他真名的男人,再次从云上咖啡馆失踪,同时失踪的还有老板娘的那只白猫,丽莎小姐。
据说文乔治留下了一个笔记本(应该就是他曾经给我们看过的),上面有他一篇未写完的小说(姑且称作是小说),小说的名字叫《刺杀文乔治》,但我们谁都没能看到,那个笔记本已经被愤怒的老板娘付之一炬。新来的服务生是个留娃娃头的大眼睛女孩,我也再没有再在那里喝过黄罐的宝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