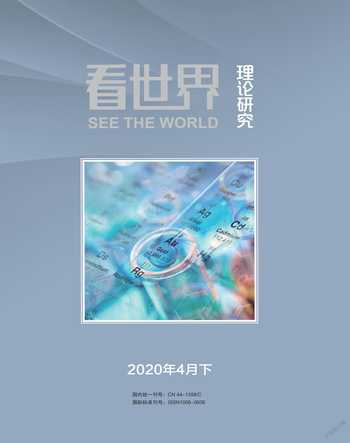从“六学”与“明学”看新媒体环境下的网络语言
摘要:随着新媒体的兴起,网络语言越来越受欢迎,新媒体自带独创的传播机制、快捷的传播方式和独特的文本要求,使得网络语言往往呈现一种病毒式的传播,蔓延极为广泛,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从去年至今年,先是以六小龄童经典语句为原型创作的“六学”语言,后是今年暑期以黄晓明相关语录为原型生发的“明学”语言,在短时间内迅速充斥整个网络,遍布微博、知乎、虎扑等各大平台,本文将从汉语语言学的视角出发,分析新媒体环境下以“明学”“六学”为代表的网络语言呈现的特点,探讨“六学”与“明学”的语言化用和传播原理。
关键词:“六学”;“明学”;语言化用;网络传播
概念界定与研究现状:网络语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网络语言是指在网络交际领域中使用的各种语言形式,包括与网络和电子信息技术有关的计算机编程语言和网络专业术语,也包括人们在互联网上用于交际的自然语言。而狭义的网络语言是指网民在互联网上用来交际的语言。本文主要谈的是狭义的网络语。
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新的媒体形态,是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的传播形态和媒体形态[1]。关于新媒体环境下网络语言的研究,近年來十分热门。由于网络语言的爆炸式发展,其更新换代速度越来越快,对于2018年下半年以来较为流行的网络用语研究已显得有些不足。本文以最近兴起的“六学”和“明学”语言为例进行分析研究,具有较强的前沿性和时代感。
研究方法:
(1)资料收集法。通过对网络环境的亲身体验和观察进行收集,语料来源主要为新浪微博、豆瓣、知乎、虎扑等大型平台.
(2)分析归纳法。在研究过程中,通过对语料的考察和分析,试图客观归纳出网络语言呈现病毒式传播的原因,进而探究网络语言流行背后的大众心理。
一、“六学”与“明学”的语言化用现象
“六学”源自饰演86版西游记孙悟空的六小龄童(本名章金莱),近年来,网民们自发对六小龄童的言行进行批判和总结,并戏谑地将其汇总成为“六学”(sixology)这一学科。“六学”的主要内容分为两类:(1)以金句、成语为代表的语言化用,主要表现为句式套用和谐音梗两种;(2)以六小龄童为原型,以表情包为载体的图片迁移。1而“明学”,是围绕明星个人的语言和行为,重点研究相关经典语录和规律的学问。其内容也可大致分为两类:(1)古诗词与“明言明语”相结合的创造与再创造;(2)以gif动图、视频为表现形式的综合传播。
“六学”最早在知乎兴起,其发展已有几年历史,然而从去年起,套用六小龄童模板进行发挥的网络语言迅速在各大平台蹿红,连“人民网”等官方媒体都开始运用“六学”体发微博,足见其流行之广和影响之大。同样地,明学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年前黄晓明参加综艺《全员加速中》,主要被网友们以记录和点评其霸道总裁式常用语等传统方式进行研究。今年夏天,在综艺节目《中餐厅》火爆前后,以芒果台为代表为网友们带来了大量“明言明语”的第一手资料,促进了明学流派的进一步发展,为明学注入了新的生机,更多网友采取了分析与创造结合的方式,从语言学、心理学、哲学、影视文学等多个角度进行挖掘,获得了广泛的研究成果,它不仅蔓延在网上冲浪的各个领域,也成为“反杠精”的标准句式,更是与“六学”一样被官方媒体——比如曾在CCTV的《共同关注》栏目中被主持人朱广权引用。自此,“明学”与“六学”并立于学术之林,成为21世纪网络语言界两大显学。
“六学”和“明学”研究由来已久,可始终在小众范围内传播,不曾大范围走红,而当两者的语言化用产生后,在很短时间内便蹿红各大平台,或许很多人并不理解这些戏谑背后的深层含义,但几乎人人在网上都或多或少见到过这些言论。
“六学”的谐音梗主要与六小龄童的本名章金莱相关,如“违章”:指违背了章老师的意志,要向全国人民谢罪;“章口就莱”:原指章金莱老师总能逮到机会宣传自己的作品;“无中生友”:指章老师在录制节目时总说外面有小朋友问自己“孙悟空叔叔有几个女朋友”,此处不再一一举例。而所谓金句套用是根据六小龄童大量同质化微博内容改编,大致模板如下:“惊闻……我不由想到我……的故事。明年年初,中美合拍的西游记即将正式开机,我将继续扮演美猴王孙悟空,我会用美猴王努力创造一个正能量的形象,文体两开花,弘扬中华文化……”。以司法考试为例:“惊闻最近大家刚结束法考,十分艰难,说到困难,我就想起了我在86版西游记中饰演的孙悟空克服九九八十一难,明年年初,中美合拍的……”2。
而“明学”一派则创造出了以“明言明语”为基础的古诗改编。如“霜叶红于二月花,行李两人一起拿”“兰陵美酒郁金香,听我的不许受伤”“春潮带雨晚来急,我不觉得这是问题”“春风又绿江南岸,听我的我说了算”“留取丹心照汗青,开会一定好好听”3等等。严肃的诗歌形式碰撞上网络语言的生搬硬套,构成十足的反差喜感。此外,网友也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开展了霸道自信的晓明式语录的自发运用,无论是你的领导、情侣还是素不相识的网友,似乎人人都可以在某个瞬间变成“黄晓明”。“明言明语”在面对冲突的观点时尤其地适用,当有杠精声称“只有我一个人觉得xxx吗?”时,你便可以用一句“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轻松堵住,无论对方的本意是什么,以不变应万变,都给你强行扯回来。将剑拔弩张的辩论消解在显然未经思考的程式化回应中,令人啼笑皆非。
这一出出嘲讽两人的“黑话”游戏,起源两人的个人表现,却都高潮于网友的自发联想。关于此类格式流行语,从“凡客体”的网络爆红就开始了,广大网友就此竞相模仿,使语言结构的效仿成为极具新网络语言风格的表征之一。以特定的句法结构为框架,根据上下文语境,联系热点时事,网络写手们灵感迸发,只要与“六学”、“明学”文本相近,就能强行联系,产生新的文本,并进行鬼畜式的重复和改编,在互联网上形成病毒式的蔓延。
二、“六学”“明学”语言化用的病毒式传播原理
对于语言的病毒式传播,在这里借用孙喆的概念定义:“受众在主动接受数字化信息的同时对其进行加工,并向基于相似信息获取和分享需求的人进行发布和转发,进而形成信息迅速以人际圈席卷群体并波及大众的无偿复制、几何倍增的传播形式。”[2]形成一个完整而连续的传播机制需要三个关键性的要素:一是作为“病原体”的传播内容,即“明言”“六语”;二是具有接收者和传播者双重身份的易感人群,即活跃在各大平台的网民们;再次是作为病毒扩散渠道的传播途径,即新媒体;在这三个要素共同作用下,“病毒”发生“感染”,“明言”和“六语”发生无限复制、改编和增殖。
(一)强大的“病原体”
首先,两人早期曾活跃在大荧幕上,早已为观众所熟悉,话语原型具有很高的关注度,因此,在两门学问复兴之时,其群众基础已经相当雄厚,人们能迅速做出评判,并广泛地参与到“六学”“明学”语言的改编中来。其中,谐音词流行的内在原因,主要是音节的简化。汉字的每个音节都是由声母、韵母、声调三个部分组成的,声调由原来的8个简化为4个,声母由原来的35个减少到22个,韵母由原来的142个减少到39个,数量变化极大。因此,人们可以用有限的音节去对应无限的汉字,从而导致大量同音词的出现,在语用的过程中用以形成大量的谐音现象。此外,输入法的作用也不容小觑,汉字输入法一般采用拼音输入,为了让网民的沟通更加高效便捷,往往只要打出几个首字母,输入法就会为我们自动联想近期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比如在输入法上打出“zkjl”,“章口就莱”就排在第三位,当打出“我不要”时,输入法就会自动弹出“你觉得”,这为“六学”和“明学”的传播推广作了非常大的贡献。除此之外,语言自我进化的潜力是无穷的。在浩如烟海的网络信息中,句子模板化语言类型一直十分显著,类似于传统语言的仿写。人们可以根据不同语言环境和语言表达的需要,参照某一种模板,另造与原句的句式相同、内容相近的句子。语言系统的成分是有限的,包含有限的词语,如“中美合拍”“文体两开花”“听我的”以及特定的句法结构和联想模式;而言语是无限的,人们可以在这个特定的语言系统中创造无限的句子,对固定的语言材料进行复写,引入新词,并创造新的句子。通过替换个别语素或词汇,便可利用网络语言的衍生性產生大批新的段子,上至政商学,下至工农兵,人人皆可熟练掌握套用,真正做到无门槛表达,各个行业、各个领域都能掌握并运用该种句式的改造。人们在迅速掌握话语模板后,便轻而易举地复制,并进行源源不断的改编和再创造,形成病毒般的传播。
(二)双重身份的“易感人群”
病毒式传播中,传播主体的最大特色就是信息接受者和传播者的双重身份。他们往往能从信息传受中获得某些收益,如娱乐、人际关系、信息获取等,整个过程完全是主动进行的。网民们对“六学”“明学”的语言化用便是处于这样一个“主动获取——自觉接受——主动再传播”的模式之中。这些语言的易感人群大多在15岁——40岁之间,他们乐于网上冲浪,常年混迹b站、虎扑、知乎各大平台,善于造梗、讲“黑话”,且往往紧密联系时事。同时,他们又肩负学习和工作的压力,因而具有更强烈的“娱乐至死”精神和解构主义倾向,更乐于对六小龄童所代表的孙悟空形象和传统言情青睐的“霸道总裁”形象进行消解和颠覆。此外,互联网大量的碎片化信息使得受众应接不暇,使他们对信息的敏感好奇程度大大降低,逐渐产生审美疲劳,化用名人语录对名人进行嘲讽,对他们来说更刺激,更具有挑战性。模式化句式大面积流行,其背后还有大众追随潮流的心态,这种全新造句的潮流不单单是因为寂寞,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共鸣,人们借助“六学”“明学”这类工具识别同类,划定交际圈,并通过相关语言的使用不断增强这一交际圈的认同感和黏合度,从而加速了语言信息的传播。新媒体环境为受众提供了一个庞大的议题市场,信息不再是从传播者“推”向受众,而是由受众充当议题“把关人”的角色,从中选出感兴趣的信息,心甘情愿受到“感染”,而后,“被感染”的受众往往又出于信息共享、实现自我表露或成为意见领袖的愿望,主动将病毒信息散布给具有共通空间的人[3]。
(三)新媒体时代的传播途径
作为无限自由、开放、交互性的交集分享平台,新兴媒体极大解放了公众的话语权,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媒体,每个人都可以在浩瀚的时代洪流里发出自己的声音,更趋于口语化和随意性,使得网络语言具有多样性和不规范性。并且,由于如微博等平台对字数的限制,以及信息的泛滥膨胀,使得传统意义上长篇大论的叙述手法已经不再适用,人们在回复和发帖上都尽量压缩文本内容。“章口就莱”、“文体两开花”、古诗金句套用等固定语句,言简意赅,背后含义浅显通俗,这与碎片化时代的要求相适应。新媒体时代的病毒式传播区别于传统传播依赖于大众媒介和口口相传,其文本易于复制和扩散,从而不断蔓延,从而实现“病毒”的全面传播。
因此,在新媒体的环境下,“六学”与“明学”语言的传播更具爆炸性,“病原体”一经引爆,“病毒”在短时间内迅速加倍复制和增殖。由于每一个被“感染”的受众都拥有自己的信息传播圈,因此,他们的每一次转发、评论都可能会携带许多潜在的受众,当这些潜在受众也进行转发,病毒感染者的范围就会进一步扩大,病毒的传播也会呈几何式增长。
三、对病毒式传播的思考
新媒体环境下网络用语的扩散能力无可置疑,但倘若“病毒”感染一发不可收拾,后果也令人担忧。在“明言”“六语”迅速传播的过程中,网民们难免会陷入唯恐落后的情绪与盲目从众的心理,以戏谑来娱乐,以恶搞来反抗,甚至导致畸形的审丑文化。不过,在当下的网络亚文化生态圈里,没有什么能永垂不朽。互联网是健忘的,浪潮式的兴起——短暂的狂欢——讯速的寂灭乃是网络话语的发展常态。新词汇的逐渐产生和旧词汇的不断消亡是语言发展的一个必然规律。对于以此解压、反抗的网友来说,有趣新鲜至上,总会有新的“梗”被抛出,来取代陈旧的表达。如今网络用语的更新换代速度不断加快,如去年流行的“先定一个小目标”等,今年已经很少见到。对“六学”和“明学”语言的反复恶搞和追捧热潮,也难逃速朽的命运。
四、结语
词汇系统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它是一个持续发展的动态系统。层出不穷的网络流行语丰富了汉语的词汇,为这个系统输入了新鲜的血液,使其健康地新陈代谢。此外,社会发展迅速,新的事物和新的认知不断产生,原有的词汇库缺少反映相应变化的词语,网络流行语的产生则有效地填补了这个交际的空白。“六学”与“明学”的语言化用打破了讲话的知识体系,形成了新的审美风格,在幽默的语言背后隐藏着暗讽的锋芒。当语录已经成为一种“梗”时,其语言本身的含义早已从原有语境中抽离出来,形成空泛而又开放的固定形式,为语料的复制、改编、传播创造了条件。不过,正因为其缺乏深度,仅停留在对知识的简单复制,会加深审美的快餐化。“明言”“六语”的传播,也许正是新媒体的迅速发展下,娱乐至死的时代产物。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网民人数的不断扩增, 网络语言逐渐走进大众的视野, 语言使用者常常故意偏离语言常规, 创造性地使用一些语言, 由此产生许多网络语言的变异现象。一方面, 这些语言变异现象可为现代汉语的发展注入新鲜活力;另一方面, 这些网络语言变异现象也对传统语言规范造成了冲击。因此, 应对其加以规范和正确引导, 以减少网络语言带来的负面影响。
注释:
1.对“六学”的资料整理主要出自知乎。“六学”反对的主要是六小龄童如下几个方面:因循守旧——在演讲生涯中不断重复过往的话语,出现数量惊人的复读情况,这与去年爆红的“人类的本质是复读机”遥相呼应。德不配位——六小龄童仅扮演了一版孙悟空,却把自己当做吴承恩先生在世唯一代言人,肆意改编戏说《西游记》。见利忘义——章金莱禁止他人恶搞西游记,却代言许多恶搞西游题材的电影、作品、电视剧,以及不分场合强行宣传个人影片。但我们不能一味批判六小龄童,对于六小龄童的演技及相关成就依然应该给予肯定,抓住事物的两面性才能更好地认清“六学”。
2.为更好说明“六学”的化用,类似例子还有“惊闻最近考英语四六级,说起六,我就想到了我六小齡童,明年年初中美合拍的西游记……我将扮演美猴王……”以及“深圳天气”官博发表的“天气持续干燥,大家要注意用火安全,说到空气干燥,就想到西游记中唐僧师徒经过干旱的西域各国,……开机……文体两开花……”“天天玩这个梗有意思吗?像复读机一样。说起复读机,我就想起了我自己……”
3.“明学”古诗改编的资料整理来源于微博和bilibili的鬼畜视频,语料主要来自黄在综艺节目《中餐厅》里作为店长的言论,此类视频意在嘲讽其强行营造的“霸道总裁”人设。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新媒体——媒体形态的一种
[2]孙喆.新媒体环境下的病毒式传播——以神曲《江南style》为例[J].今传媒,2013,21(06):52-53.
[3]张曼. 网络微博语言的个案性分析[D].广州大学,2012.
作者简介:
冯语潼(1999—),女,山东省烟台人,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武汉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