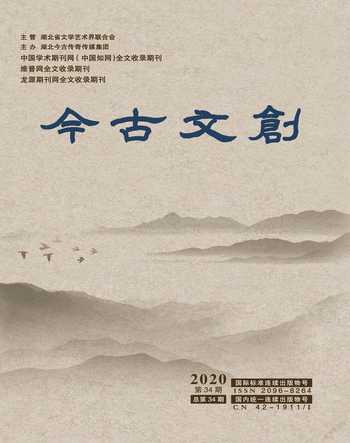破碎的噩梦
田戴瑶
【摘要】 剧情片《梦之安魂曲》是禁毒题材中对于“禁毒”体现得尤为明晰的一部影片,与《猜火车》等同为毒品题材的电影不同,该片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出发,在电影发展中中体现出弗洛伊德的梦的加工机制,剧情设置则体现出穆尔维所论述的影像与叙事机制交替,以及看/被看的二项对立世间的叙述与影像序列,使电影非常具有层次性,展示了瘾君子世界里浓郁的绝望和凛冽的寒冬,具有非常强烈的黑色电影风格以及反毒品导向。
【关键词】 梦;女性主义;禁毒电影
【中图分类号】J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34-0071-02
一、男性与女性
该电影中一共有两条故事线索,一条是以哈瑞的母亲萨拉及其医生、朋友为主的故事线,另一条则是哈瑞与好友泰伦以及女朋友玛丽安的故事线。两条线索相互平行而互有重合,如在影片一开头则是儿子贩卖母亲的电视机的冲突点,运用了分屏的手法来体现母子之间的疏远,在这部影片中,哈瑞的角色是整个电影的线索和讲述人,在穆尔维的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中论述了主动/被动的两性劳工分工的叙事结构,穆尔维认为“奇观与叙事之间的分离,支持男性角色作为推动情节发展、促使事件发生的主动的一方”。
在影片的一开始,儿子强行带走母亲唯一的娱乐工具电视机,而且质问母亲“为什么要让我有罪恶感呢”,而母亲则只能懦弱地躲在锁起来的门后从钥匙孔看着儿子带走自己的电视机,而无力安抚儿子的情绪。错误的一方在这里占据了绝对上风,而懦弱的女性则处于绝对从属地位,母亲的地位是绝对被动的,而男性是作为权利代表出现的,在同题材电影中,如《猜火车》《发条橙》《疤面克星》《大毒枭》等毒品类电影中,大部分为男性主人公,影片围绕观众认可的主导型角色来构成影片,进而推动进程,这样的设置使观众将注意力集中于观众自身的荧幕替代者,即电影的主人公身上,从而使电影人物控制事件发展的权利与观看的主动性的权利相结合,两者结合给予观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感,进而转化为一种生理上的快感。毒品许多国家是被法律禁止的,而一些毒品对身体的伤害也阻止一部分人尝试,而在这种心理认同中,观众能够得到一种与这种男性主人公在权利的顶端以及在感官上的极致快感,进而达到一种心理高潮。
二、幻想与现实
20世纪提出的梦工厂,就已经包含了电影/梦的类比,在弗洛伊德“梦的四种机制”中,提到了一个二次加工机制,而这些论述梦的理论类比到电影中也有着极其相似的功能,梦的二次加工与电影对于素材的加工的类比是有意义的,而在吸毒者这个特定群体中,幻觉在吸毒者的生活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吸毒之后的致幻性是他们的快感来源,根据弗洛伊德对于梦和白日梦的论述,如果说梦与白日梦的区别在于二次加工的程度不同,白日梦相较于梦境二次加工的程度更强,并且有一定的自主性去重新编排那些童年的记忆素材,而吸毒之后的幻觉更像是二次加工程度更强的白日梦,这种幻觉更加反映了一个人的潜意识,更加能够反映出人物埋藏于深处的愿望的满足。
三、得到与失去
在《梦之安魂曲》中,萨拉是一个值得分析的重要角色。弗洛伊德在《性欲三论》中把窥淫癖看作是性本能的构成要素之一,并且认为窥淫癖在本质上是主动的,而从电影中来看,萨拉是一位喜爱甜食、中年丧夫的独居妇女,唯一的儿子与自己的关系也不是很好,她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看电视,是一位忠实的电视迷,而当她接到电视台通知她被选中录制节目的电话后,萨拉似乎重新焕发了光彩,她希望能够在电视上美艳动人地穿着红色裙子,就像她年轻的时候去接送儿子的时候光彩照人的样子,正如萨拉所说“你爸爸非常喜欢这件,我现在仍然能记得当时他看我的眼神”。萨拉在这种来自丈夫的凝视中感受到了来自异性对于她个人魅力的肯定,是精神分析中最原始的性动能,在这种男性的肯定中,她能找到一种价值,而现在她已经孤独而衰老,她非常想展示出她最为动人的一面,在这种在舞台上被别人窥视和称赞中得到一种性源欲望,类似于弗洛伊德所说的自我力比多的技能,激发自身本能的一种原发的动能,去复制年轻时候的快感,而这种对于凝视的欲望的满足渴求,也导致她过度依赖减肥药而导致坠入毒品的深渊。
电影中还存在着另一个女性人物,哈瑞的女朋友玛丽安,她是一位美艳动人的瘾君子,同题材电影中,都会有女性的存在,在《跑火车》中的女性因孩子无人照料惨死而悲痛欲绝;《低俗小说》中米娅吸毒过量导致晕厥;而《梦之安魂曲》中玛丽安也最终沦为毒贩的性玩具。玛丽安在这部电影中是一个完全的悲剧角色,如果说萨拉是被忽视的孤独女性,玛丽安更像是一个被贬斥的女性,在精神分析中提出了“作为影像的女性,会引起他所指的阉割情结的焦虑,而男性则从两种方式可以逃避这种阉割焦虑”。而该电影则体现了这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物恋对象来代替她,或者是把表现的人物转化为物恋对象,使她能够在自己的控制之内进而消除这种威胁感。从玛丽安从电影中出现,她即与哈瑞出现在统一画框作为前景,在延时拍摄中这两个人物始终处于画框的最前面,而不管其他角色如何變动,这两个人始终在前景拥抱在一起,两个角色有大量的身体接触,如胶似漆,两个人似乎是极其亲密的,玛丽安既作为了影片中哈瑞的凝视对象,也同样作为了电影观众的凝视对象,具有双重凝视效果,而得到了观众对于哈瑞这个角色的认同感;第二种方式是对有罪的对象进行贬值,惩罚或者拯救来实现重新平衡这种原始的阉割创伤,比如在一系列黑色电影中触犯法律的美艳女郎最终被绳之以法,而在《梦之安魂曲》中,在他们走投无路之时哈瑞建议玛丽安去向她的追求者阿诺德要钱,而这一举动可能意味着玛丽安要付出更多的代价,而哈瑞却运用他的男性权利强迫玛丽安去做这件牺牲自己的事情。
在这个片段中,玛丽安坐在一边接受着来自哈瑞的反问“我有几个月没见过他了”,而哈瑞站在她的面前进行施压,“那又如何,他不是经常给你打电话吗?”玛丽安在这个片段中被哈瑞潜移默化地赋予了不忠的标签,尽管玛丽安从未背叛过哈瑞,但是哈瑞的盘问让她感觉自己有错,并且下定决心为哈瑞付出,为他重整旗鼓提供资金。在这里,男性处在了合法的一边,而女性处在了不合法的一边,而玛丽安在沉思中决定做哈瑞的牺牲者和救赎者,“重要的是怎么从他那里弄到钱。”玛丽安在这个时刻已经放弃了自己作为哈瑞女朋友的道德规范,而只想按照哈瑞所说的方法去解决当前的问题,似乎她就是唯一的拯救者,而男性无意识地用贬斥女性的方式逃避了弗洛伊德所提及的原始的阉割焦虑,哈瑞逃避了自己的责任并且将后果都施加在玛丽安身上,但是从电影中可以看出哈瑞对玛丽安并不是没有感情的,哈瑞在胳膊的伤口发作时仍然不忘给玛丽安打电话,而在睡梦中看到红裙子的女性也是潜意识中认为是玛丽安,在截肢手术醒来之后也是喊的玛丽安的名字,而这种逃避原始阉割焦虑的潜意识也解释了哈瑞这种又爱又贬的矛盾感情。最终玛丽安在一次次放逐自己之后也完全放弃了自己的身体,逐渐成了毒品的奴隶,最终变成了毒枭的性玩物。
四、希望和绝望
而从《梦之安魂曲》的情节点设置来看,影片紧紧围绕着人性冲动的本能来完成了剧情的冲突和升华,每个人物都有其渴望得到的东西,萨拉想得到的是通过吃减肥药获得苗条的身材,哈瑞和塔伦想得到的是通过毒品赚钱,玛丽安想得到的是毒品本身,而每个人都是依赖毒品去获得自己想要的,以达到内心的富足或者生活上的自给,而每个人与毒品博弈最终都以惨淡的结果收场:萨拉因为减肥药使用过度住进了精神病医院,哈瑞因为注射感染切除了自己的胳膊,泰伦为了救哈瑞锒铛入狱,玛丽安为了毒品放逐自己成了毒枭的性玩具,每个人都死在了自己的凛冬,再无春天可言。
整部电影基本是压抑黑暗的,而这种压抑更是由于每个希望和温情都伴随着更加厚重的绝望,比如哈瑞为了保释泰伦拿出了他们的大部分积蓄,导致他们费尽心思赚的钱一扫而光,哈瑞对玛丽安的关心和恳求却只是想让玛丽安出卖身体向她的追求者要钱,哈瑞为妈妈买了电视机并且奉劝妈妈不要再吃减肥药,而最终电视机却让母亲沉迷减肥药而精神失常,泰伦为了救哈瑞只能冒着入狱的风险送他去医院,而自己也被抓住入狱,每个温情都是伴随着更加的黑暗而来的,正是这样的剧情设置让整部电影在看到一点希望的时候就被更加厚重的绝望取代,影片中穿插的小时候纯粹的温情很快就被现实所代替,所有的希望只能停留在幻想中,只能成为一个不会实现的梦境,没有希望的希望才是更深厚的绝望。
五、结语
除此之外,《梦之安魂曲》具有非常独特的拍摄手法,剧中的音效更是点睛之笔,光怪陆离的快速剪辑让人眼花缭乱的同时更加生动的刻画出一个噩梦般的世界,在影片的最后几个镜头,萨拉在幻想中的灯光下满足地躺在病床上,玛丽安怀抱着自己出卖身体赚来的钱蜷缩在沙发上,哈瑞胳膊被截肢痛苦地哭泣,泰伦在监狱的床上,幻想着母亲的温情蜷缩着入睡,蜷缩着身子是胎儿在母体中最为安全的状态,而四个人最终都只能活在个体为自身编织的梦中。在梦中找到精神寄托,呼应了“梦”的主题,吸毒就是一场噩梦,沉迷其中则无法醒来,整部电影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禁毒电影,而其中的一些裸露镜头也加深了这个毒品的噩梦的惊悚感和绝望感,这也许是导演想表达的一部分,而影片中處理人物发展的节奏以及矛盾转折也是非常值得商讨的。
参考文献:
[1]Mulvey,L. Visual Pleasure aud Narrative Cinema[J].Screen,1975,16(3):6-18.
[2]李恒基,杨远婴.外国电影理论文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3](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Ⅱ[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4]戴锦华.电影理论与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5]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第二卷)[M].宋广文译.长春:长春出版社,1998: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