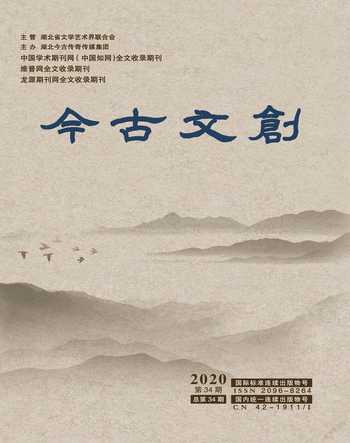论乡土文学中人性美的缺失
【摘要】 对于人性美丑的审视历来是乡土小说中不可或缺的表达,本文试图借助一部特别的乡土小说《呼兰河传》分别从人性的失常、无常、庸常三个层面论证人性美的缺失性表达,并试图站在文本之外呼吁关注乡土小说本身的价值。创作者笔尖深入乡土,在人性美丑的抵牾中给后代研究者空间,在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带后人走进那场遥远的文学盛宴。
【关键词】 人性美的缺失;人性失常;人性庸常;人性无常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34-0004-02
克利福德·格尔兹在《文化的解释》中表达这样一种观点:人类本能地掌握着世界乃至主宰着世界,但是当一些未知的事件或现象超出了他们所能理解的范围,人类便感到威胁,以致造成经验世界的混乱,从而杜撰出“鬼”这一概念。[1]经验世界的混乱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类的迷信愚昧,麻木和冷漠,而这滋生了乡土农村封建性的壮大和发展。因此,对于人性美的缺失性表达成为历来乡土小说不可或缺的一种表达,间或掺杂人道主义的关怀,从而将愚昧搬上了荧幕,以乡土封建陋习为载体,在以启蒙为宗旨中剖析国民的劣根性。
萧红的《呼兰河传》无疑是对20年代乡土小说的继承与深化,同样一群可恶又可怜的人诞生于她的笔尖:冰天雪地里老头子的一趔趄换来的不再是常态下的搀扶而是乘人之危(偷馒头)的慌乱奔逃;在风雨的洗礼中,村里出现了大自然带来的裂痕——泥坑子,车夫经过时车胎陷入其中,以及无数次在裂缝里上演着的灾祸:埋葬过猪,闷死过狗,淹死过猫,甚至偶尔一些瘸瞎疯傻之人也难免其祸。呼兰河里的人做惯了思想上的矮子,遑论行动上的巨人?灾难未降临自身之前,人人皆是“看客”,这些人爱极了热闹,爱看……这都是发生在呼兰河的故事。
一、透过小团圆媳妇解读人性的失常
萧红的《呼兰河传》中极多的是琐屑的故事拼凑,零碎的故事于读者而言更多的是脑海中的一闪而过,继而烟消云散。世人都纠结于该书是否具有自传性,洞察个人的隐晦仿佛比作家本身所有传达的深思更让人着迷。茅盾评此书: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小说,而在于它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2]如果对于作品体裁的界定算不上“诱人”的成分,那贯穿作品其间的人性延伸算得上是“诱人”的因子吧。
小团圆媳妇的塑造无疑是这本书的亮点所在,从她的“亮相”直至“死亡”读者如在一百摄氏度的蒸笼里渐渐体会冰凉的丝袜一点点烂透,最后全身冰凉。
小团圆媳妇无名无姓,已如她的婆婆——胡家大儿媳妇。婆婆听从道人之说将小团圆媳妇全身不挂在众目睽睽之下抛入滚水之中生烫,直至活活烫死。周围的人群开始张罗着救她,可是在她被丢入沸水之中,无一人来制止这场“人澡宴”。看着她一动不动,周围的人群渐渐散去……
萧红除却将小团圆媳妇之死鲜血淋淋展现于读者面前,能让读者痛入骨髓的还在于将鲁迅缔造的“看客”形象搬入其间,不同于鲁迅凌厉的目光和俯瞰式的蔑视,作者不自觉地化作看客的参与者,使得她的笔触多了些许温凉和矛盾,她谴责小团圆媳妇婆婆丧尽天良,她又将其心酸不易紧缀其后,让读者跟着一并纠结,该恨还是该爱?在爱恨的权衡中质疑人的复杂性,小团圆媳妇之死究竟怪谁,是萧红提出的一个时代性疑题。萧红的乡土小说一定程度上仍是对于前期乡土小说“是什么”“为什么”的延续乃深化,匮离了“怎么办”的寻找出路式探索也许会成为后世所诟病的点,可是有时候发现问题或许本身比解决问题要更难上加难,正是前一辈们对于乡土人性美缺失发出的叩问使得后人为探索出路而苦苦追寻,这本身就是一种贡献。
乡土小说作为特殊的文学题材,往往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新时期以来,乡土小说仍然以旺盛的生命力存在于当代文坛,可贵的是这些作家们在深情与感恩中依然能正视故乡的污秽和落后:刘震云在眷念之外的对于故乡人性弱点的不规避;贾平凹在商州系列外的废都西安;莫言、余华等人故土书写中的两道风景线。它们依然肩负着揭露陋习变革农村的使命,以农村社会之小口洞见整个社会之大洞,从而改良整个社会现状的雄心。
二、透过有二伯透析人性的庸常
在小团圆媳妇的死去中看客们终于等到了故事的大结局,无趣的生活需要发掘新的东西来增添调味剂,嗜偷成性的“有二伯”渐渐地由故事的配角变为主角,甚至贴上了颇负活力的“小偷”标签,人有所失皆是他手,而“我”作为真相之帝再度成为荧幕后的见证者,“我”深知有二伯虽有偷手的习惯,但也有被冤枉的时候。随之而来的是看客心中燃起的烈焰雄光:有人说他上吊,有人说他投井,,有二伯依旧活得好好的,人们逐渐对他失去了兴趣。
如果说,小团圆媳妇之死让人在看客们的身上看到了人性的残忍进而引发深思。那么,有二伯身上体现的是大众的主观猜忌性所引发的一种罪恶。因为有二伯身上存在这种前车之鉴,人们学会了嫁祸,在嫁祸之中享受着做坏事的快感,却又不必承担做恶事所要承担的恶果,也许有二伯的存在使得更多的人敢于无所忌惮的去做偷手之事。就像《杀生》这部电影所演绎的一样,因为牛结实做过坏事,所以只要有坏事发生就和牛结实有关。也许生活一直需要这样的人来保障他们的安全。
二伯在众口铄金的指责中,他也有口难辩吧。这就是人性的庸常,人人口说眼见为实,人人口说眼未见之事,有二伯上吊了,有二伯投井了,有二伯……人们在流言蜚语中传递着美好的愿望来满足看客之心。
早在千年前孟子主张“知人论世”,大意即是指了解一部作品不单单只看其内容,而是能够深入到作者创作的背景和年代中去方可实现对作品的理解与升华。《呼兰河传》是萧红写于40年代蛰居于香港期间,无论是身体和精神及情感状态都不尽如人意,现实的无奈无法撑起心中的理想——投身到救助农工劳苦大众的群中,内心的苦闷和无奈使得萧红对于生命生发妥协,就像那群生活在呼兰河里的故乡人终会在庸常中碌碌无为,她在写看客,也在写自己。
三、透过歪嘴子解析人性的无常
无聊的看客又开始寻求新的目标——歪嘴子,在信誓旦旦的讨声中,看客们终于在沉浸于自己是预言家的喜悦中,歪嘴子媳妇生下二儿子撒手人寰。
人们将视线继续转向歪嘴子身上来,深信不疑其子不能久活,只是这次没能如愿,眼看其越长越大,人群渐散,开始寻求新的被看目标……
之所以将这个层面的人性定义为“无常”是因为人性存在着太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常常感慨“命运无常”,却少有人慨叹“人性无常”,但是当提出了这个概念世人却又深有同感,人性的恶之深度远远会超出想象,像是每天发生在身边的各种非常态的事件一样,先是震撼,然后憤懑,但又在平静的生活中期待着新的故事上演。萧红的《呼兰河传》让人关注着人性之恶究竟会走向何方,但渲染人性之恶并非是萧红的目的归宿,而是抑恶扬善,通过对人性之恶的表现呼吁人们向“善”,从而深发启蒙劝善的作用,这也正是历代乡土小说的使命所在。
茅盾先生指出:“《呼兰河传》中作者思想的弱点除了因为愚昧保守而自食其果,这些人物的生活原也悠然自得其乐,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而这两重的铁枷,在呼兰河人民生活的比重上,该也不会轻于他们自身的愚昧保守罢?”[3]在弥漫着硝烟的年代萧红能够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写故土儿女,又何尝不是对故乡圣土里这篇精神家园的坚守,她们愚昧保守却自得其乐,她们消极懒散却祥和安逸。可贵的是,萧红在枪林弹雨中留下了别具一格的风俗画,在个人情感的偏赖中有自己的私心——未被战争玷污的故土,同时也站在人性的制高点上对于故乡人的审视,也完成了对其知识分子写作立场的坚守。
孙郁老师说,“生活固然美好,但草木的性灵几被水泥覆盖,不及乡土那么带有野趣了。未来的趋势乡土有可能进一步减少,在更多的人过上便利富足的城市生活后,恐怕关于乡土的文字就稀罕了。”[4]在城市文明崛起乃至覆盖全球的趋势下,像萧红这类作家及穿梭在作品中的或残暴或温良的乡土记忆亦将去渐远,也许乡村文明终有一天成为城市文明中的一粒砂。那个时候乡土记忆或许真的是遥远的神话传说了吧!那么在人性美丑的嬗变中,也许更应该怀以宽容之心去领悟作品,解读作者。
参考文献:
[1](美)克里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2][3]茅盾.呼兰河传序[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6.
[4]孙郁.关于乡土的那些文字[J].前线,2013.
作者简介:
闫艳红,女,汉族,陕西榆林人,南昌大学文学院2019级硕士在读,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