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你时雨停(二)
白玉京在马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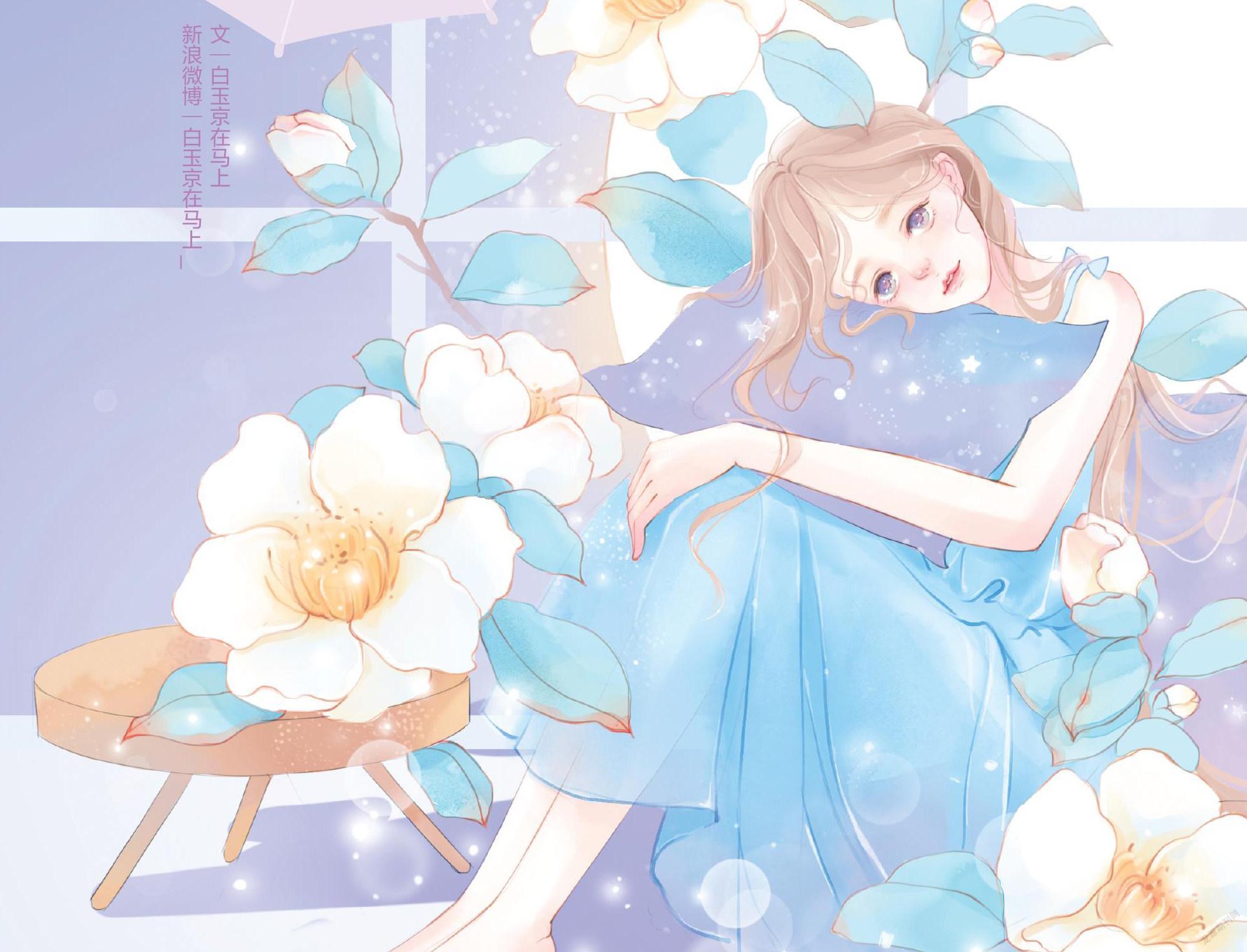
前期回顾:崔时雨称重结束,被张诚然邀请到餐厅吃饭,一听说聂廷昀也在,她忍不住答应了这场邀约。聂廷昀问她,他们之前是不是见过,崔时雨予以否认,并提前退场离开。
冰凉的水扑在脸上,随着抬头面向镜子的动作,水珠滑到耳后、颈间,浸湿了领口。
她双手撑在冰凉的盥洗台上,一下一下地努力呼吸。
轰鸣声从左耳穿过右耳,声音渐渐微弱,世界终于安静下来。
她再三权衡,还是抵不住看他一眼的诱惑,莽撞地闯到他跟前来了。
这个错误,不知该怎么挽回。
她掀起T恤下摆擦了擦脸。
盥洗间在曲折长廊最尽头,她方向感极差,走出来之后,从大堂到各个餐厅、店面,绕来绕去怎么都找不到正门,甚至不知不觉下到了负一层。
人流稀疏,各个店铺装修显得尤为高冷,她踌躇半晌,站在原地张望了片刻,靠近一个店面,要开口问路。
“请问……”
“两位,谢谢。”
一个沉冷低哑的声音打斷了她的话。
崔时雨脑子“嗡”的一声,她缓缓转过头,看见聂廷昀就站在她旁边,活生生的。
侍者满脸堆笑:“好的,二位里面请。”
见崔时雨还傻站着,聂廷昀歪了歪头,示意:还不进去?
她拒绝不了聂廷昀的任何要求。
崔时雨迈步跟上去,在他对面落座。
侍者拿来菜单,她瞥见“水蟹粥”几个字,眼神微微一滞,咬住下唇。
“招呼也不打就提前离席,原来是自己偷偷下来找东西吃。”聂廷昀看着菜单,眼皮也没抬,揶揄她,“你倒是会找地方,看在张诚然的面子上,总得请你吃饱,不然他白张罗这一顿饭。”
他说这些话时,语气如常,似乎没有刚刚那么讨厌她。
可是……
见崔时雨低垂眼睫,也不吭声,他又问:“聚餐的时候吃不下饭吗?吃东西和咽药一样。”
他一直看着我吃东西?
崔时雨终于觉得哪里不对劲,皱了一下眉,抬眸看向聂廷昀。
聂廷昀放下菜单,有点儿不耐烦她的沉默,只好问道:“要说什么?”
崔时雨定了定心神,才说:“你有话要问我?”
聂廷昀没有答,朝侍者指点菜品,合上菜单。
热茶呈上来,他先递到崔时雨手里。
“你不用这样防着我。”聂廷昀似笑非笑地看她,“我不会动张诚然的心头好,只想问你一句话。”
崔时雨的脸色有一刹那的惨白,又很快恢复如常,她点了点头,说:“……你问。”
聂廷昀静默了两秒,缓缓开口:“两年前,你有没有去过F大承办的大学生柔道冠军杯赛场?”
水蟹粥端上来,雪白的粥里露出金黄的蟹壳,姜丝错落散在周围。
他将香气四溢的粥推到崔时雨的跟前,看到她拿了勺子,却迟迟不动。
聂廷昀也不知自己在等待一个怎样的答案。
是她或不是她,重要吗?
可他莫名觉得,不只是两年前的那个时刻,而是这些年来,一直有什么隐隐的线索,串联成一个模糊的人影,他摸不着,也抓不住。
两年前,柔道赛场上,他竭尽全力扛到了最后一秒,终于迎来胜利。他看见对手绝望而不可置信的眼神,裁判宣布他胜利的同时,全场的欢呼声和尖叫声几乎把他淹没。
可随即,视线里一片朦胧。
耳际有人在说话,鼻息有消毒水的味道,他努力掀开一点儿眼皮,很快又重重地合上。
教练的声音近了,远了,然后消失了。
不知过了多久,他艰难地睁开眼睛,分不清眼前的一切究竟是梦是真。
医务室的病床边坐着一个陌生的女孩,正专心致志地为他按摩手臂,帮他缓解肌肉拉伤的疼痛。
是护士?不对,她穿着柔道服,系着黄色腰带,是选手。可她为什么会来给他按摩?
他眯着眼睛,纤长浓密的眼睫阻隔住部分视线,因而她在他眼中是如此朦胧而失真。
然后,她仿佛意识到了什么,猛地抬眼,与他视线相撞。
“我好像醉了。”他哑声喃喃着。
她松了手站起身,连退两步,似乎是要逃走,迟疑地看了他半晌,又仿佛知道他现在意识不清,终于开口回答:“你现在不清醒。”
“像是醉了。”他执意如此定义此刻的知觉,”可是感觉不坏。”
“没有人喜欢醉的。”女孩似乎是觉得他在说胡话,放下心来,坐回去继续为他按摩手臂,漫不经心地自语,“人们只是喜欢逃避。”
他想开口辩驳,沉重的眼皮再次垂落,视线模糊之际,仿佛看到了她离开时柔道服背后的名字。
醒来后,他谢谢教练帮他按摩手臂,教练见鬼一样看着他:“我忙着管下个比赛的孩子,哪有时间顾你?校医没照顾你吗?”
聂廷昀蓦然噤声,有一瞬的怔忡。
女孩的轮廓,柔道服背后的名字依稀浮现。
他恍惚觉得那不是他第一次见到她。
而此刻,他终于等来了答案。
崔时雨舀起一勺水蟹粥,低垂视线,摇了摇头,语气平稳,毫无破绽。
“没有。”停了停,她补充道,“两年前,我没有见过你。”
水蟹粥蒸腾出热气,熏红了她的脸颊。
聂廷昀没有再说什么,几不可见地点头,像是在说“知道了”。
她捏着勺柄,用力到指节压弯,很久才放松力道。
聂廷昀垂下眼睛,不再看她,淡淡道:“喝粥吧。”
她低下头,一声不吭地舀起粥。粥喝了大半,她无法从余光判断他的喜怒,终于忍不住抬眼,视线交织,聂廷昀正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对方的瞳色在流光的映照下,令她有种被凝睇的错觉。
崔时雨感觉到自己的手指在抖,陶瓷的餐具撞击出轻微声响。
他为什么看着我?
下一刻,他站起来,朝她倾身,缩短了这一张餐桌阻隔的距离。
她不由得屏住呼吸。
他的目光仔细地扫视过她的面容,终于开口:“你过敏了?”
她下意识地抬手,要触碰发痒的脖颈,却被抓住手腕。
她受惊般看着他,那眼神好像他是什么恐怖分子,让他只能松开手。
他的指腹擦过她的手腕处的皮肤,这是一段非常柔软的,未经训练磨砺的皮肤。
他有一瞬走神,又很快放冷了口气,声音低低地责问:“你不知道自己的忌口吗?”
她张了张口,似乎要解释,最终却变作哑巴,什么都说不出。
气氛有些窘迫,聂廷昀见惯别有用心的女孩叽叽喳喳,头一次遇到这么一个闷葫芦,还仿佛避他犹恐不及,只能无奈地说道:“我叫张诚然回来送你去医院?”
“不用!”崔时雨回答得很快。
聂廷昀挑了挑眉,那表情似乎是在问:那你现在要怎么样?
“我……去一下洗手間。”她紧紧抿着唇,强忍着不适。
他无法理解:“去了就不过敏了?”
“我需要吐一下。”
他终于确定,无论是等她给答案,还是等她做决定,都是个非常愚蠢的想法。
聂廷昀低声说:“等我一下。”
他起身,签了单回来,见她果然乖乖地坐在原处等待,心头不知怎的一软。他拉住她的手腕,没给她拒绝的时机和余地,在她反应过来之前,已经带着她往外走了。
一路进电梯,上到二十层,他刷卡进门。
崔时雨胃里翻腾得厉害,连开口询问的力气都没有,聂廷昀把人推进套房的盥洗室。
崔时雨愣愣地看着门在眼前关上,随后,听到外间传来脚步声,和房门关上的声响。
这是……怕她尴尬吗?
聂廷昀正在电梯里等着数字依次亮起。
他觉得自己贸然将小丫头带到自己领地的举动有点儿莫名其妙。
但很快,他又说服了自己——算了,看在张诚然的面子上。
“您好,聂先生,请问有什么需要吗?”前台小姐见他直接下来询问,稍有讶异。
“我的……朋友,螃蟹过敏。”
聂廷昀想了想,要了一张便笺,写下呕吐、红疹的症状,又写下房间号交给前台。
“好的,稍后会将过敏药送到您的房间。请问需要红糖水或温水吗?”
聂廷昀点点头,看了看表,返身上楼。
他推门进房间,盥洗室里隐约传来讲电话的声音。
“封寝了?好……谢谢。”
她的话语简洁又干脆,同和他说话时的唯唯诺诺判若两人。
聂廷昀站在门口,不由得挑眉。
门内,崔时雨坐在冰凉的地面上,挂断电话。
折腾她半天的水蟹粥终于被她吐出去了,她打开空气循环,等待味道散去。
窘迫至死恐怕和现在这个局面差不多,她开始反思自己怎么走到了这个地步。
她低垂着头,有些眩晕地想,这一切好像不知不觉脱轨了。
她不该参加这次聚餐,不该同他吃这顿“加时饭”。
柔道比赛里,加时赛给人垂死之际的一线生机,也给人筋疲力尽后的绝望。
她无法预料结局会是哪个,所以纵容了自己的贪欲。
她有原罪。
门外传来低声询问,打断了她的思路。
“你还好?”
“我没事。”她的声音听起来还很冷静,紧接着咬住下唇,轻声补充道,“谢谢。”
聂廷昀转身回到客厅,打开了电视,调大声响。
几分钟后,客房服务员送来过敏药和温水,他在门边道谢,一转身,却见崔时雨已经走出来了。她额上还有微微的汗,面如白纸。
聂廷昀用下巴示意她坐下,看着她吃完药,说道:“你家在本地?一会儿我送你回去。”
崔时雨一言不发,抱着双膝蜷缩在沙发上,愣愣地看他。
聂廷昀被看得蹙起了眉。
她的眼神专注,眼皮却疲倦地垂下来,一张巴掌脸,因数日以来的减重,呈现出略微脱水的症状,眼眶有些发暗,看起来像是随时要晕倒。
他看得出她很不舒服,手倏然抬起,又克制着落下来。
电视里开始响起十一点半的重播新闻的声音,沙沙的声响里,他和她无言对视。
他疑心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看哪里,紧接着,他猛地探出手,托住她沉落到那一侧的头。
他弯腰,维持着一个辛苦的姿势,细细的发丝掠过他手腕。
他忽地想起古人说的一个词:螓首蛾眉。
聂廷昀骨子里有着家教浸淫的绅士风度,却决不是个温柔的人。
唯独此时,他不知怎的定格了时间,不敢动作,只怕将她惊醒。
他想了想,顺着她歪头的方向,小心地将手慢慢放下来,令她侧躺在沙发上,再缓慢地将手抽离。
崔时雨仍旧闭着双眼。
他没发现自己脊背上出了细细的一层汗,只是松了口气,拿了薄被盖在她身上,留下便笺,转身走了。
关门声响起后,崔时雨缓缓睁开眼睛。
其实,在打了个瞌睡脑袋撞进他掌心的时候,她就已经醒了。
她感觉此时颊边、发间似乎还残余他的温度和气味。
离得太近了,她还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打开安全区域,让他踏入。
她蜷缩在沙发里,探手拿起矮几上的便笺,上面写着:“客房早餐预约在明早七点钟,没有任何螃蟹或海鲜成分,可放心食用。”落款是“聂廷昀”。
一手极漂亮的行楷字,明显是临过帖子的,有钟繇风骨。
便笺翻过来,背面是他的手机号码。
他对谁都这样体贴吗?还是……只因为他将她当作了张诚然的“心头好”?
隔天回到学校,她已经错过了晨间训练。冯媛西想要问责,见她小脸白得和纸一样,又拎着药,不由分说批准她去休息。她拗不过教练,只好回到寝室。
走上空寂的楼梯,她感觉到胃仍在隐隐作痛。午后的阳光透过天窗照落下来,她的影子曲折地落在阶级上,一折,一折,再一折。
寝室里四下无人,她拿出柜子里的记事本,记下昨天的日期。
“我又见到他了。”她写下这么一句话。
想了想,又划掉,她接着写下一句:“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我,我有些害怕。”
她费尽心思见过他一千次,一万次,却不指望他能记得其中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
她只想成为他的陌生人,或者是……有过一面之缘的陌生人。
合上本子,她伏在桌前,做了一个深呼吸,闭上眼睛。
她的鬓发间,仿佛还有他掌心的温度。
离柔道联赛还有两天时间,两所学校的柔道部都在加紧训练。
崔时雨将聂廷昀的便笺夹在笔记本里,拼命克制住另一样贪欲——联络他。
理智虽如此,但她强大的潜意识早已将那一串号码倒背如流。
这天训练结束,堂姐崔念真说来接她吃饭,她才想起今天是她的生日。每年的生日,她例行公事般要和父母见面。在他们貌合神离的时候如此,现在各奔东西了,仍旧如此。
训练结束,偌大的场馆又只剩她一个人。收拾完道具,她走出去,外面的天色已经有些暗了。堂姐崔念真已经在车里等了她很久,终于耐心耗尽,掏出手机来给她打电话。
打了一次,两次,没人接,锲而不舍地拨了第三通,崔时雨才慢吞吞地出现在她的视线里。
她降下车窗催促:“快点儿!”
崔时雨开门上车。
崔念真瞥她一眼,忍不住说:“一股汗味儿。”
崔时雨不以为意:“没回寝室洗澡,怕你等不及。”
“不是我等不及,我的姑奶奶!”堂姐发动车子,一脸焦急,”你知道为了给你庆个生,你爹媽好不容易才聚到一起,订了包厢等你半个钟头了。”
崔时雨无意识地笑了一下,脱口道:“给我庆生?”是为了让他们得到心理安慰吧?
堂姐偏头看她一眼,刚张开嘴,可是瞧见她面无表情的模样,又忽然什么都说不出来了。作为崔时雨大半个人生的参与者、旁观者,连崔念真都觉得,堂妹的爹妈在做家长这方面,的确存在很重大的失误,或者说是偏差。
包厢里,这对离异夫妇,一年到头只在女儿生日这天才难得见上一面,此时正有点儿气氛诡异地聊着自己的近况。
“你在杭市的那个展,我听朋友说了,评价很高啊。”
“哪里哪里。”
“下次的画展一定邀请我,我认识一个导演,对花鸟鱼虫的国画非常痴迷。”
崔时雨的妈妈尹楠一头短发,非常干练,凭借媒体人身份混迹半个娱乐圈,能言善辩,长袖善舞。她父亲崔崇年言谈儒雅,只云淡风轻一笑。
聊着聊着,不免尴尬冷场。
这时,崔念真操着一口播音腔推门而入:“当当当当!寿星驾到!”
崔时雨迷迷糊糊地被推到主位上,一系列毫无灵魂的庆生步骤开始进行。她无比顺从地照着指示吹蜡烛,闭眼睛,切蛋糕,回应生日快乐的祝福,却唯独没有偏头和坐在左右两边的父母对视一眼。
尹楠连喝了几杯白酒,后来就有点儿上头,扯着崔时雨的手絮絮叨叨道歉:“妈妈知道,这些年你一直怨我,但是妈妈那时候不成熟,哪能想到那么多呀?有句话怎么说的,都是第一次做父母……你看今天这生日,你连个笑脸也没有……”
崔时雨心道,她到底想说什么呢?
关于家,关于父母,关于羁绊与眷恋——这些字眼和情绪都太奢侈了。
她阻断谈话:“妈妈,我从来没有怪过你,我也没有为你们伤心过,真的。”
她父母同时僵住了,用一种无法形容的眼神看着她。片刻后,尹楠起身离席:“我去一下卫生间。”
紧接着,崔崇年走到她面前,欲言又止,最后只说:“囡囡,没事的,继续吃饭吧。”
庆生到最后,虽没有其乐融融的气氛,却也还岁月静好。
坐到了堂姐车上,崔时雨才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问道:“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堂姐没吭声。
“我看到妈妈哭了。”她回忆。
堂姐终于忍不住,“呵”了一声:“搁我我也得哭。我这和亲生闺女掏心掏肺道着歉呢,没等来一句安慰,亲闺女反而说根本没为这些事儿伤心过,能不难受吗?”
崔时雨有些愣怔,道:“那她希望我说什么?”
“她不是希望你说什么!”堂姐郁闷到快要爆炸了,“她根本不需要你说什么!她需要你像亲闺女那样抱着她,跟她一起哭!你懂吗,崔时雨?”
崔念真吼完这么一句,车里陷入一片死寂。
车子猛地停下来,险些和前头的车辆追尾,崔时雨抓住了车顶的把手,在震荡过后,无意识地放下手来,按住胸口。
她忽然觉得无法呼吸。
堂姐又问:“像今天这种奇葩场面,你都不会觉得伤心吗?”
“应该是……会伤心吧。”她也不确定。
崔念真叹了一口气:“你当时到底在想什么?”
崔时雨沉默半晌,低声说:“我什么都没想。”
她能想什么?即便她想,又真的有用吗?
她习惯了顺其自然,在别人看来更像一种对人和事的淡漠。
她恍惚想起,幼年时,第一次被父母寄养在朋友家,她巴巴地站在门口,扯住母亲的裤腿不要他们离开,最终也只得忍着几乎要被掰断手指的痛楚接受突如其来的分离。
总归一切都是徒劳。
“堂姐。”崔时雨没头没脑地说,“我好像一个假的人。”
一个和喜怒哀乐隔着厚厚一层……墙壁、玻璃或是雾气的假人。
“时雨,够了。”堂姐突然红了眼眶,伸手揉了揉她的头发,“你过两天还要比赛,先不说这些了,等你打完比赛,好吗?”
崔时雨看着前方,视线里是长长的车队,尾灯的光线映进眼底,带着奇异的色彩。
比赛——是啊,她的比赛。
她点了点头,不自觉地放松了绷紧的神经,连眼神也稍稍带了温度。
希望一切能够如她所愿,乘胜前行。
周末,高校柔道联赛在海市体育馆开幕。崔时雨坐在备赛区,冯媛西握着她的手,一直不停地和她说战术。可她总是忍不住要走神。
余光处,体育馆的另一头,聂廷昀坐在教练旁边,依次和女将们击掌。
他穿一身熨帖的休闲装,白色T恤,黑色长裤,击完掌,两手便撑在分开的双膝上,似乎在静静地听着教练说什么。
崔时雨忽然觉一阵恍惚。
没有人知道,他的每一场比赛她都不曾缺席,那些流汗甚至流血的比赛里,她跟着哭过,笑过。
她在他永不会知晓的一隅,将曾如顽石的心脏化成波澜频起的湖水,却没奢望过他会回眸身一顾。
而这一次,是他坐在观众席上。
崔时雨无法克制自己的紧张,心跳声沿着血脉、骨骼,回荡在耳中,她的视线忽然有点儿模糊起来,呼吸憋在喉头,要很艰难才能顺利完成一次吐息。
她闭了一下眼睛,再次睁开时,已经被人用力推向赛场。
眼底是明黄色的垫子,她怔了几秒,才抬起头来,看到对手气势汹汹地来到面前。
是丁柔。
巨大的屏幕上,电子钟开始倒计时。
“崔时雨,他们都说你以技术华丽取胜。”丁柔低低道,“领教了。”
她怔了一下,哨声已经吹响,丁柔挪动步伐,朝她抓来。
崔时雨扬起手,对方一抓落空,她退了半步,心狂跳起来,意识到自己乱了章法。
状态不对。
盘桓片刻后,崔时雨抓住时机,死死扯住了丁柔的柔道服领口。
场外响起教练的声音:“穩住!时雨!”
湛蓝的布料攥在掌心,一个不留神,她也被丁柔紧紧抓住,两个人俯下身子,开始手劲的较量。
丁柔被甩了个踉跄,这零点几秒间,未及站稳,大腿已经被崔时雨趁机勾住,猛地向上翻去,随着全场惊呼,丁柔在大力翻转下拽着崔时雨的袖口猛地跃起旋身!
冯媛西庆祝胜利的“一本胜”未及出口,眼前的场景却令所有人大惊失色。
丁柔竟以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稳稳站住了,没有被扑倒在地!
教练吹响哨声,示意两人松手,秒数暂停。
场边,聂廷昀始终面无表情地注视着场上的战况。
他的视线短暂地停留在崔时雨沮丧的面容上,见丁柔朝他望来,带着求助的表情,聂廷昀做了个手势,示意她主动进攻。
丁柔安下心来,点了点头。
两人重新站到场中,裁判“开始”才出口,丁柔就攻势迅猛地跳过来扯住了她的领口。崔时雨偏了偏身子,没能避开。
对方的手劲远胜过她,崔时雨用尽全力猛地摆脱对方的拉扯,反手去拽丁柔的衣襟,却被她抬手挡住。下一刻,丁柔双手重新扯住她,俯身进入她身前空位,猛地将她顶在背上,就要甩出一个背负投!
天旋地转间,崔时雨的头已经重重地砸落在地,后颈剧烈弯折的痛觉让她再也无法坚持住这样一个类似于后折腰的动作,在身体放弃之前,理智却硬生生地让她做出了与生理相悖的选择——她挺着脊背猛地转了身,脱力般双肘撑着跪倒在地面,避开了背部着地。
裁判吹响哨子,示意这次进攻无效,全场哗然。
刚刚两人的交手可谓险象环生。
丁柔方喊了暂停。此时,距比赛结束还有一分三十四秒。
崔时雨气喘吁吁地跪在地上,试图起身却失败了,周身绷紧后袭来的酸痛让她几乎脱了力。她用余光瞧见丁柔奔向指导教练,而聂廷昀站起身,低头给丁柔指导战术。
他在教她,如何打败我。
崔时雨心里涌起一股无以言说的难受来。
比赛再次开始,由于体力已经耗尽,崔时雨只能退守。
聂廷昀坐在场边,有些不忍看下去。
他知道这场对峙,一定会以崔时雨的失败告终——她已经没有力气再做下一次进攻了。
下一刻,全场掀起一阵惊呼。
“腕挫十字固!”
倒计时结束的三十秒里,丁柔与崔时雨摔倒在地,崔时雨猛地抬腿去锁对方的手臂,丁柔却比她更快,眨眼间,她的右臂已经被丁柔牢牢锁在双腿间,拼命扯向反方向。
那是撕裂般的剧痛。
她如同一条被网住的濒死的鱼,拼命挣扎,随着读秒结束,全场的欢呼声里,她瞥见丁柔猛地松开她跳了起来。
“丁柔,以腕挫十字固一本胜!”
崔时雨仰躺在地面,迟来的痛苦一瞬间席卷肩背,她以残余的理智判断:我脱臼了。然而灵魂仿佛离体,高高俯视着惨败的自己,任凭躯壳狼狈不堪地陈列在众人面前。
包括……聂廷昀面前。
丁柔和队友一一拥抱,瞧见聂廷昀起身走过来,高兴地迎上去:“聂老大!我赢了!”
聂廷昀没有看她,甚至没有说一句“恭喜”,他的表情是前所未有的平静。
擦身而过之际,她听到他不带语气的一句话:“她脱臼了。”
赛场上一片混乱,有工作人员上前观察崔时雨的情况,可是无法轻易将她扶起,只要一碰她的手臂,她就出现痉挛性的反应。
就在众人混乱地围在旁边时,有人分开人群,走过来。
冯媛西偏头瞧见来人,愣了一下。
他是对方柔道部部长——赫赫有名的聂廷昀。
体大的女将们纷纷屏住呼吸,只怕呼出一口气来,眼前的聂廷昀就跑了。
崔时雨在剧痛下闭上了眼睛,耳际是无尽的嗡鸣,然而此刻,穿凿过她苦痛的一个语声,如同救赎一般,让她双眼勉强睁开了一丝缝隙。
“我看看。”聂廷昀额发湿透,微微皱着眉,出现在她朦胧的视线里。
她撑不住合上了眼,感觉到有手臂绕过她的后背和腿弯,将她轻轻巧巧地抱起,避开了脱臼的肩臂,一步一步地移动起来。
他身体的温度透过T恤、柔道服传过来,几乎使她感到灼痛。
抱着他的人……是聂廷昀。
崔时雨耷拉着头坐在医用床上,只觉治疗的时间漫长而痛苦。
她的眼睛半闭着,似乎又能朦朦胧胧地瞥见坐在不远处正注视着她的男孩。
“复位做完了,缠上绷带起码要固定半个月,尽量不要训练了,不然影响恢复,还会造成习惯性脱位,那以后就真的没办法练柔道了。”
医生结束工作,让她稍微侧身躺一下,说道:“休息一会儿。”
冯媛西仔细地听着,一脸紧张地坐在床边。
“感觉怎么样,时雨?”
她艰难地牵动嘴角,露出一抹微笑,终于让冯媛西放了心。
外头有人叫她:“冯教练,下一场啦!”
冯媛西站起身要出去指导,又有些不放心,对聂廷昀嘱托再三,才出去。
崔时雨半躺在医用床上,紧张地等待时间过去。
她从没想过时间会变得这样漫长。空旷的房间里,他和她都没有开口说话。
她想,我该说些什么吗?
可他忽然开口:“我替小柔说声对不起。”
聂廷昀起身,缓步靠近,她几乎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香水味道,清冽如同山泉。
她没有抬头看他,却知道他坐在了床侧,自己伸手可及的地方。
“不是她的错。是我明知道这个固技危险,却没有及时放弃。”崔时雨冷静地说道。
聂廷昀看着她低垂的眉眼,心里轻笑一声。
好倔的小丫头。他活了二十余年,罕有向人表达歉意的时候,这声道歉,她居然还不领情。他蓦地伸出手,碰到她的手腕,崔时雨打了个激灵,猛地抬头看着他,想要动,却被牢牢握住了。
“别动,小心脱位。”
聂廷昀拿过她的手,避开了绷带的部分,在小臂、手腕处力道恰好地按摩。
她愣愣地看着他,冰冻的血液一刹那奔流起来,汩汩涌向四肢百骸。
失败的痛苦和满心不可言述的热望,也一并涌上心头。
她放任自己的视线凝在他脸上。
聂廷昀忽然问:“明知道危险,明知道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挣脱,为什么不放弃?”
被腕挫十字固制伏后,她只要轻击两下对手的身体抑或是地面,表示认输,就可以从桎梏中解脱出来,避免惨烈的受伤。
聂廷昀在她不回血的手臂上轻轻按压,暗暗惊奇,这样纤弱的手臂,是怎样使出那些需要爆发力的柔道技术的?而后,他听到女孩轻柔而微哑的声音。
她的声音似乎没有色彩,一切都是天然的,不加修饰的,纯粹的婉转和清丽。
那几乎不像一个运动选手的声音。
她说:“我害怕失败。”
“没有选手不害怕失败。”聂廷昀笑了一下。这并不值得冒着自伤的危险,做无谓的坚持。
“我好像很害怕在你面前失败。”
聂廷昀手上的动作微微停滞,抬眸与脸色苍白的女孩对视。心中所有困惑,所有不解,在此刻终于寻到答案。
他想问:我们果然是见过的,对吗?
可她已经接着说下去了:“我可能更害怕在你面前轻易失败。好像再坚持一下,哪怕受一点儿伤,也是对自己有了交代。”
他面对过太多的告白、追求,却在此刻,因她毫无意图的倾诉而沉默。
“我对你来说很特别?”聂廷昀微垂了眼睛,嘴唇微翘,“你喜欢我?”
他脱口一问,带着某种与生俱来、被人崇拜的倨傲,也像是带着一种揶揄。
可没料到,她竟给了他坦然的回答:“是啊。”
崔时雨轻轻弯起嘴角,笑意稍纵即逝,有种脆弱的美。
一字一句,以极为绵柔的力道化入他的脏腑。
“在看到你之前,我不知道人为什么会哭和笑,你为什么会拼尽全力只为了一场胜负。那年,我仰头瞧见你,你只是看了我一眼,我就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明明人的心一直是在跳的,却偏偏要说一个人看到另一个的时候,会心跳。那种跳法好像是不一样的。”
崔时雨语气如常,困惑地偏头思索,终于找到了最佳的形容:“好像是一个死了很久的人,突然活过来了。”
一刹那为一念,二十念为一瞬。
遇见他的那一瞬,她在无数念起念灭间通彻了灵魂。
一刹那的刻骨于是成为永恒——历经几载星月,依旧铭心刻骨。
聂廷昀目不转睛地凝视她清明而澄澈的眼睛,克制着心头巨大的震撼,始终没有开口说半个字。
他不记得了。
让眼前这个女孩突然活过来的那个瞬间,他竟毫无印象。
下期预告:
原来在三年前,崔时雨见过聂廷昀比赛胜利的那一刻,而后,因为聂廷昀,她也进入了人和高中学习柔道。她本来與他只是两条平行线,却终于忍不住在十八岁这年向他靠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