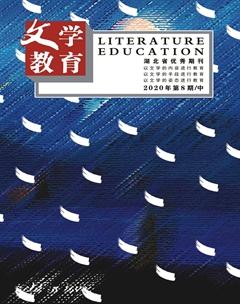回忆我的邪子嘎嘎

我的嘎嘎,也就我的外婆,是个邪子。在我们保康山区,都把疯子叫做邪子。我的嘎嘎应该属于那种间歇性的神经病患者。
嘎嘎姓陶,和嘎公住在离我家三四十里外的南漳板桥王家湾。小时候每次过年时,我总要随爹妈一起去给他们拜年,一开始坐在娃娃儿背笼里背着我,后来我长大了就独自一人去。正月十一是嘎嘎的生日。
去嘎嘎家的路特别难走,要翻竹杖坡、张道垭、樊家寨,再过摩天垭、万丈坡、大竹坪……每次去,都要给嘎嘎带些礼物,两斤白糖,三升黏米。嘎嘎那里是不产水稻的,所以每年去都会带点儿。有时也带十几斤黄豆,那是嘎嘎春上撒种用的。
我每次去嘎嘎家,翻过她家房子旁边的山洼,总听到一阵狗叫,有时还不止一只,我吓得连忙站在她屋旁边的田坎上,大声疾呼:嘎嘎——嘎嘎——给我拦狗子!这时,身材瘦小的嘎嘎,一颤一颤地赶过来,一边拖着竹条,一边吆喝训斥狗,又急急叫到,虎娃儿!你是个稀客呀!满满的喜悦之情,含在她满脸的褶皱中,让人心暖,也让人心疼。
一阵嘘寒问暖后,她从火房里冲杯糖茶,边走边用一根倒筷子在杯子里来回搅动。我刚接过杯子,她连忙又从屋里柜子中给我端一葫芦瓢的柿皮、柿饼、核桃、花生之类的零碎食果,偶尔也有一些别人送给她,她舍不得吃的橘子、糖果。
嘎嘎和嘎公的院子,孤零零地坐落在山坳里,黄土墙,屋顶盖着从附近撬来的薄石板,层层叠叠,因为年代久远,石板缝里生出了几根狗尾巴草,在风中摇曳。门前也是用石板铺成的场子,场子外面有几根高大的泡桐树和楸树,上面有几个喜鹊窝。喜鹊总会趁人不备之时,落下来偷啄屋檐下的玉米粒。嘎嘎家四周有许多柿子树、核桃树,她每年都会为我们这些外孙、外孙女准备一大堆好吃的。
嘎嘎家门前不远有个山包,山包上有座高大的古寨,一面临崖,寨墙上的垛口清晰可辨,我曾经一度坚信,它就是课本上长城的缩影。据母亲讲,嘎嘎的娘家就在寨子那边。寨子是以前附近村民为躲兵而修的寨子,具体的年代谁也说不清,厚厚的寨门需要几个人才能推开,寨子里有股泉水,可供躲难之时饮用。每次看到那座古寨,我都想登上山顶去看看,却不敢张嘴对嘎嘎说,一是上寨子的路不好走,再者,感觉对于她来说,寨子早已司空见惯了,一点不稀奇。
据说,嘎嘎一次意外生病,随后就得了间歇性的神经病。那时,嘎公是大队的粮食保管员,也是老裁缝师傅,长期不落屋。再加上,当时医疗技术也不发达,只能任其病情加重了。
我发现,一旦没有别人时,嘎嘎嘴里总是嘀嘀咕咕不停地念叨什么,全是些无中生有的事儿。要么,谁家某某又偷了她家的粮食;要么,是嘎公背着她,跟某某村妇好上了,等等。还好,嘎公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一般都不会跟她计较的,确实忍不住了也会大声训斥几句,嘎嘎或许能消停几分钟,不久又继续了,大家都知道她有病,也听之任之了。
记得小时候,嘎嘎有次来我家玩,深夜,爷爷在睡觉前,见家里的大黄狗趴在屋角落里,不肯出去,爷爷抡起拐杖,大声呵斥,赶狗出门。嘎嘎在隔壁屋,闻声披衣而出,硬说爷爷撵她走,并吵着找他评理。平时脾气火爆的爷爷,气得脸红脖子粗,但始终没有发一言。
有一年,嘎嘎来我家玩时恰逢落雪,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地上约摸三四寸深。嘎嘎却急着要回家,任凭爹妈怎么劝说都不听,最后,硬是杵着竹棍,深一脚浅一脚地要回家。父亲无奈,只好跟在后面,走了一段,路滑雪厚,确实不敢再走了,父亲忽生一计,以带路为由,带着嘎嘎在山林里兜兜转转,最后,天快黑时,又把嘎嘎带回到了我们家。
嘎嘎有五个女儿,虽然也曾先后招了二姨父和幺姨父,但两个上门女婿后来都因各种原因搬迁他乡,不能真正为她和嘎公养老。幸亏大姨嫁得不远,在嘎嘎生病时,和另几个姨经常轮流回来照顾。嘎嘎临走前,除幺姨外,另外几个都来给她送了终。
那年过年,我与弟骑摩托去给嘎嘎上坟。在大姨夫的带领下,我们走在曾经熟悉的小路上,路边的许多树木已经将这条羊肠小道遮得密密麻麻。偌大的埫田,长着齐腰深的杂草,埫中间那块葫芦状的深井也已干枯,田边的大桑树,只剩下深褐色的主干,像一只抓向天空的枯瘦的手。遥想当初,嘎嘎背着熟睡的姨们,在地里春播秋收,在深井里舀水背水,在桑树上采桑喂蚕,心中不由感慨万千。
我们穿过荆棘,来到嘎嘎的坟场前,一片枯黃的茅草,几乎掩盖了整个坟茔。一场噼里啪啦的大火之后,我们才靠近坟前,一块大姨夫亲手打凿的碑,立在坟前,这时我方知道,嘎嘎的真实姓名。
上坟完毕,我们转身离去。这时,我才发现嘎嘎门对面的那个深褐色的古寨,虽然依然屹立不倒,可是垛口已经不复存在了。
张道虎,现代农民,在乡村从事瓜果养殖和文物保护,业余写作。现居湖北保康县马良镇峡峪河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