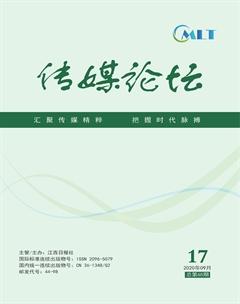媒介偏倚理论视角下花山岩画的传播探析
摘 要:从媒介偏倚理论出发可以发现,新的媒介技术改变着受众的时空体验,形成新的传播生态,同时也对民族文化传播的形式与内容提出了新的要求,花山岩画的传播一方面需要满足受众的新媒介时空体验,另一方面也要警惕迎合新媒介时空感知对文化内涵的侵蚀,应该在新的媒介技术环境下寻求传播的平衡性。
关键词:媒介偏倚;花山岩画;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079 (2020) 17-0-02
一、引言
加拿大学者伊尼斯在《帝国与传播》(1950)和《传播的偏倚》中论述了传播媒介的偏倚问题。偏倚时间的媒介是某种意义上的个人的、宗教的、历史的、特权媒介,强调传播者对媒介的垄断和在传播上的权威性、等级性和神圣性。偏倚空间的媒介则凭借其技术优势,更加偏向大众的、文化的、普通媒介,强调传播的流行化、现代化和公平化,因此,它有利于传播范围的控制和管理。
花山岩画位于广西宁明县耀达镇,是战国至东汉时期岭南左江流域壮族先民骆越人巫术活动遗留下来的遗迹,2016年“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顺利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岩画本身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具有历史性、空间性、形象化等特征,以媒介偏倚理论来分析新媒体的时空观,并在此基础上思考新媒体时空感知下的花山岩画文化传播也可以引发许多思考。
二、媒介的时空特性
人类的传播阶段经历了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几个阶段。
(1) 原始的口语传播阶段,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性能都处于较低水平,既不能远距离传播也不能长时间保存,然而两者却相对平衡;
(2) 文字媒介阶段在时间偏向性能上有了进步,甲骨文等一类的书写内容能够长时间的储存,但在传播范围上依然受限;
(3) 印刷媒介在保持书写媒介时间偏向性能的同时,实现了空间偏向性能的提升,使媒介系统恢复了时空偏向的相对平衡;
(4) 传统电子媒介在空间偏向性能上实现了突破,使媒介空间偏向性能凌驾于时间偏向性能之上,媒介时空偏向的相对平衡再次被打破。
农业社会时期,人们生活依照的是“自然时间”,工业社会里发明了钟表后,人们开始依据“钟表时间”生活,进入到媒介化社会,电子媒介正建构着人类新的时间观念——“媒介时间”,而当我们考察网络时代的媒介时间时会发现,全世界发生的大量事件呈现在受众面前时并没有所谓的时间顺序,它有可能是按照主题、类型或者任意联系同时出现,从而使整个事件都失去了其内在的时序性,此外,网络环境下信息接收的即时性也使接受者越来越排斥等待,同一事件的碎小信息可以在被知晓的当下立刻形成传播,也造成了媒介在时间上的碎片性和瞬间性。最后,即时性和碎片性的接收也会使媒介时间更加的个人化。造成的结果便是媒介化的生活里没有完整的、线性的时间逻辑,只有时间的拼贴,所有事件都好像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没有先后。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地理空间对人类来说已经不再神秘,传播速度的提高已经打破了人类生存的地域界限,麦克卢汉提出的“地球村”成为现实,空间距离不再是影响认识、影响传播的障碍。全世界的人们在网络上关注讨论同一个议题,参与同一个社会活动,形成了一个没有中心的空间、扁平化的空间、可以渗透边界和文化的空间,网络所形成空间里的社会活动对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會产生巨大的影响,网络打拐、网络打假、冰桶挑战、METOO运动……VR/AR技术下虚拟空间的沉浸,更是让媒介技术形成的空间与现实空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网络空间里以一种“缺席的在场”,形成新的社会连接和虚拟空间的整合。
三、花山岩画传播中的时空偏向
花山岩画以岩石作为媒介展示内容,是典型的偏倚时间性的媒介传播方式,也因此可以在时间的推移及沉淀中显示出他的“历史性”和“文化性”的价值。然而随着现代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及频繁的更新换代,对偏倚时间的传播媒介产生巨大的挑战。换言之,现代的传播媒介更多地注重向“空间”偏倚,即占领越来越多的传播面及受众,其造成的结果是典型的碎片化,“快餐式” “热点”层出不穷,但来得快去得也快,这种对于媒介“时间”特性的破坏会妨碍人们对事物的系统理解。
以“媒介偏倚”理论来观照,我们能发现在花山岩画的文化传播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从媒介空间来分析,“花山岩画”的传播小高峰出现在2016年岩画申遗前后,大量即时性的新闻议题的生产传播能够占领一定空间,但传播的方式依然是偏向传统媒体和传统的视频及新闻文字形式,缺乏新媒介环境里受众需要的“在场感”与“参与感”,也因此无法形成广泛的传播和讨论。从时间性上来看,花山岩画本身的媒介性质过多的偏向时间性,其沉淀的厚重历史内涵与今天的新媒介时间性强调“即时、浅层、碎片”来说本身就充满着矛盾。毋庸置疑,花山岩画在当下也采用了各种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利用新媒体技术看似打破了时空壁垒,但从传播效果来说,一是空间占领不够,二是对文化内涵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产生割裂。
四、媒介偏倚理论视角下花山岩画的传播启示
(一)满足受众的新媒介时空体验
正如上文中分析的那样,新的媒介技术改变着受众的时空体验,“沉浸式”的信息接收环境也塑造了受众新的信息接收习惯——生活在媒介容器中,瞬间体验时间流逝与空间流动的快感,无法从中抽离出来。前一秒还在为偶像剧中男女主角三生三世的虐恋揪心哭泣,后一秒便以“缺席的在场”在社交网络里对发生在遥远距离的社会新闻评头论足,这已经成为网络时代绝大部分受众的日常。压缩的时空体验使得大多数受众已经无法沉下心来对一个复杂的事件来龙去脉或者一个文化的历史内涵进行深入解读,如果不能让他在接触的第一时间里产生好奇或者明白大概,那么很大可能会被丢弃在信息的海洋里。
因此,文化传播也需要适应这样的情境,完成文化传播的下凡变身,满足受众新媒介的时空体验——即时满足与强调存在感。网上常见的“三分钟看完某部电影/电视剧” “一分钟带你浏览某个空间或事件”等内容便是对受众的“即时满足”,补救信息的碎片化。
“强调存在感”则是基于新的终端设备为受众提供的空间感知,“冰桶挑战” “朋友圈摄影大赛” “带着微博去旅行”等话题能够火爆和吸引更多人参与的要义便是新的媒介赋予受众的存在感。现实世界里发生的大小事件我们都喜欢拍照发到微博、微信朋友圈,朋友聚会时的美食“朋友圈先吃”,新媒介时空体验的核心之一就是强调存在感,“花山岩画”的传播需要从厚重的“历史”时间偏向了向大众化的“空间”转移,适应受众对信息接收即时、迅速的需求;同时又需要化解和避免传播时产生的距离感和陌生感,形成“缺席的在场”的存在感知,是花山岩画的传播适应新媒介时空的首要问题。
(二)警惕迎合新媒介时空感知对文化内涵的侵蚀
一方面我们要认识到新的媒介技术带来的媒介时空的影响,花山岩画的传播应在新的媒介时空感知下尽可能地满足其接收习惯和需求。但是另一方面,还需反思新技术带来的时空体验对文化的侵蚀。迎合碎片化、热点化的传播环境,造成的结果往往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妨碍接收者对事物的系统认知,挖空心思设计的话题或活动如昙花一现仅在短时间类产生一点火花便消失。
究其原因,网络传播生成的是一种极速文化,受众在新的媒介时空里的感知平衡被破坏,时间是断裂的、碎片的,只注重当下短暂的时间弥补和享受,时间序列和时间本身都被新技术的传播加速所消解。求新、求快、求趣、求浅是当前大众文化的主要表现。然而与流行文化相区别,民族传统文化需要延续性的时间来接收,才能对文化内涵产生深入的理解、思考和认同。
《红楼梦》为什么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褪色,反而历史长河中被无数受众无数次重新发现,产生思考,甚至形成“红学”,除了它本身的文化艺术价值外,还有赖于其偏向时间的传播媒介和传播环境。传统文化的时间厚重感如果缺失,会使文化背后的内涵、价值不能够沁入人心,最终使传统文化与受众之间产生无法跨越的时间鸿沟。
此外,从新媒介空间偏向上来说,一是快速发展的媒介技术打破了空间障碍,占有越来越多的传播面,形成“大众”文化与流行,二是受众的感知空间压缩,即我们常说的“地球村” “扁平空间”。二者的效果殊途同归,即增加了文化的同质化生产与接收。为了实现经济利益,需要不断扩大文化传播的范围,不断增加文化的生产量,同时想尽办法增加文化的消费量,其中最简单的办法便是用简单的、通俗的、流行的解释来取代复杂的、抽象的、差异化的文化内涵;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提到的那样直接以一套标准模式进行文化的工业化生产传播。
大众媒介技术的发展在打破时空障碍上可以说如日中天,我们欣喜于新的传播方式和传播环境的产生,但也必须去考虑这种新技术在发展的过程中瓦解了什么,特别是对文化传播来说,一味地迎合新的媒介技术环境,压缩时空感知,无疑会是致命的打击和侵蚀。
(三)“花山岩画”传播中的新媒介时空平衡
综观当前的“花山岩画”传播,更多的还是传统媒介环境下的传播,即电视纪录片、宣传片、旅游推介、闻报道等。过多的偏向时间厚重感,其结果正如上文所说,传播内容与受众之间存在距离感和陌生感,也缺乏参与度。而在受众的信息接收感知上,割裂了各个感官感知的整体性。新媒介技术发展让人的感官与认知难以分辨,为文化传播提供了立体式形态,VR\AR技术大行其道,虚拟现实与客观现实的边界越来越模糊。
在这样的技术背景下,我们所说的时空平衡變成媒介时间、现实时间、媒介空间、物理空间的多元感知平衡。新的传播体系以高效的传播方式扩大了信息传播的范围,同时也对传统文化艺术的形式与内容进行着选择与更新。如为纪念建军90周年,人民日报客户端借助人脸识别、融合成像等技术开发的H5产品《快看呐!这是我的军装照》,通过一键形成军装照,创造了10亿加的浏览量,H5链接被分享给微信好友或微信群的次数超过4800万次,H5链接被分享到朋友圈的次数超过1100万次……简单的一个产品却是新媒介多元时空平衡非常好的例子。要适合新的传播环境,“花山岩画”的传播也不得不顺从媒介的特性,去改变自己的生产与运作模式。简单的如数字花山博物馆,利用AR/VR技术形成“技术的在场”,创意活动直播将媒介时空与物理时空重叠形成感知平衡,线上传播适度的将“历史性”向“流行性”转移占领传播空间,线下传播包括线下文化产品的开发注重代入式的体验感和参与感。
五、结语
回顾整个传播史,传媒技术的发展实际上是从体内传播延伸到体外传播,以此来打破时空的障碍,追求感知能力的大幅提升。传媒技术的进步是对时间与空间的再分配与再整合。必须认识到人与媒介交互延伸这一新的特征,理解传媒偏向中人从信息的传播者、接收者也同时逐渐变成重要的“媒介”。基于技术设计的沉浸式的虚拟时空传播应用越来越多,而媒介技术发展对传播生态产生的变化和影响也会给研究者带来越来越多新的问题和视角。
参考文献:
[1]何镇飚,王润.新媒体时空观与社会变化:时空思想史的视角[J].国际新闻界,2014(05).
[2]陶阳谷.时空审视中的大众新媒介焦虑思考[J].现代视听,2016 (07).
[3]鲍立泉.新媒介群的媒介时空偏向特征研究[J].编辑之友.2013 (09).
[4]刘丹.新媒体时代的时空重构[J].新闻研究导刊.2016(24).
[5]余荣华.10亿+浏览量!人民日报“军装照”缘何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EB/OL].搜狐号:网络传播杂志https://www.sohu.com/a/274832892_181884,2018-11-12.
[6]吕文杰.花山岩画及其传说研究综述[J].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02):27-30.
作者简介:王敏利,女,汉族,广西全州人,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新媒体传播、民族文化传播。
课题项目:本文系广西民族师范学院2018年科研项目《媒介偏倚视角下花山岩画传播的“历史性”与“流行性”研究》 (项目编号:2018YB008)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