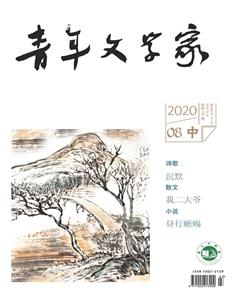英美新批评视域下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摘 要:透过英美新批评理论的内核,从语言伦理、书写伦理和阅读伦理三个层面阐释苏词《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的文学意蕴,进而挖掘中国传统文学的现代性价值。
关键词:英美新批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中国传统文学的现代性价值
作者简介:蔡宇莎(1994.12-),女,汉族,宁夏人,北方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文论与比较诗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0)-23-0-02
英美新批评作为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文论的重要流派之一,它通过对诗歌语言学层面的分析,得出影响诗歌创作和诗歌接受的、具有文本本体性的批评理论。而《定风波·莫听穿林打葉声》(为方便论述,后文简称《定风波》)由中国传统词人苏轼所作,并深受历代文人墨客的喜欢与推崇,但对于它的解读始终停滞于“知人论世”的传统美学批评范式中。为了还原这篇词作独立于词人的文学审美功用、建构中国传统文学的现代性价值,故而在英美新批评的理论视域下,从词作的语言伦理、书写伦理和阅读伦理三个层面阐发其文学意蕴。
一、语言伦理
英美新批评沿着现代语言学的研究路径,默认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具备符号性和系统性,而语言伦理是指语言在一定场域内被普遍遵循的语法规范,具体表现为语境、语音、语汇和语义。接下来,就从这四个维度剖析《定风波》的语言伦理。
这首词的产生离不开词作的诗学语境。众所周知,词从诗中脱衍而出,自然保留了众多有关诗的文学传统:早在先秦,《诗经》就开辟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抒情道路;等至汉朝,随着乐府诗的发展与兴盛,中国传统诗歌实现了四言诗向五言诗的过渡;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佛教进驻中原,加快了中国传统诗歌对于自身语音形式的革新,出现了讲求“四声”、避免“八病”的“永明体”诗歌;直到唐朝,诗歌的外在表现形式和诗歌的韵律原则达成统一;转至宋朝,想象世界的抒情需求同现实世界的叙事需求相互作用,共同推动诗歌转型为词。
它的题序说明了词作产生的现实语境。被贬黄州的苏轼在三月七日前往准备度过余生的沙湖探看农田,却在返归的路上遇到大雨。拿有雨具的仆人先行离开,被迫淋雨的同行者感到失落狼狈,但是苏轼并未察觉不悦,反倒认为这场雨下得别有一番趣味。不一会,天空就放晴了,回到家中的苏轼及时捕捉稍纵即逝的灵感,提笔写下《定风波》。
它的语音排列体现出文本的音乐性。上片和下片均各由五句话组成,上片依次为七言、七言、七言、两言、七言,下片依次为七言、两言、七言、两言、七言。其中,七言和两言的组合使用有助于词作旋律线的凸显和词作节奏的切分。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创造性地选用律诗的平仄格式,一方面较为坚持首句对仗,另一方面,力图打破律诗的“粘对”原则,将“仄仄平平平仄仄”连续运用。除此以外,上片的韵脚“声”和“生”同下片的韵脚“醒”和“晴”都出现在各自的首句和末句,从而保障句段语音形式的完满性。
它的语汇使用反映了词人的文学素养和语言格调。在朝为官的苏轼,拥有良好的家学渊源和极高的文学素养,他的诗词歌赋无不流露出雍容自得的文人气息。在六十二个字组成的《定风波》中,有不少字词折射出雅词的光晕,例如,“吟啸”、“徐行”、“平生”、“微冷”、“相迎”、“萧瑟”等。当然,由“穿林打叶”、“竹杖芒鞋”、“一蓑烟雨”、“料峭春风”、“山头斜照”等四字词的表述,恰恰体现出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文人对于雅俗共构文本这一审美准则的转向与接纳。
最后,在悖论、反讽和含混等表达技巧所形成的张力结构中,这首词的语义逐步走向丰盈。纵观全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和“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都是依据词人的悖论性体验而产生的悖论性词言。“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借助反讽,显露出词人不同于达官贵族的情丝意趣。“一蓑烟雨任平生”和“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凭借含混,将词句的字面意义和词人的人生顿悟紧密结合。
二、书写伦理
英美新批评主张诗歌中的世界并不是一个被诗人简化删改的世界,而是一个充满多重意义的本原世界。因此,诗人如何创造诗歌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诗歌对本原世界的展开与揭示,而诗人创造诗歌的方式统称为“书写伦理”。接下来将从写作视角、写作内容和写作主旨等三个方面洞悉《定风波》的书写伦理。
苏轼在写这首词时,受到封建贵族和市井平民双重视角的影响。一方面,唐末宋初以前文学话语的主导权始终掌握在王公贵族的手中,他们继承前人的文学遗产,并在以皇权为中心的文学范畴内不断进行文学内容和文学形式的开拓。另一方面,因教育体制的革新和官僚机制的调整,有许多来自社会中层和底层的文人学士进入朝阁,而他们的审美风尚势必会作用于宫廷文人的创作。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扎根,一批具有非主流文学审美的文学接受者开始要求能够容纳除庙堂文学以外的、更加多样的文学作品。最终,词成为达官显贵进行文学实验的阵地,成为饭后茶余的调剂品。当然,作为身处朝野中心的政治家和文学骄子的苏轼也不例外。
词作上片是作家在处境中的所思所想,下片是作家将自己置于处境的空间之外所进行的一种超越场景、超越自身的哲学性思考。上片:词人截取下雨时的一段场景,重在描述自己在雨中的心情。首先呈现一个不害怕风雨的心境,然后是在风雨之中怀揣万丈豪情。然后将自己的窘迫处境和别人的幸福人生进行比较,最后认清生活的现实,选择现实所带给他的一切。他冷静地分析了自己的处境,并接纳这样的人生。下片:词人截取雨后的一段场景,酒醒后的词人看到被夕阳斜照的山头,突然意识到,人生其实没必要着眼于那些快乐与悲伤,所有的沉浮都只不过是一场经历,如果看明白这一点,就会明白人生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写这首词的目的不仅在于抒发情感,还在于透过风雨人生,看到人间大道。词说;“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回首看看曾经经历风雨潇潇的那段路,似乎也没有那么坎坷、那么顺利。事实上,停笔至此的苏先生才真真顿悟生活的真谛,风风雨雨是生活,轻轻松松是生活,失意漫长是生活,幸福短暂是生活,生活嘛——陌生地过活所有发生的平凡时刻。苏轼得意但不自负,他明白所谓的乐观豁达不过是普通人面对苦难的一种平衡方式,那些在乎的、关心的始终抵不过平淡与真实。
根据上述内容,不难发现,词作的意义在经历了感情的升腾、理性的思考、现实的陈述和生命哲学的积淀,作家借助作品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依依展现,并且在这个过程,作家通过写作,促进自己的思考,更新自己的思想境界,把从现实生活中所带来的个性逐渐瓦解和重塑。所以,写作伦理的意义在于作家通过写作,形成文本智慧,并逐渐与文本保持相对独立的关系,即:当作品完成的时候,作家的写作使命完成;作品具有了其独立的价值,并与作家形成相对独立的关系。从这个层面上讲,当词被词人创造出来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词人的媒介使命完成,并与词实现了“万物与我一体”的审美理想。
三、阅读伦理
在西方文论史上,英美“新批评”的出现标志着从文学外部研究转向文学内部研究,文本开始具备相较独立的文学价值,不再被某种单一视角列为政治或宗教的传声筒,而是转变为借助现实生活表现人性、反映人心的媒介。这也就意味着与文本紧密相关的读者,也需要从忽视文本本身转向发现文本自身价值,从而更新自己的阅读方式,感受不同于传统的阅读体验,从而做到尊重作家的创作、尊重文本的叙事性和抒情性、尊重读者的主体性,以便于诗意地栖居在被开拓出的大地上。
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认为作家的生平经历及文学素养、作家所在的社会环境及时代背景对作品的产生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为了更加准确地提炼出该词的文本价值,读者需要结合作者的相关生平经历和创作背景。人们常说能够写出伟大作品的作家都是一群幼稚至极的孩童,尤其是中国古典诗词圣坛中的作家。他们在政治生活中不具备长远眼光和趋利避害的能力,常常陷于平白无故的党争,为排遣郁结于胸的烦闷,转向文學的创造,故有“国有不幸诗家幸”的说法。此观点的产生与发展必然有一定的原因,但此观点不一定完全适用于苏轼。他来自四川眉山,经过考学为官,从地方升至中央,倘若没有什么真才实学、没能为百姓办实事谋发展,他至多不过是一介清贫书生,整日为食色之事辛劳奔波。所以,作为有为青年,他固然有自己的为官之道、处事之方。至于那件被文学史家主观放大的“乌台诗案”不过是国家进行政治变革而采用的一项文化性政策。该项自下而上的文化政策在颁布与实施的过程中势必影响居于文化上位者的利益,而苏轼作为一名身处于国家机器上的骨干,必然逃避不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命运。当然,这段历史无疑从根本上促进了苏轼对于生活本质的思考,提高了对于文学艺术创作的能力,确定了在宋代文坛的核心地位,至于本篇词作,便是他被贬黄州的第三个春天所写。
另外,深受诗学传统影响的读者常常习惯于把这部作品纳入婉约派的行列,实际上,婉约是苏轼采取的一种艺术策略,是词作意象进行排列组合所产生的形式效果,就其根本风格理应是豪放派。苏轼未经同意,就被归置于传统;他自以为与传统决裂,却深受传统影响;他与传统达成和解,并开始调用传统;传统生育现代,现代演化传统……换言之,身处复杂环境的苏轼,勇敢直面一个又一个困难,并动用智慧来探索、理解其内质,向着不断形成的自我理想辛苦跋涉、努力靠近,而这种精神恰恰熔铸于苏轼在文本当中所创造的叙述者形象之中。特别地,当把文学照进现实时,该人物形象又何尝不是一位为天地立心的歌者、一位白发渔樵江渚上的隐者、一位头脑清醒投身现实的战士、一位有勇气成为平凡人的智者?倘若如此文学光晕仅仅理解为一种温和平淡的气质,会不会难承其重?故而,这部作品是一部用婉约之形彰显豪放之情的佳作。
四、中国传统文学的现代性价值
《定风波》被视为中国宋代词人苏轼的佳作之一,里面必会积淀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学追求、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功用,而通过英美新批评的理论方法,有助于在历史新时期语境下重新理解和阐释它的现当代价值,进一步探究中国传统文学的现代性。
《定风波》中的叙述者形象揭示出人的悖论性体验和悖论性存在。这个叙述者形象与词人本身有着很大的契合,在一定程度上水乳交融,最终导向作为人的生存处境,并用一种诗性的情怀接纳生命的美与丑、乐与痛,在一种潜隐于世的二元对立中寻得统一。
《定风波》反映出想要建立审美共同体的美好追求。从文本内部看,现实环境与文本的想象环境相结合、文学传统与时代文学诉求相结合、大语言与文学语言的充分结合、文本结构与诗歌结构的交叉与组织共同形成一个由各类符号组成自稳定系统,反映出一种文学创作的和谐统一的中国文学文本风尚。从文本外部看,苏轼作为政治家和文学家的双重身份、苏轼文学作品在宋朝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学空间中的坐标性价值共同整合为一种闪现中国人气质、延续中国人精神血脉的丰碑。故而,从文到人,暗含了一种巨大的文学力量:在审美力量的组织与调度下,告诉我们“人”从未离开家园,“人”从未身处家园,我们能够拥有的只能是一份直面生活的勇气与坦诚、一份抚慰心灵的安宁与诗意。
参考文献:
[1]吴铜运主编.高中文言文译注及赏析.长春:长春出版社,2015.
[2]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3]马新国主编.西方文论史(修订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