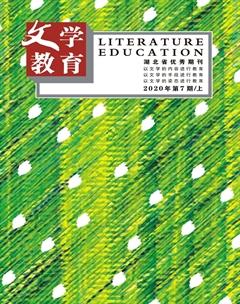信仰的救赎:从宣泄与补偿解读《智血》
内容摘要:弗兰纳里·奥康纳是20世纪美国南部的女作家,在美国文学史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奥康纳几乎所有的小说都展现了她眼中信仰在当时特定社会背景下的生存窘状,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作者的心理失衡,修补这种缺失成了奥康纳创作的动机。本文将以奥康纳的代表作《智血》为例,从心理的宣泄与补偿的角度看作者将海兹等畸形信徒人物安排在当时尴尬困境中情节的写作意图。
关键词:《智血》 弗兰纳里·奥康纳 心理宣泄 心理补偿
奥康纳出生在美国南部的佐治亚州的一个天主教家庭,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她创作的高峰时期,这个时期的美国南部正处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一切都在进一步商业化。但奥康纳看见了它物欲横流且信仰摇摇欲坠和虚无主义的社会本质,它不能再为这位虔诚的教徒带来一种强有力的信仰的力量了。社会心理学家伯科威茨(L.eBkrouitz)认为当个体在既定的环境中无法获得想获得的东西时,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出现“相对剥夺”的产物——挫折。当个体被激起挫折感时,就会采取一些方式去填补剥夺感带来的心理空缺体验,这时候有的个体会选择做出侵犯、宣泄等行为。奥康纳作为一个狂热的天主教教徒,面对无法在人群中再感到到信仰存在的情况选择了写作,用笔下人物不断追寻探求的故事最终找到耶稣、皈依耶稣的故事来作为一个替代性满足达到心理补偿的目的。
在奥康纳那里,上帝并不单单只是一个启示,一个神迹。她认为没有任何人可以代表上帝。在她笔下与宗教有关的人物没有一个不是畸形的,身份上的畸形、心理上的畸形、身体上的畸性……但奥康纳的作品并没有停留在只是描写上帝显灵治愈了这些畸形的部分来展现信仰的肤浅表面,而是通过畸形人物对信仰的怀疑到故意毁灭再到接受上帝来使信仰迸发出更大的力量,以一种重塑的形式,让笔下的人物从当时令人失望的社会里解脱出来回到上帝那里去。就像她写给友人的信中说的那样:“每部伟大的作品中,都会有一个上帝的恩典涌现、等待被接受或被拒绝的时刻。”[1]奥康纳处于一个信仰逐渐缺失的年代,她在她的作品中表达着“上帝一直在身边”的观点,在当时社会现状不能支持她的信仰的同时,这也是一种弥补。
一.心理失衡的起源:信仰的生存窘状
《智血》以一个青年教徒海泽·莫茨(Hazel Motes)坐火车想回到故乡却去了另一个城市开始生活展开整个故事,整个故事展示了当时美国南部的两个现状,一个是社会中无处不见的虚无主义和信仰危机;就像第一章描写的那样,海泽参军时战友们告诉他根本没有什么灵魂,在火车上向耶稣发出呼喊得到的却是列车员的一句:“耶稣早就消失了”。当海泽说道自己不信耶稣时,女人的反应是“谁说一定得信”等等,实际上这辆火车上根本没有人在乎海泽是否相信耶稣,因为他们心里早把耶稣抛下了。另一个现状则是人们对信仰的理解只停留在表面,认为上帝必定会以神迹的形式向人们宣告存在并拯救自己的信徒;海泽的祖父是他们那的巡回布道师,满脑子耶稣,但最后人们把棺材盖子关上他仍动也没动。在祖父的口中耶稣之血为救赎人类的灵魂而流,无论是多么肮脏灵魂耶稣也不离不弃,但在祖父死时,他的信仰没有产生任何拯救他的灵魂的迹象。在天主教中罪恶的实质是指人迷失了,离开了正路(通向耶稣身旁的路)。但祖父只看到了耶稣为拯救有罪的人而死,但他忽略一个事实,耶稣之血最终只会拯救那些真正忠于他的人(遵循上帝旨意的人)。[2]这是海泽后期陷入矛盾境地的直接原因,一方面内心深处对耶稣深信不疑,一方面又无法相信像祖父那样的布道师口中塑造的上帝表象,所以不断“犯罪”企图让耶稣显灵惩罚自己来证明自己的信仰是真实存在的。奥康纳被夹在这两种社会现状的洪流中,但她仍然积极地信奉自己的信仰,她通过移情给海泽·莫茨这个人物,让其几经波折最终皈依上帝来进行了一次心灵之旅。
海泽在到达托金罕后开始了远离耶稣的“罪恶”之路,在这个城市他邂逅了霍克斯、萨巴斯、恩克诺等人,这些畸形的人物都是当时社会现状下天主教信徒的缩影。一部分是以恩诺克为代表的人,另一部分人则以霍克斯、绍茨等人为代表。在奥康纳看来,他们各有各的罪恶,都是需要被摒弃被惩罚的特殊群体。
二.心理宣泄:对信仰困境中信徒恶劣行径的摧毁
书中恩诺克是一个盲目坚信自己身上流着智慧的血液的人,他并不尊重上帝,但听了海泽的新教说法后为他偷来了博物馆中的干尸,认为那可以代表新教中的新耶稣,做这一切只为了自己能成为海泽新教中的“人物”来证明身体中智血的正确性,但后来那具干尸却被海泽摔得粉碎。书的最后恩诺克去抢走了猩猩的服装,变成了猩猩。就像奥康纳本人所说那样,恩诺克的智血流遍全身就是没有流到他的脑子里。恩诺克认为耶稣仅仅是一个启示,一定会选中某个人,一定会有一个实物化的代表,这就是他对信仰的理解,书中奥康纳安排恩诺克夺走猩猩服装穿上蜕变成猩猩的情节戏剧性的展现了这个坚信自己流着智慧血液的人,在那猩猩表皮下仍然愚蠢的本质。奥康纳通过塑造恩诺克这个人物来狠狠嘲讽了那些曲解和对信仰理解不透彻的人,這些人对耶稣的定义是对当时社会虚无主义的一种变相的认可。尼采认为虚无主义来源于人们意识到“上帝死了”,如果上帝只是一种启示,是一个人,是一种代表,是人们感性世界的一部分,它不具备永恒的特质,那么它是归属于虚无的,这是对信仰的一种驳斥与挑衅。她本人也曾言道:“如果上帝仅仅只是一个启示那还不如没有上帝。”最终奥康纳用这样的情节安排否决了那些浅薄的理解,她把恩诺克变成了猩猩,这个从头到尾都认为自己是智慧血液的拥有者不过是一个对信仰浅信即止的荒唐小丑罢了。在弗洛伊德看来,潜意识的自然流露则是文学作品的本质。他认为一篇作品是一个作家的幻想代表,因为成人的幻想在现实生活中受道德、法律等的限制很难实现,因而必须用一些手段加以隐藏,用文学创作来宣泄、补偿的行为就这样产生了[3]。前文提到,作为虔诚且狂热的信徒,奥康纳对像以恩诺克为代表的人的作为感到愤怒与不屑,但在现实生活中奥康纳没有办法去让这些人中每一个都领悟真谛,所以在《智血》中出现了恩诺克这样的角色,用以宣泄她内心对这类人的肤浅而盲目的厌恶情绪。
而像霍克斯这样的在布道会上企图用弄瞎眼睛来证明自己忠于上帝最终却还是胆怯退缩了,扮作盲布道师整日宣扬上帝一副一切信仰至上模样的信徒却有一个违背教规的私生女,这种狂信徒与未婚父亲重叠的身份加剧了这种悲剧式的冲突,私生女萨巴斯被抛弃成为定局,而上船离开的霍克斯也许就预示着他会在逃离谎言的过程中走向下一个未知的灾厄。至于绍茨则根本不在乎上帝,他只想要钱,盗取了海泽的“新教”与另一个和海泽酷似的先知索拉斯·莱菲尔德一起在街上用“没有耶稣基督的圣教”来骗取钱财。最终以海泽故意撞死这位先知为这场新教骗局画上句号。奥康纳对这段杀人场景描写得很細致:“先知吓得开始狂奔起来。他撕掉衬衫,解开皮带,扒掉裤子,并伸手抓着腿想把鞋子也脱掉,但还没有等够到,埃塞克斯就把他撞翻在地,从他身上碾了过去。海泽开出去大约二十英尺后停下车,接着又倒了回去,再次碾过那人的身体,这才停下走了出来。埃塞克斯压住那位先知的半边身体,好像正得意扬扬地守卫着这终于被他压倒的人。此时,那人趴在地上,没了衣服和帽子,看上去和海泽并不相像...”[4]按照文艺心理学的观点,作者安排的故事情节是作者的心理投射,那么在《智血》中海泽撞死先知的情节就能很好的展现出奥康纳面对上述社会现状的愤怒心理。她描写海泽撞倒先知后又再开车碾压回去,用暴力冲突场面把内心对于这种信仰缺失的焦虑全部跃然纸上。文中海泽在撞先知之前命令他脱掉衣服,后面又描写没了衣服的先知与海泽并不相像,说明先知只是装扮了海泽的表,没有与他的质相似。奥康纳特地用这个细节把两者区别开来,也就相当于在把自己与停留在信仰表面的人区别开来。先知在《智血》中为了自己的私欲对自己明明相信的东西说出不相信的话,这使海泽很愤怒,他是:“有两种人我最受不了”[5]“一种是不真诚的人,另一种是伪装成别人的人”[6],先知两种人都占了,最终招致了自身的毁灭,但这样的人还是在死之前还奋力呼喊着耶稣求救。奥康纳描写海泽给了这家伙一掌猛击,那之后他终于死了,但海泽却毫不惊慌也不后悔,好像很享受除去这类人的过程,甚至想听听他还想说什么却发现没了呼吸。他对尸体毫不关心而是转过头去擦试自己的车然后回城。这一部分的描写是奥康纳心理宣泄的高潮部分,从海泽两次“碾”过先知、用“脚尖踢”他、在他背上“猛击一掌”以及埃塞克斯“得意扬扬地守卫着”半死不活的先知的这些细节和从头到尾海泽对杀害先知的主观态度都能看出来奥康纳是愤怒的、蔑视的。就像叶舒宪先生在《文学与治疗》提到的文学治疗自身的观点那样,作家通过文学创作将内心积压的情绪于作品中宣泄出来,才能在精神上获得健康。奥康纳生活在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的美国南部,这个对信仰分外在意的传统地区在向现代化商业化的过渡中不断地遗失自身的一些东西,逐步进入虚无主义的世界。奥康纳就将海泽安排在这样的小说背景下,安排了他去杀掉这个招摇撞骗的先知,用这种怪诞和暴力的安排去释放心中的怒气,缓解自己身在当前社会里精神和心理上的失衡。这也就顺应了普鲁斯特所说的“写作有益于身心健康”的观点。
三.心理补偿:脱离现实困境后信仰的最终救赎
对于信仰奥康纳有着异于常人的坚定与深刻理解,在那个年代的美国,如何面对虚无主义成为那个时代的人了一个核心问题。[7]海泽的出现不仅仅是一种奥康纳对于社会现状的愤怒宣泄,还是一种与虚无主义的对抗,是奥康纳对人类信仰的扩充,更是奥康纳的一种积极心理补偿。在海泽撞死了先知之后,他开始思考如何在下一个城市城市开展宣扬他的“新教”,但这时候海泽的车已经破损到无法到达下一个城市了。他让加油站的小伙子给他灌了水就上路了。“你只管灌好了”[8]他说得这样义无反顾,“要了张地图就开上路了”[9]。但在接下来的行程中海泽的车被警察推下了坡,他去往新教的道路也被截断了,接着海泽返回了女房东那儿把自己弄瞎,故事至此海泽的皈依之路才真正进入化形期。
在书中海泽认为他有一辆车,这车就可以带他去任何地方。当时海泽的唯一想法就是开着这辆车去下一个城市布道、宣传他的新教。车其实可以看作是奥康纳为海泽创造出来的具有现实意义的满足自我需要的工具,在故事的前中期海泽都为了逃避罪恶而逃避耶稣,为了逃避罪恶不惜创造出一个荒诞的新教会。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最高级的需要就是自我实现的需要。每个人都为了达到这个需要不断的提升自我,追求真善美让自己趋于完人。海泽逃避罪恶正是为了满足这种最高需求的一个表现,如果没有耶稣也就没有罪恶也就不需要被拯救,这种想法正好就为满足自我实现的需求提供了可能性,但这种什么都没有的理论正是虚无主义的代表。他的车作为让他不断宣扬这个新教会的“帮手”被路上的一位警察推下山摔得“马达也弹出来滚到了远处”[10]也就象征着海泽这种企图利用虚无主义理论逃避罪恶的不可行性。
在海泽的车被推下山后,“海泽看着这一幕,呆了几分钟。他的脸仿佛反射出了前方整个壮阔的画面,从眼睛到灰蒙蒙的辽阔天空,不断地深入,一直到漫无边际的太空。然后他双膝一软,两脚悬空地瘫坐在路堤上。”[11]接着警察问他想去哪里自己可以捎他过去,海泽却回答“哪也不去”[12]警察注意到海泽“脸上的表情一成不变,都没有把头转过去正眼看那个警官。他似乎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那广袤无垠的宇宙中去了”[13]这部分描写了海泽的逃避之路受到不可抗的阻挠后海泽的反应。海泽的眼睛透过天空深入到宇宙中去了,且一直将注意力集中于那里,他终于看到了平日里被他所忽视的东西,在一切逃避罪恶的方式都被摧毁之后,海泽终于意识到上帝就在身边,这也为后面回去后买石灰弄瞎眼睛埋下了伏笔。在海泽弄瞎眼睛之后跟女房东说:“如果眼睛没有底,反而能装更多东西”[14]从前他眼睛还是好的时候他都忙着逃避罪恶逃避上帝,眼里装不下上帝,如今眼睛瞎了,不用再看现实里的东西了反而能够将自己的信仰装进去。海泽在弄瞎眼睛之后女房东问他为何不再布道了,海泽回答说没有时间,因为自己要还债。海泽在胸口绑铁丝,在鞋子里铺沙砾、玻璃渣等穿着走路,都是在为曾经远离上帝的罪恶还债。女房东“总会觉得身边藏着某个东西,却又怎么也找不到”[15]那就是上帝一直在身边的描述。
奥康纳在海泽弄瞎双眼后从房东对他的观察中描写了海泽皈依上帝后的状态。女房东认为海泽的脑袋“比外面的世界都还要大,大到足以囊括天空和行星,以及过去、现在和未来所有的东西”[16]最后她在海泽的尸体旁“感到终于抵达了某个遥不可及的起点,只见他越走越远,渐渐隐入黑暗之中,直到变成那一个光点。”[17]海泽皈依上帝到死亡的这一部分是奥康纳心理补偿的代表。海泽从原来的怀疑到逃避最后终于直面信仰皈依信仰,也是当时社会里多数信徒对待信仰的缩影,奥康纳给《智血》的主角海泽(Hazel)这个名字,在《新约》中Hazel意为看得见上帝的人,其实在小说的开头海泽一出场就为结局海泽一定会皈依上帝给出了提示。全篇的升华部分被放在了结尾,海泽弄瞎眼睛、赎罪、死去、最终回到上帝那里去。奥康纳将自己的作品看作是一件艺术品,认为它拥有拯救他人的力量,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正是需要一个海泽这样的信仰领导者,把人类信仰从表层推动到一个新的高度,奥康纳在生活中没有这么一个人出现,于是她创造了海泽,用《智血》的故事不仅补偿了当时社会气氛下让自己产生的信仰相對剥夺感,也填补了当时社会下信仰救赎者这个空缺。在小说的开头,海泽在火车上发现自己的痛苦只发自思乡与耶稣无关。那时候的莫茨家就只剩他一个人了,已经没有家了,他无法再回到家乡。而在《希伯来书》中提到:“他们所向往的是一个更美好的,就是在天上的家乡。”在天主教中信徒们都会在天上的家乡再团圆。在故事的结尾海泽变成了一个光点,揭示了他皈依上帝后,回到了天上的故乡。[18]奥康纳用这个细节展示了上帝的恩典,这对15岁就失去父亲的她来说也是一种心理补偿,通过描写海泽最后得以平静解脱为自己与父亲创造了一种“天上再见”的可能性,也减弱了身患红斑狼疮的她的死亡焦虑,她本人就是比海泽更加虔诚的信徒。
四.结语
用现在的目光来看弗兰纳里·奥康纳,是她特殊的信徒身份和那个时期美国南部的社会气氛成就了《智血》。她的《智血》也为美国宗教文学增添了新鲜血液。但就奥康纳本人来看,笔者认为更多的展示的是她对当时社会的一种警告和她本人内心翻涌的情绪。从奥康纳其他著作里可以看出“接受上帝的恩典获得救赎”是她永恒不变的母题,怪诞、阴暗、哥特式的描写都成为奥康纳的标签。但“真正的艺术家却要鞭辟入里,要投进深渊里披泥探珠,所以他们得到的意象精妙深刻,不落俗套。”[19]在奥康纳写作的那个年代,整个美国其实都普遍存在一种怨气即对现代社会的不满,他们感到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精神荒漠,那个时期美国文学很多作品都描写了现代美国生活的孤独和空虚。所以奥康纳笔下的世界也是凄凉而扭曲的,她在极力展示着一个没有天意的世界的无序与混沌,她创造的人物都是“不合时宜”的、“矛盾”的、“残缺”的,是当时社会某些群体的缩影。奥康纳用这些人的故事来展示人生与信仰二者的关系,一方面在作品中惩戒他们,另一方面又利用他们昭示信仰的本质。借移情于作品宣泄她的“怨气”也通过最后作品主人公被救赎来达到一种精神满足。
参考文献
[1][4][5][6][8][9][10][11][12][13][14][15][16][17]弗兰纳里·奥康纳著,殷杲译.智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v,133,133,133,135,135,137,137,1
37,137,145,145,143,152
[2][18]蒋莉莎.怨恨之维—弗兰纳里·奥康纳小说新析[D].华东师范大学,2011:27,31-32
[3]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滕守尧等译.性爱与文明[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141-156
[7]杨纪平.反抗、皈依、幻灭——奥康纳《智血》中的宗教思想[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8(01):110-113.
[19]朱光潜.文艺心理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208
(作者介绍:江悦溪,成都大学师范学院2017级应用心理学专业学生,研究方向:心理学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