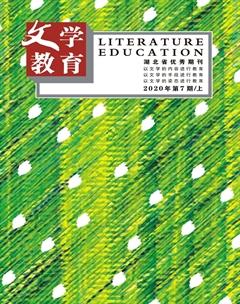香雪们的青春
内容摘要:青春意味着成长,同时也意味着对自我的认知。这种自我认知是复杂的,既包含对自己内心的认识和体验,更是以多种外在关系为坐标,对自己存在的定位与评价,并由此确定自我的人生方向。在台儿沟的姑娘中,香雪无疑是自我意识最为明显的一个,也是对自我的定位和处境最为敏感、认识最为清楚的一个。火车来了,香雪总是第一个出门,但是,当姑娘们向火车涌去时,“只有香雪躲在后边,双手紧紧捂着耳朵。看火车,她跑在最前边;火车来了,她却缩到最后去了。她有点害怕它那巨大的车头,车头那么雄壮地喷吐着白雾,仿佛一口气就能把台儿沟吸进肚里。它那撼天动地的轰鸣也叫她感到恐惧。在它跟前,她简直像一棵没根的小草。”人与机器是一个隐喻,在其背后有着丰富的内容。
关键词:《哦,香雪》 青春 时代
铁凝的《哦,香雪》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虽然只是一篇短篇小说,但它丰富的语义直到现在似乎还远未阐释完结,这正是经典的特性与魅力。
要深入地理解这篇小说,就要将它放到它创作的时代中去。一般来说,每个作家都不可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一些作家的创作与他所处的时代可能近一点,一些作家与他所处的时代可能远一点,但他们与时代,与他所处的社会现实总是密切相关的。《哦,香雪》创作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现在的年轻读者可能对四十多年前的中国现实缺乏真切的了解。那是一个天地翻覆的时代,是一个改革创新的时代,是一个热血沸腾的时代,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热情、希望与理想的时代。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有过许多这样的时代,除旧布新,人们喜欢用青春、青年,甚至少年去形容这样的年代,它告别旧时代,开辟新生活,因此它充满了活力。中国四十年前的改革开放正是这样的年代。这样的色彩也必然反映到文学作品中,并且产生了一大批堪称经典的作品。铁凝的《哦,香雪》就是其中的典型。所以,阅读这篇小说,在为其中的青春热情感动的同时,要去寻找这一青春情感的源头,去理解它所包含的时代气息。
这种新生的、带着青春气息的年代总是相对于过去而言的。与它相近的几个时间节点我们要知道,一是1976年结束了十年动乱,二是1978年底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合体会议,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从文革结束到八十年代初,中国当代文学曾经出现过短期但影响巨大的,以反映十七年特别是文革十年动乱生活的“伤痕文学”。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社会与经济开始了全面复苏和跨越式发展。仅仅短短几年时间,中国文学的精神面貌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歌唱新时代,描绘新变化,礼赞新生活成为文学的重要主题。可以将《哦,香雪》与此前几年的“伤痕文学”进行比较,《哦,香雪》除了出现了“公社”这一带有过去色彩的字眼以外,完全没有对此前生活的描写,作品中的人物几乎都没有对过去生活的记忆。台儿沟虽然不富裕,甚至落后,但这种不富裕和落后似乎是抽象的,小说对此采用的是一种中国传统乡土小说普遍性的描述,甚至,它还带有了古老乡村的温情和诗意。作品显然回避了对十七年特别是十年文革中国农村停滞发展的描写,也未对产生贫穷、落后的社会原因作任何的反思与批判。换句话说,作品采取的是正面的视角,同时也是前瞻的视角,用当时倡导的主流态度就是“一切向前看”。它用一列火车的到来喻示了台儿沟的开放,表明了台儿沟将告别封闭、落后走向光明、进步和富裕。火车曾经是现代工业的象征,作为一种成熟的文学意象,它一直是现代化、进步、力量与开放的载体,在文学作品中,类似的意象还有许多,如电灯、电话、广播、公路等等,一切现代的、工业文明的产物都与深山、农舍、炊烟、小桥流水、鸡鸣犬吠等构成对比,显示了改造旧世界、创造新生活的力量。在《哦,香雪》中,火车再次被赋予这样的功能。是火车的到来,使古老的台儿沟获得了新生。
如果不是有人发明了火车,如果不是有人把铁轨铺进深山,你怎么也不会发现台儿沟这个小村。它和它的十几户乡亲,一心一意掩藏在大山那深深的皱褶里,从春到夏,从秋到冬,默默地接受着大山任意给予的温存和粗暴。
这不是普通的火车,这是从首都北京开来的火车,而且,火车不仅仅是经过,还要在台儿沟停靠一分钟。“这短暂的一分钟,搅乱了台儿沟以往的宁静。”小说由此开始了它的故事。
这时,故事的主角出现了,这是一群年轻的姑娘。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虽然是火车改变了台儿沟,但这十几户乡亲出场的只是这些年轻的姑娘们。显然,作者认為年轻人更容易接受新事物,对陌生的事物更为好奇,也更向往外面的生活,而女孩子们从形象、言谈举止上也更显青春活力,更具美感。当火车还没在台儿沟设站只是一经而过的时候,姑娘们就兴奋起来了。
十七八岁的漂亮姑娘,每逢列车疾驶而过,她们就成帮搭伙地站在村口,翘着下巴,贪婪、专注地仰望着火车。有人朝车厢指点,不时能听见她们由于互相捶打而发出的一两声娇嗔的尖叫。
等到火车在台儿沟停靠后,就更不得了了。
台儿沟的姑娘们刚把晚饭端上桌就慌了神,她们心不在焉地胡乱吃几口,扔下碗就开始梳妆打扮。她们洗净蒙受了一天的黄土、风尘,露出粗糙、红润的面色,把头发梳得乌亮,然后就比赛着穿出最好的衣裳。有人换上了过年时才穿的新鞋,有人还悄悄往脸上涂点胭脂。尽管火车到站时已经天黑,她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心思,刻意斟酌着服饰和容貌。然后,她们就朝村口,朝火车经过的地方跑去。
还有小说最后的场景,已经不仅仅是这群被火车带动起来的姑娘,连同她们的古老的家乡都迸发出了活力。
山谷里爆发了姑娘们欢乐的呐喊。她们叫着香雪的名字,声音是那样奔放,热烈;她们笑着,笑得是那样不加掩饰,无所顾忌。古老的群山终于被感动得战栗了,它发出洪亮低沉的回音,和她们共同欢呼着。
这些是多么欢乐的场景,充满着青春时期特有的情感、心理、动作与表情。梳妆、打扮、出门,迎接火车的到来,这每天的一分钟,成了台儿沟姑娘们的必修课。随着故事的进程,姑娘们不仅是看,她们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火车开进台儿沟的生活中,她们与乘客们交流,与乘务员交流,与他们做起了买卖。在这样的生活中,她们走出了台儿沟,而外面的生活也走进了她们的心里。一切都是新鲜的,充满了诱惑、希望,连同她们生活的环境,一切都在改变,都在变得美好。正如那时流行歌曲所歌唱的,“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阳光”。这就是八十年代,重新启航的中国,青春的中国。
青春意味着成长,同时也意味着对自我的认知。这种自我认知是复杂的,既包含对自己内心的认识和体验,更是以多种外在关系为坐标,对自己存在的定位与评价,并由此确定自我的人生方向。在台儿沟的姑娘中,香雪无疑是自我意识最为明显的一个,也是对自我的定位和处境最为敏感、认识最为清楚的一个。火车来了,香雪总是第一个出门,但是,当姑娘们向火车涌去时,“只有香雪躲在后边,双手紧紧捂着耳朵。看火车,她跑在最前边;火车来了,她却缩到最后去了。她有点害怕它那巨大的车头,车头那么雄壮地喷吐着白雾,仿佛一口气就能把台儿沟吸进肚里。它那撼天动地的轰鸣也叫她感到恐惧。在它跟前,她简直像一棵没根的小草。”人与机器是一个隐喻,在其背后有着丰富的内容。香雪不仅对火车这一庞大的机器感到恐惧,更对它所带来的一切未知的东西感到茫然,在它所代表的城市、现代化、财富、进步等等面前,她作为落后的山里人感到无比的渺小和自卑。这是香雪的自我定位,也是香雪意识到的人生境遇。这样的定位与人生境遇不是火车来的那一天才被她意识到,不一定是火车,也不一定非得是火车的出发地首都,其实,离台儿沟十五里地的公社,以及居住在公社的同学与台儿沟和香雪就已经构成了城与乡的差别,她们的生活对香雪来说是遥不可及的,所以,她们在香雪面前具有明显的优势。“她们的言谈举止,一个眼神,一声轻轻的笑,好像都是为了叫香雪意识到,她是小地方来的,穷地方来的。”她们用的是塑料文具盒,一天吃三顿饭,而香雪用的是做木匠的父亲为她做的木头文具盒,一天吃两顿饭。“香雪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了,她好像忽然明白了同学们对于她的再三盘问,明白了台儿沟是多么贫穷。她第一次意识到这是不光彩的。”这不仅仅是香雪对自己的定位和生存状态的认知,而且,这认知里面包含的价值判断有着那个时代鲜明的特色。正是在那个时代,人们才开始认识到贫穷是不光彩的。与此相关,过去不曾意识到的或者被压抑的城市、现代、洋气、美丽等等才开始作为正面的东西被肯定和追求。
令人欣慰的是,这种自我的定位并没有压倒香雪,相反,成为她改变生存境遇的起点。香雪和台儿沟的姑娘们一道,开始了对新生活的追求。
日久天长,这五彩缤纷的一分钟,竟变得更加五彩缤纷起来。就在这个一分钟里,她们开始挎上装满核桃、鸡蛋、大枣的长方形柳条篮子,站在车窗下,抓紧时间跟旅客和和气气地做买卖,她们踮着脚尖,双臂伸得直直的,把整筐的鸡蛋、红枣举上窗口,换回台儿沟少见的挂面、火柴,以及属于姑娘们自己的发卡、香皂,有时,有人还会冒着回家挨骂的风险,换回花色繁多的纱巾和能松能紧的尼龙袜。
这可不是一般的物物交换,再往前几年,这样的交易是不可想象的。不管是哪种交换形式,生意的主体都是集体或国家,而个体间是绝对不允许的。当然,这篇小说探讨的不是改革开放后经济生活的活跃,不是在呼唤新的市场经济,而是描写台儿沟的年轻人对新生活的追求。不要小看姑娘们所挽回的那些物件,它们和火车一样,代表的是新的世界,新的生活方式,甚至,是新的文明。应该看到,作家对物件的选择是非常细心的,以凤娇为代表的小伙伴们好像对城市生活中的日用品与装饰品更感兴趣。一开始她们还是一帮好奇的看客的时候,透过车窗看到的就是妇女头上别着的金圈圈,比指甲盖还小的手表。不能轻看凤娇们的眼光,更不能以一句“俗气”可“物欲”就为这群小山村的姑娘们定了性。也依然要回到当年。如果不是改革开放,凤娇们是不会有这样的眼光,也不会有这样的追求的,因为也就是几年的时间,人们才给了财富、物质、装饰、美化,甚至身体以应有的位置,而使用这些“奢侈品”的勇者正是年轻人。
当然,香雪与凤娇们确实不一样。当凤娇们在眼花缭乱的车窗后面看到了头饰和手表的时候,香雪看到的是皮书包,她不但和车里的乘客交换物品,还“抓空儿向他们打听外面的事,打听北京的大学要不要台儿沟的人,打听什么叫‘配乐诗朗诵(那是她偶然在同桌的一本书上看到的)”。这是香雪与凤娇们的区别,因为香雪是台儿沟唯一考上初中的人。这里,要特别重视作品中的一个意象,那就是自动铅笔盒。这个意象在作品中几乎是与火车一样重要的意象,它不仅是一个文具用品,不仅代表城市、代表先进的工艺制造,更具体地象征了香雪对一种明确的理想与生活方式的追求,那就是知识。同桌的塑料文具盒使她意识到了自己的贫穷,意识到了台儿沟的“土”,但当她在火车上看到了自动文具盒,并想方设法要得到它,乃至勇敢地跳上火车,直至为用四十个鸡蛋的代价去换它而误了下车,在黑夜地走了三十里地的时候,情形就不一样了,它承载了香雪太多太多的青春情怀与人生理想。
这是一个宝盒子,谁用上它,就能一切顺心如意,就能上大学、坐上火车到处跑,就能要什么有什么,就再也不会被人盘问她们每天吃几顿饭了。
这是典型的八十年代的社会心理与核心价值,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人生。可以说,知识,就是八十年代年轻人的宗教。有了自动铅笔盒的香雪仿佛变了个人,她看世界的眼光都变了,她好像第一次看清了她常见的风景,她不但看清了它们,更看到了它们的未来,看到了台儿沟的未来,看到了姐妹们的未来。这是作品最具抒情性的段落,也是小说中香雪的高光时刻。
大山原来是这样的!月亮原来是这样的!核桃树原来是这样的!香雪走着,就像第一次认出养育她长大成人的山谷。台儿沟呢?不知怎么的,她加快了脚步。她急着见到它,就像从来没有见过它那样觉得新奇。台儿沟一定会是“这样的”:那时台儿沟的姑娘不再央求别人,也用不着回答人家的再三盘问。火车上的漂亮小伙子都会求上门来,火车也会停得久一些,也许三分、四分,也许十分、八分。它会向台儿沟打开所有的门窗……
就是在这样的诗意中,凭借自动文具盒,香雪达成了自己的理想,而且,这样的理想又是在同时对社会的美好展望中呈现的。
还得回到凤娇身上。虽然,作者着力塑造的是香雪这一形象,但凤娇身上实在负担了太丰富的内容,香雪是作家理想中的人物形象,所以,铁凝只得将另外许多青春的形象语义放到凤娇身上,这反而成就了这一形象,她更现实,更接地气,也更为丰满可感。除了上面提到的凤娇对物质的敏感外,在她身上,青春情感的萌动是十分显著的性格特征。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几乎全是女孩子,男性形象只有两个,一个是没出场的香雪的父亲,另一个就是列车乘务员,外号“北京话”的小伙子,可以说,这个形象就是为凤娇设置的。没有这一形象,凤娇心中那隐秘的对异性的向往就无从显露,无以表达。小说开始不久,“北京话”就出场了,并被定位为“快乐的男乘务员”,他长得“白白净净”,“身材高大,头发乌黑”,有两条灵巧的长腿。小伙子长得帅,是首都的人,有着令人羡慕的工作,人又好。这样的形象显然很招女孩子们的喜欢。也许因为凤娇有点大大咧咧,也许是凤娇脾气好,所以,伙伴们就拿她和“北京话”开玩笑,其实,这玩笑里实际上藏着许多姑娘共同的情愫。但在作品中,凤娇确实是将自己的情感表露得较多的姑娘,当别人提到这个小伙子的时候,她会不由自主地朝小伙子的三号车厢望去;当别人说小伙子的白是“捂”出来的时候,她会在心里替他抱不平;而在物物交换中,凤娇总会主动找小伙子交易,为了和他呆的时间长一点,凤娇“故意磨磨蹭蹭”,而且,与一般的做买卖不中,她不是想着占他的便宜,相反,总是要多给一点,少拿一点。
她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和他的交往,她愿意这样的交往和一般的做买卖有所区别。有时她也想起姑娘们的话:“你担保人家没有相好的?”其实,有没有相好的不关凤娇的事,她又没想过跟他走。可她愿意对他好,难道非得是相好的才能这么做吗?
这实在是非常美好的情感,它还谈不上是爱情,它只是青年男女发乎自然的两情相悦,是青春期男女非常正常的情感。正是这样的情感,让人觉得生活的美好,觉得友谊的可贵,觉得这个世界让人依赖,值得我们去好好对待。后来我们知道,小伙子已经有了爱人,不知凤娇知不知道,不过知道了又怎么样呢?男女之间难道除了爱情就不能有其他的情感吗?
这确实是一篇青春叙事,自我意识,青春理想与青春情感,组成了台儿沟姑娘们一段青春人生,更形象地写出了一段青春中国的故事。几十年过去了,如果台儿沟還在,那从她身边呼啸而过该是高铁动车了吧?香雪们也早已长大,她们此后的人生又是怎样的故事呢?
汪政,著名文学评论家,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