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温州和温州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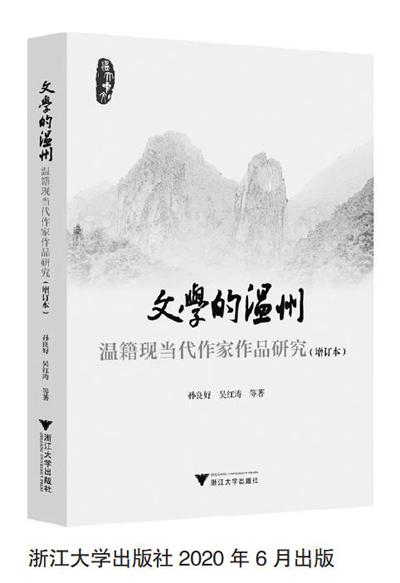
精彩温州
午夜时分抵达巴黎,一位素未谋面的温州朋友到机场接我。花都经过一天的狂欢,已睡眼惺忪。街道寂静,只有很少的车子在寂寞中疾驶而过。朋友热情用车领我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兜风。从协和广场到凯旋门,放射形的街道花一般地展开。朋友自豪地告诉我,温州人几乎包揽了世界时装之都的服装市场。说是“几乎”,是因为那些高端的、传统的名牌是不可替代的。朋友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出色的温州人。这是我这次来到巴黎第一個夜晚的第一个感受:温州人聪明、能干,他们的足迹遍布天下。
想起我有几双皮鞋,都是温州的朋友买来送我的。朋友告诉我,质量无可挑剔。我一直珍藏着,舍不得穿。我还想起,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大潮,温州在全国领了风气之先。随后的房地产热,温州的“炒房团”,让京沪的地产市场顿时热腾起来。温州人会理财,所谓的“炒”,其实就是让多余的资金流动,从中获益,社会因这种流动而充盈活力。改革开放中,他们的无畏和智慧让国人为之气壮。
此刻放在我案前的书稿,是论述温州文学的一部专著。主撰孙良好先生特请我们关注被“商”海淹没了的温州的“文”名的事实:“当代温州以商著称于世,‘文名为‘商海所淹没,不太引入注目。其实,拨开‘商的层层迷雾,温州的‘文也称得上光彩夺目。”(孙良好:《文学的温州·小引:关注“商”海中的“文”名》)孙教授所言正是,是温州人的聪明才智造就了温州经济的繁荣,又因经济的繁荣而促进了此刻书中记载的文学层面的,亦即精神层面的丰裕。温州因勤勉与才智而精彩,温州到底是精彩的。
哲学经典告知我们,人类的进步是由于人类以其智慧和勤劳创造了物质财富,在物质丰裕的基础上,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得以飞腾,从而生发出并创造了社会的文明。我们回顾温州的历史得知,正是作为基础的经济的繁荣,创造了文学的、艺术的、精神和意识形态的精英文化。古往今来,温州文学艺术的繁盛,正是由于他们的这种创造和积累,从而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上建构了丰饶的文明——关于建筑的、绘画的、音乐的,以及关于文学的一切成就。
午夜巴黎街头的一次相遇,与精明的温州入夜游中的晤谈,以及联想到此际案头上温州学者的书稿,启发了我:勤劳的温州、财富的温州,创造了精彩的温州;一个城市和一个地区的历史天空,因此出现较之物质的丰裕也更久远、更灿烂的精神的、文化的彩虹。
诗性温州
从我的家乡福州溯闽江北上,武夷山脉绵延于闽浙赣三省边界。武夷山、太姥山、仙霞岭,满目绮丽,一直延伸到瓯江之滨,在此接上了秀美俊逸的永嘉山水。瓯江在温州城边画了一道弧线,捧出了一座诗之岛——江心屿。浩然楼屹立江中,纪念的是孟浩然,还是文天祥?不得而知,主人也莫衷一是。但历史曾经的足迹是真实的,江心屿的月光让我迷恋也是真实的。温州周遭,秀山丽水让人目迷,我寻找过梅雨潭的绿,那是朱自清先生数十年前的“叮嘱”。当年少不更事,书本中相遇的美丽却是永存于心,直至那年,挚友相伴临潭赏翠,这才遂了心愿。
永嘉山水,世所闻名,楠溪婉转,雁荡风流。美景依稀,与别处不同的是,它的山情水意,总与诗文雅致相伴,从而得以传扬。人们展识温州,总能在秀丽的山间水涯遇到赏识并揭示这山水之美的贤者和智者。历史因这种相遇而绚丽。史载,王羲之、孙绰、谢灵运、颜延之、裴松之、萧逸、王筠、丘迟,都当过永嘉郡守。(《温州府志》)史书曰:“尝考自东晋置郡以来,为之守者,如王羲之之治尚慈惠,谢灵运之招士讲书,由是人知自爱向学,民风一变。”([明]任敬:《温州府图志序》)温州的历史铭记着能识其旷世之美的诗人,谢灵运和王羲之是温州的骄傲。
温州到处留有谢灵运的行迹。九山之冠的积谷山有谢公岩,相传岩上所留墨迹乃是康乐(康乐即谢灵运)所书。谢灵运是中国山水诗的鼻祖,他的诗歌灵感来自温州的秀美山川,他与这里的自然风景朝夕相处,乐不知返,信笔所书,山光水色跃然笔墨间。郡人为他的离去怅惘,“康乐乘舟从此去,何时再见谢公屐”!温州人怀念这位诗人太守,修谢公池,建康乐坊,筑池上楼,都为了那惊天动地的一池春草!
近世温州以财富闻名,却是轻忽了它绵远的诗意。当年郡人说到王羲之,更是深情绵邈。传说右军当年,公余休闲,登舟游塘河赏荷,有诗曰:“时清游骑南徂暑,正值荷花百里开。民喜出行迎五马,全家知是使君来。”这首诗写的是右军当年清兴,时人与之同乐的情景。羲之当年为永嘉守,“庭列五马,绣鞍金勒”([宋]祝穆:《方舆胜览》),每出行,五马临街,气象巍峨。今日温州,五马街、五马坊、墨池坊的地名犹存,可见郡民思念之深。
为了寻觅诗情温州,我曾多次登临浩然楼眺望瓯江烟云,在那里与诗朋文友畅话池塘春草;也曾漫步五马街,于灯火阑珊之间怀想右军兰亭风采。楠溪江畔渔歌,雁荡山间丽影,有人相依月下,有人合掌峰前。清风明月,塘河莲香,总令人不由自主地联想金陵城里乌衣巷口的野花和堂前燕子。温州毕竟是多情的、诗性的。温州是一曲悠远的歌谣。
文学温州
温州因它的历史和现实的渊源,因它特殊的、有别于其他地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而创造了它独特的文学和艺术。我读《文学的温州》书稿,字字句句跳进我的眼帘和心头的,都是亲切,都是深情。此书上编列唐浞、莫洛、林斤澜三家。莫洛先生诗名远播,神往久之,却是无缘当面聆教。记得早年在家乡读书,初中生,狂爱诗歌,知道森林诗丛有莫洛的《渡运河》,但囊中羞涩,买不起,只能在唐浞的长篇诗论《严肃的星辰们》中寻找诗家足迹,想见诗家风采。
我当年神往唐浞的诗论,他的开阔和文采令我着迷。当时我尚未读到他的诗作,幻美的旅者是后来的认知,更不知他的十四行诗和长篇叙事诗的辉煌。我承认,唐浞先生是我从事诗歌批评的启蒙者,我的诗歌批评的兴趣乃至行文风格、我的批评的灵感都受到唐浞极大的启发。可以说,我是学着他的批评方法一路走过来的。20世纪40年代后期,我开始读他的作品,也只是遥遥地念想。20世纪80年代我与“九叶诗人”中健在的八位建立了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其中就有唐浞先生。
我与林斤澜先生是北京作协的“同事”,也是亲切的朋友。那年他在家乡小住,我与他相会于瓯江之滨,并一起去医院看望病中的唐浞先生。我喜爱林斤澜的作品,短篇和散文,都喜欢。他早期的小说《台湾姑娘》《新生》,以及他的杂文和散文,都默记于心,且偶有引述和评论。我和林斤澜同属于北京作协,我们常在一起开会,他也常来北京大学。来北京大学,我们会一起去拜望吴组缃先生。斤澜善饮而不醉,饮时满面春风,我多陪他。我们不仅是文友,也是酒友。
《文学的温州》是一本关于温州文学的史传之书。著者汇集,研讨、检索,历数年课堂讲授、专题研习之功定编。全书精心选取温州文界前辈以及后学,并诚邀青年才俊入传。全书资料丰沛,结构疏密有致,涵盖赅备,论述中肯,足显学术涵养之深。此书于我,除闽浙地缘接近,因“风月同天”而倍感亲切之外,书中列举诸家(除琦君先生外),与我多有不同程度的交往攸关。其中年寿最长者,应属夏承焘先生。我有幸与夏先生亦有一面之缘。
记得那年,是北大陈贻掀先生邀请夏先生造访燕园,我奉命陪侍。先生曾以《瞿髯词》一书赠我,此书我珍藏至今。今读书稿,夏先生部分,其间《玉楼春——陈毅同志枉顾京寓谈词》令我眼前如显电闪:
君家姓氏能惊座,吟上层楼谁敢和?辛陈望气已心降,温李传歌防胆破。
渡江往事灯前过,十万旌旗红似火。海疆小丑敢跳梁,囊底阎罗头一颗。
词作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其时天下平和。夏先生当然读过陈毅元帅的名篇《梅岭三章》,我想他们不仅彼此心倾,而且是彼此心折的。当日国内气氛轻松,元帅与词家对坐论词,此情此景,令人神驰。
永嘉者,永远嘉好之意也。永远嘉好的岂止是山水,岂止是勤劳和精彩丰裕,岂止是文学艺术的鼎盛!永远嘉好的是一派自古而今、继往开来的文脉。
2020年6月12日
北京疫控调低等级,艳阳满天
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作者:谢冕,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首任院长。著有《文 学的绿色革命》《中国现代诗人论》《新世纪的太阳》《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1898:百年忧患》等专著十余种。
编辑:张玲玲 sdz110803@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