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张岱
安冬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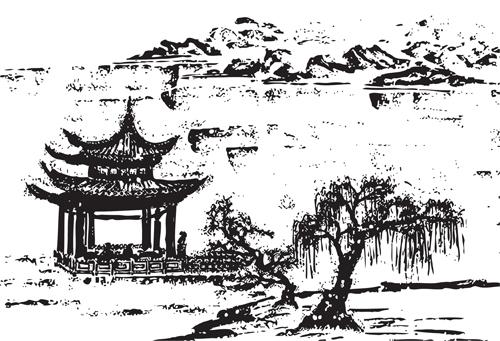
在一场栋笃笑演出中,黄子华拣出李小龙电影里一句话来,这句话是:“我读的书少,你不要骗我!”(我读得书少,你唔好呃我。)他自然是讽世,说可以把这句话用在要考自己的老师面前,用在卖水果的小贩面前,用在开会的人大代表面前……想起这句话,却是因为刚刚读了一些张岱的文字,忽然生出受骗之感。自然,这话不是问张岱,问的是我自觉上了其当的一些人。
想当初,我也买过《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夜航船》,翻看下来,感觉平平。或许之前看多了赞美《湖心亭看雪》如何晶莹,《西湖七月半》如何微讽,以及“且让小僧伸伸脚”的笑谑,“扬州瘦马”的风俗,胸中横着一道梁子,再去看书,见到的仍是不无卖弄趣味的腐儒一枚。所谓闲适,所谓性灵,所谓自嘲,原来不过口味调试得好的山西果醋。我知道,林语堂喜欢他,这是自然;我知道,周作人推崇他,那可不就是因为这人也是“个人本位”么,恰好能当“言志派”的代言人,可以拿来反对载道派的大嗓门。
可是,可是,如今我才发觉,全不是那么回事。我好像是上当了。谁说张岱是言志派,他竟然是如假包换的载道派,只不过是个很讲人情物理、很有趣味的载道派罢了。他看重的文字,不是自己的《梦忆》《梦寻》,而是《四书遇》,是《石匮书》。他说,在明末动荡离乱的日子里,东奔西走,身无长物,只有《四书遇》放在箱底,只字未遗。是啊,这是经解,当然是读书人所宝重的。而《石匮书》则是支持他在山河变色之际活下来的力量,因为写完这部三十岁就开始准备的史书成了他的生活目标。他怎么会变成“闲适”和“性灵”的“个人主义代表”了?
张岱编过《一卷冰雪文》,他在序言里感慨文章的知者难遇:“特恨遇之者不能解,解之者不能说。即使其能解能说矣,与彼不知者说,彼仍不解,说亦奚为?故曰:诗文一道,作之者固难,识之者尤不易也。”很遗憾,他自己就碰上了这种情况。 “遇到”他、喜欢他、鼓吹他的人,竟然是“不能解”的,比如林语堂,鲁迅就讽刺林氏整理的《琅嬛文集》连句读都不通,“连文章也看不懂、点不断,如果选起文章来,说这篇好,那篇坏,实在不免令人有些毛骨悚然”(《“题未定”草》)。
那么周作人也是“不能解”的人吗?这个我倒懷疑。周作人实在不会属于连句读也“点不断”的那类,他一个劲儿鼓吹张岱的诙谐,而且鼓吹那些记“国破家亡之痛之作”的“诙诡”(《再谈俳文》),到底是什么缘故呢?难道一向读书作文严谨的他,一时大意,误读了张岱?
翻检周作人论及张岱的一些段落,发觉并非如此。他论及张岱,固然不提《四书遇》《石匮书》,略过《于越三不朽图赞》,但是,他承认《梦忆》《梦寻》是记载“国破家亡之痛之作”。承认是承认了,话风一转,马上接着就说“文特诙轨”,举出例子,然后就此得出“游戏就是正经”的为文艺而文艺的文学观(《再谈俳文》)。他大谈张岱文章的趣味,说《陶庵梦忆》是遗民的感叹这一流文字之佳者,“而且追怀者又是明朝的事,更令我觉得有意思”。为什么有意思?周作人生怕“遗民”二字引人多想,赶紧说,这可不是自己有什么民族革命思想,只不过不喜欢清朝人的辫子罢了。他当然看到张岱的遗民心迹,知道《明遗民传》里说张岱“衣冠揖让,绰有旧人风轨”,但他赶紧说,这说明张岱文章洒脱出乎性情,不是装出来的。
确乎不是装出来的。遗民的日子不好过,曾经锦衣玉食笙歌度日的张岱半百之后躲入山中,躬耕写作,不仅面临食无米、灶缺柴的困窘,面临出仕后境遇改善的诱惑,还面临着被逼出山的威胁。这些,他都度过了,还写诗劝儿子不要应试。在顾炎武、黄宗羲的子侄门生都不免出仕的对比下,张岱可谓毫无愧色,一尘不染,也应得他所佩服的“冰雪”气质。
这些,周作人当然不会毫不知情。他之所以明明熟悉张岱的《三不朽图赞》却不大提及,当然跟他一向反对“节义”、反对“载道”是一致的。他就更不会提张岱早年还写过《古今义烈传》,张岱诗句吟咏的都是荆轲、渐离了!如此说来,这倒应了《一卷冰雪文序》中“解之者不能说”的说法,或者是“不肯说”吧。有些说,有些不说,故意描绘一个不完全的人来给读者看,这个,不就是要让读者上当吗?
看周作人弟子沈启无编《近代散文抄》,始而叫做《冰雪小品》,这应该是从张岱那里来的典故,然而最终还是叫了“近代散文抄”,莫不是怕读者深究“冰雪”的涵义?在这个选本里,入选篇目最多的人就是张岱,其次是袁宏道。可是入选的文章里,偏偏没有《一卷冰雪文序》,也就没有了张岱对“冰雪”品质的赞美和申论,入选的却是《一卷冰雪文后序》,取的是他的诙谐——为什么文选里有诗呢?“他读的书多”。或取或舍,倒是有趣。他怎不知两下合在一起,才是张岱。“解之者不能说”罢了。
“我读书少,你不要骗我。”这话也很可以问向一些文人,只可惜这些人不是“不辩解”,就是不以己非。真是令人气闷。解决的方式无他,只有多读点书,而且如鲁迅所说,不相信“选本”和“摘句”。
——《四书释注》读后
——以《陶庵梦忆》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