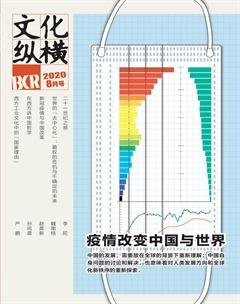上下联动:全球化的“义乌模式”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全球化争议
近年来,曾经大力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欧美发达国家政府在经贸问题上集体转向保守主义,主张贸易保护、设置贸易壁垒、架空推进全球自由贸易的国际组织。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又加重了人们对逆全球化的担忧。作为上一轮全球化浪潮的受益国之一,中国承接了大量发达国家外包的产业,而这些国家产业回归的口号使得中国制造面临重大挑战。
如果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政策继续深化,我们应当如何应对?事实上,除了我们一般讨论的政府、跨国企业和国际组织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from above)之外,还存在大量源自草根的商人利用小额资本从事全球贸易的商业活动,它们构成了全球化的另一种模式,即“自下而上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from below)。这些草根商业力量在政府、跨国企业和国际组织等上层组织的漠视甚至打压下(尤其出现知识产权、税务、外籍商人非法居留等法律问题时),仍能表现出不息的生命力,说明它们具有相对于官方组织及其主导的全球化模式的独立性。甚至有学者指出,它们的商业实践会创造出新的全球贸易规则。[1]
本文试图以浙江省义乌市的跨境电商贸易为例提出第三种类型的全球化模式,即中小企业构成的民间商业力量和部分上层组织合作促成的一种“上下联动的全球化”。具体来说,这一全球化模式可以分解成两个维度,包括中小跨境电商企业与政府的合作关系,以及这些企业与跨境电商平台的合作关系。在前一合作关系之中,各级政府为中小企业提供配套的产业政策和线下基础设施,中小企业则负责扩大出口规模、活跃地方经济。在后一合作关系中,跨境电商平台为中小企业提供网络交易市场、技术服务等线上基础设施,企业在购买平台服务的同时也活跃了网络交易市场。[2]这一模式区别于完全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全球化”模式之处在于,它的核心驱动力仍然来自民间,是基于草根商业力量自身逐利需求而建立起来的。而它区别于仅限于草根的“自下而上的全球化”模式之处在于,它吸纳了政府、跨境电商平台这些上层组织的参与,在动员整合更多推进全球化力量的同时,避免了“低端全球化”(low-end globalization)的标签及其潜在的污名。[3]笔者认为,在后新冠时代部分国家政府与民众放弃或阻碍全球化时,这一上下联动的贸易形态仍有一定的能力推进和维系当下的全球化进程。
新冠肺炎疫情前跨境电商如何推动全球化
2015年2月至2016年3月,笔者在浙江省义乌市调研当地的电商产业发展及其对从业人员日常生活的影响。义乌以商贸立市,拥有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也是得益于批发市场带来的货源、人员、交通和信息优势,该市在近十年内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电商产业基地之一。截至2018年,义乌的电商从业人员人数逾20万,内贸网商密度位居全国第一,外贸网商密度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深圳),外贸网商账户数总计超12万户。[4]2017年全年跨境电商的交易额近747亿元,跨境快递日均发货量超120万单。[5]电商产業集聚产生的巨大效益使得义乌名列由发改委和商务部批准创建的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名单中唯一的县级市,亦成为全国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试点城市之一。

每年“双十一”对于义乌电商来说都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笔者在义乌当地调研时总计采访了106位卖家,其中有5人专门从事跨境电商贸易,另有10人兼及内贸和跨境电商,所涉的跨境平台包括全球速卖通、eBay、亚马逊、Wish、敦煌网等(义乌当地也有少数自创跨境电商平台的企业,但笔者未能找到渠道采访)。2018年7月至10月笔者又到义乌回访,跨境电商此时已成为当地新的经济增长点,纳入了政府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规划,一些卖家集聚的村庄也开始打造“跨境电商村”。在中美贸易战引发的逆全球化大背景下,笔者意识到这一群体实际上是一股推动全球化的草根商业力量,通过互联网将中国制造的小商品销往世界各地,促进了全球商品贸易的联动。他们的商业活动大体符合先前学者对驱动“自下而上全球化”商业力量的定义,即资源相对有限的商人用小额资本进行跨境商品交易,并且这些交易往往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展开。[6]
首先,笔者在义乌遇到的跨境电商卖家大多经营着中小规模的企业,缺乏雄厚的经济资本。经济实力决定了他们销售的产品主要是没有品牌的廉价小商品,同时这也影响到了他们对销售平台的选择。尽管也有卖家在亚马逊、eBay等欧美电商平台上开网店,但更多的人选择了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跨境电商平台全球速卖通(简称“速卖通”),该平台相比于欧美平台的主要优势是网店运营成本较低,操作也较为简单。2015年12月之前,该平台不收取入驻费,所以初做跨境电商的卖家都会选择它试手。2015年12月之后,它开始收入驻费,但价格仍比其他平台低。吸引卖家使用速卖通的另一个因素是它的后台界面基本复制淘宝网店的后台。鉴于许多卖家是从内贸电商转行跨境电商,或者兼营两者,这种操作上的相似性便利了他们的网店运营,减少了平台转换的额外成本。

阿里巴巴速卖通是义乌商家首选的跨境电商平台
另一方面,平台的选择也决定了这些跨境电商卖家的交易对象。亚马逊、eBay等平台的主要市场在欧美发达国家,而速卖通的三个最大市场依次是俄罗斯、美国和巴西,其中两个是发展中国家。此外,白俄罗斯、乌克兰、土耳其、智利、阿根廷、哈萨克斯坦等发展中国家也是该平台的主要客源国。具体到这些国家的网购群体,鉴于速卖通走的是低价路线,其消费人群通常也是廉价商品的追逐者,为此他们甚至可以忍受三个月乃至更久的货运时间。这些特征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其网购群体大多是发展中国家(以及部分发达国家)的中下阶层。在具体交易环节,由于速卖通免费提供网页翻译服务,语言并没有成为买卖双方交流的障碍。不懂外语的卖家可以使用翻译软件和顾客交流(通常用英语),翻译的精准性也不是问题,正如不少卖家提到:“很多顾客的母语也不是英语,用词和语法都有问题,但双方都觉得看得懂就好,反而更容易达成交易。”就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中小卖家通过跨国网络渠道,将廉价商品销售给另一些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的中下阶层消费者,这个存在于大宗国际贸易之外的商业链条以其独特的方式推动着贸易全球化的进程。
但这一电商贸易的全球化并不仅靠卖家的冲劲,没有跨境电商平台提供的线上基础设施和地方政府提供的线下基础设施,[7]绝大多数的卖家没有独立的技术资本成为全球化的驱动力,毕竟他们的生意不像很多非洲商人那样可以通过人肉带货的方式进行跨国交易。[8]也是因为他们需要与跨境电商平台以及中国各级政府这些推动全球化的上层组织密切协作,最终交织成为上下联动的全球化。
首先,跨境电商平台在全球市场的推广活动为义乌(以及更广泛的中国)卖家和海外买家之间的商品交易打下了基础。亚马逊和eBay这些欧美电商平台企业在西方社会的影响力自不必说,速卖通所属的阿里巴巴集团在世界各地进行线上和线下推广的工作也卓有成效,令不少国家的民众了解到了这个来自中国的电商巨头和它平台上价廉物美的商品。以东南亚为例,除了推广速卖通,阿里还控股了该区域最大的电商平台Lazada,将淘宝的英文版植入该平台中,当地的消费者不用懂中文就可以在淘宝下单,通过阿里旗下菜鸟物流的跨国网络将货物运送到消费者手中。[9]在越南某些交通不便的乡镇,阿里平台在当地的代理人与政府部门、物流企业合作修建了转运中心。在马来西亚的部分地区,消费者可以直接在当地的7-11便利店领取他们跨国网购的商品。而在菲律宾,加油站变成网购商品的转运中心,当地的快递员从这里领取货物派送给消费者。为了更好地培育东南亚的网络消费市场,提高网购的基础设施水平,阿里还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新建了大数据中心,利用Lazada建立起类似支付宝的互联网支付系统。[10]从物流转运的硬性基础设施到数据采集分析、线上交易支付这些软性基础设施,跨境电商平台的业务扩张极大地助力了中国电商卖家的全球商业拓展。
其次,义乌跨境电商的贸易全球化也与中国各级政府积极推动出口贸易的努力紧密相连。2011年,义乌获国务院批准成为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城市,跨境电子商务就被列为发展重心之一。2018年,该市又获批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国务院和浙江省政府要求下属部门对该市跨境电商的物流、仓储、通关等方面进一步简化流程、精简审批。例如海关允许跨境电商企业按月集中申报出口商品清单,这一做法极大地便利了后者的通关流程,提高了它们的发货效率。义乌当地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优惠举措,包括给一定规模的跨境电商企业减免税、提供办公场地、财政补贴和商业贷款等。对于中小规模的跨境电商卖家而言,当地政府设立了10亿元的跨境电商产业基金和1亿元的电商风险补偿基金,用于扶持初创期的电商企业发展。此外,当地政府还承诺加强对跨境电商行业人员的技能培训,对跨境电商人才的服务保障(包括住房和子女教育方面的优惠政策),以及对纳入海关贸易统计的跨境电商企业每出口1美元给予0.04元人民币的奖励。[11]这些利好的政策某种程度上解决了跨境电商卖家的后顾之忧,也激发了他们将生意做大做强的信心。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跨境电商的危与机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极大地冲击了我国的外贸出口。作为外向型城市的代表之一,义乌2020年第一季度的外贸出口总值仅有510.3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了14.7%,但这已是当地政府和企业争取时间复工复产的结果。[12]笔者在回访这些熟识的跨境电商卖家时了解到,那些留在义乌过年或在2月中旬义乌打响复工复产号角后返回的卖家还赶上了一波出口的机会,但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跨境生意处于停滞状态。这种状况令许多卖家感到沮丧,但同时也迫使他们思考未来的出路。有的卖家开始全面转向内销;有的则一方面利用内销去库存,另一方面积极寻找新的跨境电商形式,为疫情结束后继续外贸生意做好准备。跨境直播营销是他们想到的新形式之一,有卖家就找来了疫情期间滞留义乌的外商和留学生,通过他们在其来源国的直播平台上进行产品营销,吸引粉丝。这一做法通过当地媒体的报道被更多的外贸商家所借鉴,直播活动最后甚至开进了批发市场,成为市场管理层尝试破解当前外贸僵局的武器。
外销渠道不畅只是疫情期间跨境电商卖家面对的一个困难,有订单难发货的情况更令他们头疼。笔者访谈过一位在疫情期间转售防疫用品的卖家,疫情在国外暴发后他的网店陆续收到零星的订单,但由于平台的海外仓无法入库,自己找跨境物流发货成本又太高,最后他不得不让顾客取消交易。这一困境的背后是以空运和海运为主的全球物流体系的停摆,疫情对这两种航运方式的冲击已经有目共睹。各国航空公司和海运公司暂停航线的措施直接导致了物流运输的大范围中断,所剩无几的运输仓位费用高企,跨境电商卖家因此不得不面对物流成本的急剧上涨。即便他们愿意付出高价发货,顾客所在国后续的派送也会成为问题,因为不少国家国内的物流系统也受疫情影响而停摆。有卖家就曾遭遇货物到了目标国家,物流信息便不再更新的窘况,顾客也没有收到货,买卖双方都不知道包裹在哪里。
常规物流运输停滞的难题迫使人们开始寻找替代方案,地方政府和地方国企也尝试利用自身的资源帮助外贸商家突破物流瓶颈。笔者了解到,从4月中下旬开始,义乌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拓宽国际航空物流通道的举措,市财政将补贴愿意在义乌机场开通临时货运包机的中方承运企业,同时也将奖励使用上述临时包机发货的本地或外地来义务发货的外贸企业。义乌陆港集团等地方国企也积极对接各方物流公司,为其下辖跨境电商产业园区内的企业争取发货渠道。例如4月下旬,它们租用了一架飞机承载2.5万件跨境包裹,从杭州萧山机场飞往比利时,然后由比利时邮政物流将货物转运至德国、法国、荷兰等欧洲国家。然而更值得关注的还是从义乌始发的“义(义乌)新(新疆)欧(欧洲)”铁路班列,这条基于“一带一路”倡议发展起来的运输通道在疫情期间成为部分跨境电商企业产品外运的生命线,同时也部分缓解了铁路沿线国家生活和防疫物资不足的压力。从2020年1月1日至4月21日,“义新欧”班列总共开行116列,发运9692标箱,同比增长了39.25%。[13]在空运和海运通道几近全线停摆的情况下,具有运量大、运费低廉、人员接触少等优势的跨国铁路运输实现了逆增长,让原本因疫情隔绝的各国重新互通互联。也是借助此次跨国铁路运输崛起的契机,中国邮政浙江各级分公司开始将义乌作为全省乃至全国对欧洲运邮的转运点,依靠“义新欧”班列实现规模化和常态化的输送。[14]这一举措无疑会对未来义乌跨境电商企业的对欧贸易产生积极的影响。
而在跨境电商平台的层面,尽管亚马逊、eBay等也因疫情影响陷入了半瘫痪状态,产品入库和物流派送效率大打折扣,但阿里巴巴旗下的速卖通平台却逆风而起。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指出,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给阿里巴巴提供了加速实现全球商业扩张的机会。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外疫情暴发后,各国的消费者很难在本地商场和亚马逊、eBay等电商平台上购买到防疫用品,于是他们将目光转向来自中国的速卖通。另一方面,速卖通背靠“中国制造”完备的产业链,尤其是国内疫情控制住之后中国企业快速的复工复产,这为其他国家的防疫工作提供了紧缺的物资。《金融时报》援引第三方数据指出,在西班牙和意大利,速卖通今年第一季度的客流量分别同比增长了20%和14%。在巴基斯坦,當地人已经开始从速卖通上购买口罩,然后以翻一倍的价格在线下转售。国外用户的急速增长令阿里巴巴及其合作伙伴对跨境电商的前景充满信心,并以淘宝网在“非典”疫情后占领中国市场的胜举类比此次速卖通平台在全球市场的崛起。[15]尽管笔者访谈的15名卖家中暂时没有人直接受益于这一波速卖通的全球扩张,但笔者通过他们了解到义乌跨境电商行业内确有商家因此受益。更重要的是,他们中的不少人相信如果自己能度过眼前的困境,疫情之后的跨境电商会风潮再起,甚至更甚于前——这不仅是因为平台的全球用户更多了,在经历疫情之后更习惯网购了,还因为他们认为后新冠时代如果出现全球范围的消费降级,那么义乌价廉物美的小商品也将更受欢迎。

疫情期间,“义新欧”班列成为跨境电商产品外运的生命线
结语
义乌跨境电商行业在疫情前和疫情中的实践显示,发展中国家的中小企业利用小额资本从事的全球贸易同样也能推动全球化的进程,并且在中国各级政府和跨境电商平台的支持下,形成了“上下联动的全球化”模式。在后新冠时代部分发达国家的政府与民众放弃或阻碍全球化时,“上下联动的全球化”模式基于全球市场需求的贸易形态仍会在一定程度上推进和维系当下的全球化进程。目前,虽然有不少学者用历史经验、经济规律和理论模型来论证全球化是不可逆的、目前的悲观情绪不会成为现实,[16]但这些经验与规律毕竟来自遥远的过去或抽象的推演,而本文所贡献的,是呈现了全球贸易链条中的一个个商人是如何用一笔笔订单维系全球贸易的运作的。
(责任编辑:王儒西)
注释:
[1] 温美珍:《国际小商品贸易中的信用体系建设:义乌的实践》,载《文化纵横》2019年第6期。
[2] 各级政府和电商平台之间也有非常复杂的合作关系,但鉴于本文关注的重点是基层的中小跨境电商企业如何与上述上层组织合作推动全球化,这里暂不讨论政府与平台之间的关系,相关的讨论参见Min Tang, “From ‘Bringing-in to ‘Going-out: Transnationalizing Chinas Internet Capital through State Policies,”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13, no.1, 2020, pp. 27~46.
[3] Gordon Mathews and Yang Yang, “How Africans Pursue Low-End Globalization i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vol.41, no.2, 2012, pp. 95~120.
[4] 曹晓蓉:《义乌获批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载《义乌商报》,2018年7月14日第1版。
[5] 曹晓蓉:《义乌电商年交易额首破2000亿元》,载《义乌商报》,2018年1月26日第4版。
[6] Gordon Mathews and Carlos Alba Vega, “Introduction: What is 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In Gordon Mathews, Gustavo Lins Ribeiro, and Carlos Alba Vega eds., Globalization from Below: The Worlds Other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2012, p.1.
[7] 钱霖亮:《电商经济是虚拟经济吗?——物质文化视野下的电子商务》,载《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
[8] Gordon Mathews, Linessa Dan Lin, and Yang Yang, The World in Guangzhou: Africans and Other Foreigners in South Chinas Global Marketpla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pp.81~87.
[9] 钱霖亮:《电商经济与中国软实力》,载《文化纵横》2019年第5期。
[10] Jane A. Peterson, “A Showdown Brews Between Amazon and Alibaba, Far From Home”, The New York Times, 22 October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10/22/business/alibaba-amazon-southeast-asia-lazada.html.
[11] 义乌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跨境电子商务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的若干意见》,http://www.yw.gov.cn/11330782002609848G/a/04/02/201612/t20161201_2859327_2.html。
[12] 方静:《3月义乌进出口实现恢复性反弹》,载《金华日报》2020年4月23日第8版。
[13] 龚书弘:《跨境电商单日出口票件量创历史新高,义乌是怎么做到的?》,中国义乌网,https://news.zgyww.cn/system/2020/04/24/010185500.shtml。
[14] 浙江省邮政管理局:《首趟“中国邮政号”中欧班列(义乌—马德里)启程》,浙江省邮政管理局官网,http://zj.spb.gov.cn/dsjxx/202003/t20200330_2071230.html。
[15] Ryan McMorrow and Nian Liu, “How a Pandemic Led the World to Start Shopping on Alibaba,” Financial Times, 28 April 2020, https://www.ft.com/content/4b1644b1-aeee-4d02-805a-c3ac26291412.
[16] 姜跃春、张玉环:《新冠疫情不会中断经济全球化进程》,载《世界知识》2020年第7期;朱云汉:《全球化为什么不可逆——探索新冠病毒危机后的世界》,载《文化纵横》2020年第3期;张蕴岭:《疫情加速第四波全球化》,载《文化纵横》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