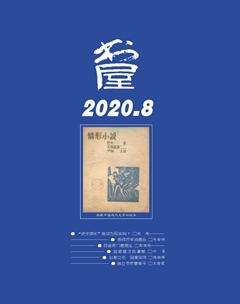诗谶与文谶
甘建华
说起这事儿真有点玄乎。之前,我从不知道李成录何许人也,更没有读过他的什么文章。偶然在网上见有纪念他的一篇小文,称其生前曾任青海省海西州茫崖行委主任、冷湖工委书记,在多家报刊发表过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茫崖、冷湖两地乃我旧时工作、生活的地方,暗中思忖,是否为其在《柴达木文事》一书中留个名字。因其文名并不大,其间诸事缠身,但他好像知晓我的心思,非要挤进这本书,冥冥之中竟以各种方式闯入视线。
2015年5月20日凌晨,李成录忽然托梦于我,将海西州群艺馆馆长乌席勒微信指点一下,倏忽不见踪影。猛然惊醒,想那蒙古族人乌席勒我也不曾见过,只是早几天应邀给即将创刊的《德都蒙古》杂志发去一篇文章,州文联负责人告诉我乌席勒主编的手机号码,双方微信随之开通,但怎么就会这么巧呢?打开乌席勒微信一路查找,见其清明那天有一首短诗悼念李成录,并有李的诗集书影。
李成录生于1963年,海北藏族华热部落人,藏名华瑞·漠然尖措,毕业于青海民族学院汉语系,民族学在职研究生,青海省作协会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进入柴达木盆地工作。2007年出版诗集《瀚海深处孤屋的灯盏》,收入八十六首诗歌及十一篇散文,网上有其《黑夜里我给你写诗》,指明写给其爱人。书名及诗题均为不祥之语,“瀚海深处孤屋”那是什么地方?“黑夜里写诗”那是什么情景?不是坟墓、阴间又是什么?
蓦地想起历代“诗谶”之说,这一中国古代诗歌中特殊的文学现象。诗谶最早出现于魏晋,到宋代已有专门的整理、记录诗谶的诗话、笔记和小说,其内容主要为诗人的生死年寿和仕途穷达,可分为吉谶、凶谶、自谶和他谶四种。《世说新语·仇隙》之一記载的便是最早的诗谶:“孙秀既恨石崇不与绿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礼。后秀为中书令,岳省内见之,因唤曰:‘孙令,忆畴昔周旋否?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于是始知必不免。后收石崇、欧阳坚石,同日收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后至,石谓潘曰:‘安仁,卿亦复尔邪?潘曰:‘可谓白首同所归。潘《金谷集》诗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乃成其谶。”
最著名的一则诗谶则与隋炀帝有关。传说他成功开凿大运河,乘彩舫龙舟下扬州,某日忽得一诗:“三月三日到江头,正见鲤鱼波上游。意欲持钩往撩取,恐是蛟龙还复休。”又作《索酒歌》曰:“宫木阴浓燕子飞,兴衰自古漫成悲。他日迷楼更好景,宫中吐焰奕红辉。”虽然诗写得一般,炀帝却自鸣得意,即刻交付乐工谱曲,令随行的宫女们合唱。然而识者却暗讶为不祥谶语,因为李渊其时已渐成势,“鲤”、“李”二字同音,而前首诗中有李渊化龙之隐喻。后来李渊大军攻入京师,炀帝躲入迷楼自杀,唐兵将迷楼付诸一炬,正应了后诗之句。
唐朝诗人崔曙早岁孤贱,曾在终南山随道士邢和璞学法术,后沦落定居宋州(今河南商丘),曾在少室山读书。殷瑙评其诗“多叹词要妙,情意悲凉,送别、登楼,俱堪泪下”。开元二十六年戊寅科(738),殿试时作《奉试明堂火珠》诗,玄宗看后大为赞赏,取为状元,官授河内县尉。可惜翌年病殁,唯遗一女名星星者,世人皆以为“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是其自谶。
《唐名媛诗小传》载:“薛涛字洪度,本长安良家女。父郧,因官寓蜀。涛八九岁知声律。一日,父指井梧曰:‘庭除一古桐,耸干入云中。令涛续之,即应声曰:‘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父愀然久之。”薛涛后来流落蜀中,为一代名妓,两句诗无意中成了她一生的真实写照。又有《春渚纪闻》载:“建安暨氏女子,十岁能诗。人令赋《野花》诗,云:‘多情樵牧频簪髺,无主蜂莺任宿房。观者虽加惊赏,而知其后不保贞素。竟更数夫,流落而终。”
五代楚王马殷、马希范时,江西廖融避乱不仕,与兄廖凝卜隐南岳衡山,号衡山居士,与逸人任鹄、潘若冲、王正己、凌蟾、王元、杨徽之等为诗友,互有唱和。晚年作诗云:“云穿捣药屋,雪压钓鱼船。”自解曰:“屋破而云穿其中,无人也;船为雪压,无用也。”遂以为不吉之兆,“病之,六十日后果卒”。
北宋绍圣年间,秦观坐元祐党籍,先是发配湖南郴州编管,后贬谪广西横州(今横县)。途经衡州(今衡阳),太守孔毅甫见过他,便对人说:“秦少游气貌大不类平时,殆不久于世矣!”秦观曾写一阕《好事近·梦中作》,内有“醉卧古藤阴下”,仅此一句中谶,后来果真卒于藤州(今广西藤县)。
再说近现代以来各种故实。1926年4月19日,徐志摩发表散文《想飞》,内中有句“到云端里去,到云端里去”,并描述了飞机爆炸的幻想。1931年11月19日,他乘飞机从南京前往北京,途中在济南南郊遇难身亡。郭小川于1975年写了一首《秋歌》,内有不祥的谶语:“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化烟,烟气腾空/但愿它像硝烟,火药味很浓,很浓。”次年10月18日,在河南安阳招待所一楼房间,郭小川服安眠药后入睡,因未灭的烟头点燃衣被窒息而亡。1996年夏天,汪曾祺给云南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褚时健画紫藤并题诗:“璎珞随风一院香,紫云到地日偏长。倘能许我闲闲坐,不作天南烟草王。”本是一时戏言,孰料两年后,年已古稀的褚时健因经济问题系狱。北大教授、著名学者金克木有本专著叫《书读完了》,意思是说无书可读了,不久遽尔离世。他的临终遗言倒是有趣:“我是哭着来,笑着走。”
我将藏族人李成录托梦这则笔记发到微信,引起海内外诸多师友惊悚骇异。青海知名作家王文泸叹息道:“你说的事情确实罕见。为了青史留名,竟然托梦于生人,实在可叹!文人之重名,一至于此乎?而‘诗谶一说,自古屡见不鲜,难以用‘巧合二字做简单解释。清代雍正时期文坛泰斗、吏部尚书尹继善去世前一月,让他的几个儿子做送春诗,幕友解吉庵写的是:‘也知住已经三月,其奈逢须隔一年。遗爱只留庭树好,余晖空托架花鲜。尹尚书大加叹赏,动笔加圈加点。尚书殁后,众人再读,方知无意中写的全是谶语。不管怎么说,既然李成录如此执着,你就满足他的愿望,让他进入《柴达木文事》一书吧!”又接现居海南岛的大学同学凌须斌来电,说是在柴达木盆地工作期间,与李成录是酒友兼文友,熟谙其人其事。李身高一米八○,长相看似粗犷,内心却很柔婉,喜爱诗歌到了痴迷的程度。每当与朋友相聚,浮一大白后必定朗诵自己的新作,以“官员诗人”自矜。2008年夏天赴省城西宁开会,在橡皮山往青海湖之间遭遇车祸身亡。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海西文学现象”一时领青海风气之先,“带头大哥”即是高澍。高澍出自山东曲阜大宅门,祖辈迁居天津卫,叔父即外交部副部长周南。他于196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汽车发动机专业,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发配到柴达木汽车修理厂,介绍信上写着“按工人使用”,于是再次发配到车间当车工。他利用业余时间搞文学创作,短篇小说《琴心》发表于《瀚海潮》1978年创刊号,是青海省“伤痕文学”出现最早的几篇作品之一。改革开放以后,担任海西州文联副主席、《瀚海潮》杂志主编,1987年5月调任州委宣传部副部长、州广播电视局局长。在那个偏远落后的地方,他发下了宏大的誓愿:“办中国地州一级第一流的台站。”孰料新官上任刚满百日,酒后骑自行车回家,刚好撞在一个也是酒后驾车人的汽车上,当场死亡,据说那个司机也畏罪自杀。
青海作家井石告诉我,高澍生前出版短篇小说集《活佛》,内收《活佛》、《新荷》、《急转弯》、《琴心》、《风起了》等九篇,此外发表过中篇小说《漠上》、《隐忧》、《带血的玫瑰》、《淡水湖,咸水湖》等,1986年加入中国作协。还有两篇中篇小说的名字,现在看来极不吉利,中了文谶:一个是《最后的红蔷薇》,在他临去世前发表;另一个赶发出来时人已离世,名为《死亡之吻》。
文谶、诗谶是什么?是所有作家都避之唯恐不及的宿命。试想一下,如果你写了什么,你的命运也注定发生什么,那是不是很恐怖?战国时代,荀子发出“言有招祸也”的警告,其高弟韩非竟以《说难》名篇,首创“逆鳞”之说,指出“因言致身危者七”。秦王嬴政为了得到韩非而出兵攻打韩国,李斯因妒其才而将其谋害,《说难》遂成文谶。《三国演义》第三回写道:“先是洛阳小儿谣曰:‘帝非帝,王非王,千乘万骑走北邙。至此果应其谶。”南宋状元文天祥曾有一篇文如其人、在某种意义上犹如文谶的经义——《事君能致其身》其中说:“委质而为人臣,当损躯以报人主。”似乎看到了若干年后自己的结局。即便元世祖忽必烈亲自劝降,许以宰相之职,文天祥依然大义凛然,宁死不屈。民国时期,章太炎、刘师培与黄侃,三个大学问家,却因行为怪僻而被称为“三疯子”,其中黄侃是章太炎的弟子。章太炎劝黄侃及早著书传世,黄侃却非要坚持“五十之前不著书”。1935年4月3日,黄侃五十岁生辰,章太炎书赠寿联:“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成好著书。”黄侃见联中有“绝命书”三字,大为惊诧。是年10月6日,黄侃由于饮酒过度,胃血管破裂,抢救无效,两天后下世。章太炎因联语成谶,余生痛悔不已。丁玲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风云人物,瞿秋白曾预言她“飞蛾扑火,非死不止”,后来的人生果然几度坎坷荣辱相伴。
1988年7月下旬,诗人海子途经柴达木盆地,写了一首诗《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这是雨水中一座荒凉的城//除了那些路过的和居住的/德令哈……今夜/这是唯一的,最后的,抒情。/这是唯一的,最后的,草原//我把石头还给石头/让胜利的胜利/今夜青稞只属于他自己/一切都在生长/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空空/姐姐,今夜我不關心人类,我只想你。”诗中两次重复“唯一的,最后的”这种极端的表达,意味着海子在这一天失去了一切,失去了诗歌和情感,也失去了创作的天才,剩下来应该干什么,还用得着我们费神猜想吗?果然,翌年3月26日,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戕,从而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
再说吾乡衡阳先贤、世界华文诗坛泰斗洛夫先生,也曾有过文谶和诗谶,而许多研究者迄今都未感觉到。还在十五六岁读初中的时候,洛夫在衡阳《力报》发表散文处女作《秋日的庭院》,却取了“野叟”这样一个老气横秋的笔名。大约是2011年秋天,借其回乡省亲的机会,我曾当面询问他笔名的来由,他笑呵呵地说:“可能是受柳宗元‘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启发,也有韦应物‘野渡无人舟自横的影响。‘野叟就是四野流浪的老汉——可不就是吗?先是从衡阳到台湾,再从台湾地区到加拿大,我现在成了一个失国的老头了。”在洛夫所有的诗歌中,《边界望乡》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曾无数次被两岸的诗评家点评过。1979年3月16日上午,访问香港的洛夫在诗人余光中的陪同下,去关界落马洲遥望内地。“当时轻雾朦胧,我从望远镜中望过去,见到……河山猛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就好像狠狠地被打了一拳。这就是数十年不见、日思夜想而又回不去的……家园吗?耳边响起鹧鸪鸟的啼叫,声声扣人心弦,我当时激动得热泪盈眶。这时才体会到什么叫‘近乡情更怯,什么叫‘有家归不得”。同年6月3日写下诗歌《边界望乡》,表达游子怀乡咫尺天涯的伤痛、落寞和无奈。名句“喏!你说,福田村再过去就是水围/故国的泥土,伸手可及/但我抓回来的仍是一掌冷雾”,“当距离调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一座远山迎面飞来/把我撞成了/严重的内伤”,后来不幸成了诗谶。2009年10月底,省、市、县三级在衡南县城云集镇,轰轰烈烈地举办了首届洛夫国际诗歌节,并为洛夫文学艺术馆、洛夫文化广场奠基,天下咸知,欢欣鼓舞。孰料“萧何们”各贪天功,互相拆台,暗中使坏,致使建好的洛夫文学艺术馆被挪作他用,门前的洛夫文化广场也被强行更名,“成了一场盛大的骗局,令我无颜回乡再见父老乡亲”(洛夫语)。
孙蓉蓉《诗歌写作与诗人的命运——论古代诗谶》一文认为:“诗谶其实不是谶,是读者在对诗歌的别解字句的过程中形成的,其中一些看似偶然的巧合又带有某种必然因素,反映了古代文人对于生命与仕途问题的关切与焦虑。而对诗谶的评论和观点,又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古代诗谶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原因,体现了传统天命论的思想、语言禁忌的影响和‘微言大义的说诗传统的深层积淀。”说白了,诗谶、文谶的主观意识十分强烈,不无偶合、附会和推论,曾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被学界视为“旁门小道”和“怪力乱神”。
在高科技非常发达的今天,人们接受信息更加全面,也愈来愈清醒理智,对于任何事情都能辩证地看待,已不再一味地相信和盲从。《孟子·尽心下》就说过:“尽信书,不如无书。”宋代文学家洪迈《容斋随笔·诗谶不然》亦云:“今人富贵中作不如意语,少壮时作衰病语,诗家往往以为谶。白公(白居易)十八岁,病中作绝句云:‘久为劳生事,不学摄生道。少年已多病,此身岂堪老?然白公寿七十五。”衡南洛夫文学艺术馆和洛夫文化广场,经过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在洛夫先生去世一年多以后,终于被新任县委书记提上议事日程,已经进入装修设计阶段,诗城云集与洛夫先生的名字再度联系在一起。这也印证了清初傅山题画梅诗句——“人力能补天地缺”。
因此,我特别推崇湖湘书法名家何满宗倡导的“写吉祥,颂吉祥”,以“德”“福”“寿”弘扬我们的美好愿景。为了诠释这“吉祥三字”,何满宗又作《吉祥三颂》,分别为《大德颂》、《万福颂》、《长寿颂》。《大德颂》:“君有德,志高洁,仁爱惠恩泽。敬老尊贤礼天下,心镜如秋月。”《万福颂》:“家和谐,人亲切,祥瑞喜相接。欢畅心海长波涌,福源永不竭。”《长寿颂》:“慈悲怀,清风节,善行圣于雪。德润众生无量寿,时空恒飞越。”并有副歌:“寿比南山久,天风颂大德,洪福万民悦。”但愿吾友的《吉祥三颂》,能给天下文朋师友一点启示,并给千家万户带来幸福美满——扎西德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