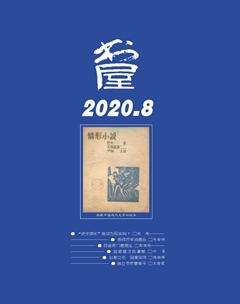陶澍寄梦“野士”左宗棠
徐志频
陶澍与左宗棠这对年龄相差三十三岁的朋友,从“忘年交”到结为儿女亲家,殷勤寄望,相互成全,过程完全是一部写实版的传奇。
道光十五年(1835),陶澍从胡林翼口中第一次听说左宗棠其人,对他作了间接了解,有了些许零碎印象。如果没有后来的见面,陶澍不会轻易肯定左宗棠。
陶澍约见左宗棠,一则出于胡林翼的举荐,二则被左宗棠过人的文才打动了。
举人左宗棠与两江总督陶澍第一次见面,时间是1837年,地点在湖南醴陵邑侯治馆舍。
陶澍返乡之行,本为专门请假回安化小淹给父母扫墓顺带探亲。官轿途经醴陵,醴陵县县令临时安排高规格接待。渌江书院山长左宗棠受县令委托,写下一副欢迎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短短二十六字,既点出了陶澍受道光皇帝两次接见的殊荣,又将其先祖陶侃督八州军事的光辉事迹合情合境嵌入,现实与历史交融,文字超凡脱俗。陶遂引左为知音,结为忘年交。左宗棠自述相识经过:“乃蒙激赏,询访姓名,敦迫延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至于达旦,竟订忘年之交。”
青年左宗棠虽然外见盛气,内藏傲骨,但到底是没见过大世面的乡下小举人,这次被陶澍虚怀若谷的心怀与礼贤下士的风度感动得一塌糊涂。他回去后跟妻子说:“督部勋望为近日疆臣第一,而虚心下士至于如此,尤有古大臣之风度,惟吾诚不知何以得此,殊自愧耳!”用湖南土话说,陶总督功劳大得下不得地,名气大得吓死个人,他如果不是祖坟开了坼,哪里有机会结识这么牛的朋友!
这次邀约见面,为左宗棠在官场内做了个活广告。一年后,两人约定在南京总督府见面,结为儿女亲家。
左宗棠开始被两江总督陶澍有计划、有节奏地纳入到他经营出来的庞大人事关系网。
陶澍在人生最后一刻做奋力一拉。他为什么如此赏识左宗棠?
乾隆四十四年(1779)1月17日,陶澍在湖南安化县小淹乡陶家溪出生。
陶澍的先祖,可以追溯到晋朝都督八州军事、封长沙郡公的陶侃,陶侃的曾孙即广为人知的田园诗人陶渊明。
后唐同光元年(923),为躲避战乱,陶侃后裔陶升,从江西吉州迁来湖南安化小淹乡。元末兵乱,陶升后裔只剩陶舜卿一支,陶氏第十二世祖陶志凤迁到石螃溪定居下来,到陶澍已历十六世。
与多数士子受母亲影响而成长起来不同,父亲陶必铨影响陶澍一生至深。陶必铨生在农家,却是个私塾先生,一辈子除了教书,没干过别的行当。虽然蜷居在偏远安化深山老林,最远也没走出过湖南,但陶老先生志气不小,从他给陶澍的取名便可反映出来:“盖其有以泽苍生也。”寄望儿子恩惠泽被天下百姓,自己当然更希望如此。
陶必铨发奋读书,方法有点特别:同时摆开几桌书,一本一本全翻开,将内容贯通起来,对江吟诵,先背下再作批语,观点“多前人所未发”。有本事同时打开几十本书一口气看下去的陶必铨,桌上摆的都是些什么内容的书籍呢?经学。经学即先秦各家学说要义,汉代独尊儒术后,经学特指儒学十三经:《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榖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宋、明两朝,流行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清军铁骑入关,将沉醉于“修炼心性”的读书人惊醒了。他们怎么也想不通:亿万华夏子民,怎么会亡于只有十五万军队,而且还处于原始状态的满族人手中?处山高皇帝远的大山中的陶必铨痛苦中寻找原因,结论是: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教中国士人“空谈理心,不理实政”,才导致明朝亡国。
清朝初年,顾炎武以思想家的眼界一针见血地指出:“舍经学无理学。”
亡国之耻,理学之痛,让陶必铨读起经学。
大清帝国统治者很快发现,汉族读书人如果攻读经学,势必干预国家政治、经济。为了管住士人的思想,朝廷将理学立为国学。体制内的读书人按着朝廷设计,纷纷进了圈套。陶必铨居地偏远,乃民间教书匠,朝廷风气力不能及。他继续读着经学,说着大话,怀着理想,没有人管。
陶必铨沉醉在经学海洋,对实学“杂书”有着狂热的兴趣。他将经学所追求的经国济世的抱负,寄托到自己与儿子身上。怀着这一梦想,陶澍七岁那年,陶必铨带着他跋山涉水来到岳麓书院。一家之主,本就家徒四壁,陶必铨舍下父母、老婆,带儿子背井离乡求学,困难可想而知。生计成为头等问题。岳麓书院当时规定,学生读书需自己带米,书院每月补贴十钱银子作蔬菜费。这点补贴,养不活父子俩。但岳麓书院还有奖学金制度,每月由巡抚或学政来主持一次月考,考到前三名就能拿到奖学金。对陶必铨来说,奖学金就是求学金。为了能在岳麓书院这座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圣殿里待下去,他不分严寒酷暑,每天坚持读到深夜,因此总能拿到奖学金。
课余,陶必铨就与学友在岳麓山中找块地方,坐下来对酒纵谈,指点天下。小陶澍在边上听,似懂非懂。坚持不到一年,因经济窘迫,家庭难以维持,陶必铨被迫带陶澍回乡。陶必铨已经心满意足,毕竟带儿子去见了回大世面,感受了千年学府的气氛。
回到安化小淹陶家溪,陶必铨操起老本行,教私塾。办私塾有两种:在自家设馆,叫私塾;上门去教,叫坐馆。陶必铨人品好,又是岳麓书院的高才生,有钱人家都抢着请他。他每次坐馆,都对东家要求,带上儿子陶澍。
乾隆五十五年(1790),陶必铨应邀到安化县城(今梅城镇)主持修复南宝塔,陶澍跟随父亲,到安化学宫读书。乾隆五十七年(1792),陶必铨到益阳曾润攀家中设馆教书,陶澍仍跟随在侧旁听,前后四年。陶澍因此跟随父亲,读到许多杂书,包括算学、测量学等技术书籍。这些书籍,为他精通经济打下基礎。
十八岁那年,陶澍参加童试,以院试第二的成绩考取秀才。这年,陶必铨在离家三里远的一个叫“水月庵”的破棚子边住了下来,专心教儿子读书。他不再设馆,也不准儿子设馆,更不让儿子干农活。父子俩对着江中巨大的“印心石”,伴随资江涛声,勤诵苦读。
嘉庆五年(1800),二十一岁的陶澍与父亲一同到长沙参加乡试。陶澍一举考取第30名举人,陶必铨却落榜了。第二年,陶澍第一次离家赴京,参加会试,这次名落孙山。他遵从父亲嘱咐,留京温习功课,准备再试。嘉庆七年,二十三岁的陶澍一举考中全国第二名,考官申报陶澍为一甲榜眼。
殿试由嘉庆皇帝亲自主持。不巧,陶澍在“策”内遗漏了一个字,读来不大顺口。关键时刻,怎能出错?陶澍被抛进二甲第十五名。虽然在全国排到第十八名,但依然是很不错的成绩。陶澍由此成为安化县有史以来第一个进士。
早年跟着父亲四处求学,生活颠沛流离,陶澍对与自己颠沛经历相似的左宗棠,本能地感到亲近。陶澍在与左宗棠聊天中发现,他在岳麓书院艰难的求学经历,与左宗棠在城南书院苦撑的求学过程心路接近,且两人课堂之外,都偏爱“杂书”:陶澍读“算学、测量学”,左宗棠读“农学、舆地学”。陶澍凭经验与阅历已经看出,左宗棠的底子与资质都属于一流,只要给到他平台与机会,一旦事权到手,他可以创下什么样的高度。因为,陶澍凭“算学、测量学”已经在本朝开创出后来者的高度。
作为清朝中期最醒目的经济改革家,陶澍一生事功显赫,主要在三个方面:其一,改漕运为海运。其二,改纲盐为票盐。其三,改银钱为制钱。
漕运是朝廷利用河道调运公粮的一种专业运输方式,说简单了,南粮北运。
秦、汉以前,北方是中国粮食主产区,政治中心就在河南、陕西,不存在南粮北运。唐、宋以来,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北方人口膨胀,帝国首都却在北方,粮食逐渐不能自给。南粮北运,成为朝廷的重点工程。清承明制,额征漕粮,每年通过京杭大运河运抵京、通二仓的粮食,最少达三百万石,多则过四百万石。北京城内,上至皇帝、皇室,下至王公贵族、各部官员、八旗兵丁,数十万人,生存的口粮全赖漕运。一旦漕运断航,意味着满朝文武,如不愿坐等饿死,只能临时迁都。漕运历经数代王朝,发展一千余年,已经形成成熟的运输体系,利益链条盘根错节。漕运的基本方式是“官督官办、国有国营”。为保证效率与公平,朝廷专设漕运总督、河运总督,权力与地方督、抚平行,三方相互配合。
朝廷设此制度本意,是为了让官员相互配合、相互监督。不料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地方要员办事相互推诿,出了问题互相扯皮,主事官员背后贪腐,办事吏员趁机“浮收”,整个系统腐败深入骨髓,到道光五年(1825),已经难以为继。陶澍勇敢担起道光皇帝指定的“国家一号工程”,他跳出帝国体制的僵化与局限,首倡海运,借助民间商人在东南沿海的沙船来运送漕粮。陶澍通过自己长袖善舞的政治运筹,改漕运为海运,大获成功。海运成功的原因,在于完全抛开河运旧有的官僚体系,另辟蹊径,借助一种新型简约的官僚体系,将新生的商人力量组织起来,政府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完成了朝廷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纲盐改票盐,与漕运改海运思路一样,将国有国营的纲盐改为自由市场竞争的票盐。陶澍左手推票盐,按市场规律出牌,右手破垄断、废特权、追缴欠课、抄没家产。盐政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两淮盐场由“商疲、丁困、引积、课悬”,一跃变为“盐销、课裕、商利、民便”。
改银钱为制钱,则是朝廷的币制大改革。清朝所行的货币制度沿袭明朝,银两、制钱并用,实行“银钱复本位”货币制度。银块称量计值,以两、钱、分、毫为单位;制钱则由政府铸造,每枚一文,规定每银一两抵钱千文。陶澍改革的方案是:官局先铸银钱,每一枚以纹银五钱为准,全部按照制钱的式样,一面用清文鑄其局名,一面用汉文铸“道光通宝”四字,暂将官局铜钱停卯,改铸此钱,经费比铸铜钱节省十倍。
但这次改革却功败垂成。为什么改革一进入深水区,才啃到硬骨头,朝廷却紧急叫停?道光皇帝给出的理由是:“大变成法”。真实的原因是,陶澍市场化改革既冲击到帝国集权制度,又冲击到农耕宗法文化,已让道光皇帝无法容忍。改革冲击制度,原因是陶澍根据商业规律,推行市场化改革,已经进入金融领域。市场的契约、平等、自由,对皇权已作无声瓦解。
对文化的冲击,基于海运拓宽了国人的视野,撼动了农耕文化的保守、内向。面对浩瀚陌生且生机勃勃的海洋,全新的主权意识、海疆意识、军事战略意识萌生,传统文化面临淬水重生。全球化到来,面对平等、民主、自由潮流,大清帝国本能退缩。
陶澍改革前,清朝有“康乾盛世”;陶澍改革之后,清朝有“同光中兴”,他所在的嘉庆一朝,恰是大清帝国由盛转衰的拐点。“同光中兴”依赖的两大得力干将左宗棠、曾国藩,皆为陶澍晚年用心提携,精心引导上来。
陶澍由此成为大清帝国由盛转衰的标志性人物:他主持的改革被叫停,标志在全球化到来的前夜,大清帝国不愿壮士断腕,刮骨疗毒,已经难以自救。站在帝国体制的角度,陶澍已经清晰看见,要振兴衰落的清王朝,关键在得人才,有一批真正通实学、敢办事、能办事的大臣。草野书生左宗棠正是陶澍认可的振兴衰世大才。他决心培养这个天资与勤奋都不俗的青年,让他来担当起挽救清朝的重任,完成自己未竟的使命。
道光十七年(1837)首次见面结交,陶澍事实上已初步定好提携计划。
第二年,左宗棠第三次会试后,应约从北京绕道到南京,在两江总督府拜见陶澍。陶澍开头故意冷落,以激将法进一步考察左的人品,直至认定他是一个不但可以托付后事,而且可以将国事担肩的正人君子,才确定破格提携。陶澍的方法,将独子陶桄托孤,约为儿女亲家。陶氏清楚,自己去世之后,左宗棠有耐心安居小淹,看完他家藏的上万册图书,其后临事再出山,必是全国一等一的大才。
陶、左公开结为儿女亲家,伦理、辈分、地位均不对等,令全国士林哗然。曾国藩当时在致诸弟的家信中责怪说,陶相老迈昏花,为了求人才竟然不顾年龄辈分,乱了伦理纲常。当然,曾国藩态度后来很快有所转变,因为他本人也与大自己二十六岁的贺长龄结成了儿女亲家,只是贺长龄庶出的小女儿许配给他的嫡长子曾纪泽,让曾家多数人感到疙疙瘩瘩。
此例可以见出陶氏破格赏识与提携左在中国官场产生的轰动效应。
道光二十六年(1846),贺长龄的大弟贺熙龄将三女儿也许配给了左宗棠的嫡长子左孝威。根据贺家的姻亲血缘排辈,左宗棠跟曾国藩也属于亲家。这是题外话,顺及。
陶澍晚年的工作重心之一,在奋其余力,以耿骨忠臣的心志,苦心孤诣为朝廷培养后备人才。为此,他对魏源、贺长龄、曾国藩、左宗棠,不遗余力进行提携,布下一盘很大的棋。
陶澍偏爱左宗棠,托孤于他,表示陶澍对通过科考入仕的体制内官员,已经心灰意冷。
陶澍这种观念,直接缘于道光皇帝长年累月对他抱怨,称朝廷内大臣平时总想自保,不愿像陶大臣一样公忠体国,为寡人分忧。听得多了,陶澍警醒。改革实践让他看清,循规蹈矩的科举人才,擅长词工,短于治事,缺乏担当。陶澍同时想清楚了一个道理:人才失求诸野。民间独立士人,是挽救清王朝最后可依托的人才。他决心以自己的名望,通过联姻的方式,为左宗棠打开名气,敲开入仕的门。
近代历史学家萧一山也看出了这点,他总结说:清朝“中兴人才之盛,多萃于湖南者,则由于陶澍种其因”,“不有陶澍之提倡,则湖南人物不能蔚起。是国藩之成就,亦赖陶澍之喤引尔”。
陶澍凭借士人的担当,终生为朝廷尽心卖力,付出了牺牲家庭的代价。他一生先后娶了七个老婆,生有八个儿子、九个女儿。但因他公务繁忙,常年奔走在官场事务最为繁杂、利益争夺最为严酷的风口,无暇顾及,在经年的举家迁徙与长途奔命中孩子相继死去,只留下七岁的小儿子陶桄。
陶澍抛弃家庭与个人幸福,为挽救衰世呕心沥血,在循吏大行其道的清朝官场,同样是个异数。陶澍舍家报国这种强大的心志与毅力,很大程度上缘于湖南这片土地的人才,历史积累两千年,这时才第一次真正得到开发。从春秋战国起,湖南一直处于自由野性、自生自灭的边缘状态,进士屈指可数,官员寥寥无几。
自隋朝设科举制度以来,到明朝茶陵才出个李東阳,高居宰相,这是湖南本土产生的第一个高官。陶澍作为清朝产自湖南本土的第一位高官,对圣贤学说、孔孟之道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诚”,这种“诚”达到近乎迷信执着的程度。他处处以圣贤标准来要求自己,规范言行,追求具备圣人的才德,治国实践中施行王道,以期立德、立功、立言,即“内圣外王”,“三立”不朽。陶澍带头如此,左宗棠紧随其后。两人同以乡下贫寒士子出身,能够相继迅速发迹,在权位匹配后大刀阔斧改革,得益于早年栖居乡下,凭勤奋苦学,以儒学修养出了君子人格。
在陶澍、林则徐二公祠,左宗棠题写过一副对联,传递出的正是这种君子人格的“诚”:
三吴颂遗爱,鲸浪初平,治水行盐,如公皆不朽;
卅载接音尘,鸿泥偶踏,湘间邗上,今我复重来。
就私情而论,因为陶澍的提携,民间士子左宗棠在大清帝国庞大的关系网与纵深的历史感中,找准了自己的位置。通过陶澍的指点,左宗棠出山前积蓄了足够的知识储备与人脉资源。陶澍因为结交左宗棠,不但事业理想找到了寄托者,而且他的独子陶桄也被左宗棠成功教大成人,学问、事业皆有所成,在身后留下十多个子女。按传统的香火观念,陶家今天数百后人,虽由左宗棠长女左孝瑜所传,但陶家血脉不断,主要还是得力于左宗棠的经营与栽培。这对年龄相差三十三岁的“忘年交”,因为湖南醴陵的一面之缘,实现了延古继今的相互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