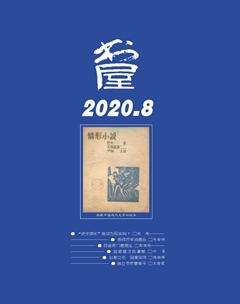回首师门感易生
彭晓玲
一
同治十二年(1873)乡试,欧阳中鹄成功中举。次年赴京会试,他第一时间去拜访了同乡好友谭继洵,谭其时任户部员外郎。谭继洵热情接待了他,留他住在浏阳会馆。此次会试未中,欧阳中鹄只得再去参加优拔贡廷试,倒取了一等,得任内阁中书,正式进入仕途。大小也是京官,几个浏阳籍京官好好聚了一次,欧阳中鹄也就安心地开始了京城生活。这年七月起,谭继洵聘他在谭家家馆教读其子嗣襄、嗣同。时欧阳中鹄二十五岁,嗣同方十岁。
欧阳中鹄学术上很推崇王夫之,王夫之号“姜斋”,他取“瓣香姜斋”之意,自号瓣姜,以示对王夫之的崇敬。也因此,在给谭嗣同兄弟教授《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时,不忘传授王夫之的学术思想。虽然王夫之的学说深奥难懂,但他的讲授深入浅出,谭嗣同一听就懂,对此产生了兴趣,并终身推崇这位伟大的学者。
光绪二年(1876)春,京师流行白喉,谭嗣同的二姐谭嗣淑患白喉病,听说谭家人不好好照顾嗣淑,母亲徐五缘很着急,带着长子谭嗣贻前去探病。不想此病非常可怕,母子都感染了白喉病,连带谭嗣同也染上了。如晴天霹雳,五天之中,母亲、长兄及二姐相继被病魔夺去生命,不到十二岁的嗣同也昏死过去。当时,谭家在这次白喉流行病中死了六人,甚是凄惨,人心惶惶,家人竟没有人敢去为徐夫人母子三人操办收殓之事。欧阳中鹄悲伤之余,毅然带人前往浏阳会馆,亲手将殡殓之事办理妥当,将几人的灵柩暂厝于寺庙。
那真是一段难熬的日子,嗣同自一月下旬发病,直至四月中旬尚不能起床,但除了欧阳中鹄,几乎没有人真切地痛惜这个病中的孩子。谭继洵在寄回浏阳的家信中写道:“嗣同于万死之中幸获一生,现尚辗转床间未能起立,仅食稀粥、蒸饼,喉间似有物阻,必因溃烂尚未生肉复原也。”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欧阳中鹄都是嗣同的安慰和依靠,一往情深地关怀着他的成长。嗣同将老师当作自己的父亲,在老师那里得到了家庭所得不到的温暖,借以度过艰难的岁月。欧阳、谭之间一开始就显得不同寻常,远远超出了一般师生情谊。嗣同不光对老师的“片纸单词珍若拱璧”,每次回浏阳,都要到欧阳中鹄家去看望老师,往来很密,乃至欧阳家上上下下都认识。光绪二十年(1894)十一月,谭嗣同正在浏阳修族谱,在欧阳中鹄未能回浏之前,主动替老师监修他父母的坟墓,在山上一住就好几天。
光绪三年(1877)八月,谭继洵升任甘肃巩秦阶道,冬天便请假携家眷返浏,以安葬头年去世的徐夫人。欧阳中鹄随谭家一同回浏阳。不想第二年,父亲欧阳向曦去世,欧阳中鹄乃居家守制。之后,欧阳中鹄先后入杨昌浚、瞿鸿禨幕府,在杨府负责教读杨氏子女;在瞿府时,瞿当时正在浙江学政任上,主要协助他整顿“诂经精舍”,曾代瞿撰《申订诂经精舍规约》、《书申订诂经精舍规约后》,体现了他主张继承阮元“专免实学”、“非以弋功名”的办学宗旨。至光绪十三年(1887),欧阳中鹄再次入京充会典馆协修,此时好友刘人熙亦为会典馆纂修,两人在京师得以朝夕与共,诗酒唱和。欧阳中鹄本不善作诗,正是在刘人熙、张百熙的带动下,诗兴大发,诗作连连,五言古诗《效陶》二十首、《咏怀》数十首等,都是作于此年,受到大家一致好评。
光绪十四年(1888),光绪帝大婚,欧阳中鹄临时充大婚典撰文,及上徽号典礼撰文。至光绪二十年(1894)二月,欧阳中鹄充武殿试填榜官。这一年发生中日甲午战争,眼见当时朝廷种种妥协,欧阳中鹄非常失望愤慨。虽正值战中,急需任人之际,欧阳中鹄仍以父亲的坟墓被水所浸伤,坚决请假回籍修墓,受到很多人非议。欧阳中鹄很是受伤,说阁臣陆润庠等也请假南归,而独指责他,实在不公。好在王芝祥给予他理解,在《致王铁珊舍人芝祥》信中,欧阳中鹄辩解道:“此次乞假,出于义无可逃,唯求此心之安。论者不察所以然,多以去非其时,疑为规避。”
欧阳中鹄经天津坐海轮至武汉,曾专门拜访了谭继洵、陈宝箴,坦陈自己对战局的看法。欧阳中鹄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主张趁未大败时言和,还可多些言和的条件。更难得的是,他在这些友人面前极力阐述了朝廷急需变法,认为非废除当时之科举制度,改习西法不行!在浏阳士人群体中,他最早提出变法主张。至十一月十五日,欧阳中鹄离开武汉,而谭嗣同与唐才常却在同一天双双从浏阳到达武汉,计划去考“两湖书院”,师生由此错过了见面。
晚清浏阳士人之学,以程朱之学为根本,而近学王夫之(船山)。当然各人又有所不同。刘人熙与欧阳中鹄,同样是宗师船山,刘人熙主要取《周易内外传》、《张子正蒙注》,而欧阳中鹄则最重《俟解》、《四书训义》。王夫之“器变道亦变”的思想,也成为欧阳中鹄当时主张变法的依据。当此社会处于急剧变化时期,包括欧阳中鹄在内的很多学人一改乾嘉朴学作风,而致力于通经以致用,从而找到了《公羊春秋》,以为找到了治世之良药。后来王闿运学生廖平以及深受廖平影响的康有为、梁启超诸人,则走得更遠,以托孔子改制,倡导维新变法。
甲午战争创痛巨深,欧阳中鹄痛定思痛,不光看到天下之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更认识到西方经济军事的强盛和政治法度的优长。于是,欧阳中鹄明确主张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各国的政法、科技、工商业,直至语言文字。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朝野上下,必尽更新,礼所谓可与民变革者,皆变革之;其不可变革者,如正纲纪,一道德,愈从而敦厚之;积中不败,然后鞭笞四夷,是以有酌取西法之论。”他还断言:“果变一切法,十年之间,必足自立。”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全国震惊,对所有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来说,这次打击极为沉重。浏阳士人中应该是谭嗣同最早得到消息,因为他此时正在湖北抚署帮助其父处理政务,很多公文、函牍他都最先读到。谭嗣同极为愤慨,心如死灰,几乎想出家为僧。欧阳中鹄由于僻居浏阳,到四月中旬始得闻此消息,竟愤恨欲死,坐卧不宁。他在《复陈曼秋》信中宣称:“四月二十后,闻和议已定,每私居啜泣,愤欲自裁……”他在《复蔚庐》信中痛陈:“和议已成,于四月十四日换约,闻之愤恨欲死。”他在《复护湖广制台谭敬甫中丞》信中悲叹:“中鹄本无宦情,自闻和议,愤恨欲死,此心更如槁木死灰。”欧阳中鹄于这年写给友人的信函中,无不长篇累牍地分析当时形势,可见其愤恨归愤恨,而其心则无时不为国为民忧虑。
此时,谭嗣同深受刺激,他决心抛弃科举八股、考据辞章等旧学去寻求新学。但“新学”究竟是什么?一时还显得比较模糊。是年十二月上旬,欧阳中鹄从浏阳致函其时正在武昌的谭嗣同,提出形势如此,个人何以自处?给谭嗣同以极大的震动。谭嗣同辗转反侧,深刻反省并思考国家命运和前途,由此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必须实行变法,以改变“养民卫民教民一切根本大法”的局面。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夏,谭嗣同的变法思想基本形成。五月二十三日,欧阳中鹄再次致函谭嗣同痛论时局;谭嗣同、唐才常等认真拜读先生手书,一字一泪,不由泪洒衣襟。
二
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时代开始,已经进行了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为何无法使国家强大起来,无法对抗日本呢?在谭嗣同看来,洋务运动不过是细枝末节,他形成了自己一套逻辑:讲求变法必先从读书人开始,要改变读书人始必先改革科举,使人人能各自精通一门,各自力争在实学上有所作为。为此,他认为最急需下手的事情,就在振兴实学,就在开算学馆培养数学人才。
与谭嗣同有相同想法的,还有其好友唐才常、刘善涵。当时唐才常和刘善涵就读于两湖书院,他们每天都会见面,并反复商议如何引导人们参与维新变法,如何兴办算学馆。于是,由唐才常上书浏阳士绅之首谭继洵,请其利用自身影响去说服湖南巡抚,酌拨浏阳南台书院膏火之半,以设立浏阳格致书院,并亲自带头捐廉予以倡导。但谭继洵却认为还是遵循一贯的规矩好,没有必要去为天下先。此路不通,他们转而竭力说服老师欧阳中鹄。欧阳中鹄在浏阳颇有名望,而且倡导变法,他倘能率众办学,应能事半功倍。
谭嗣同在闰五月初九接到欧阳中鹄的信后,写了一封洋洋万余言的回信,在信中全面阐述了对时事的看法与痛苦忧虑,极言变法之必要,内容涉及开议院、办工矿企业、办学校、改科举等许多方面。此文成了谭嗣同在甲午以后愤然而起的一篇变法宣言,无论从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超出了其师欧阳中鹄,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还特别阐述了开办实学的思想和倡立算学馆的计划。五月十日,唐才常亦致信欧阳中鹄谓:“一乡一邑,如能设法稍开风气,或培植一二人才,为将来驱驰之用,即于事不为无补,而可启一省之先声……”
欧阳中鹄认真读过谭、唐关于举办格致书院的来信,心潮澎湃,但又有所顾虑,担心浏阳儒生们依然醉心于科举,会来阻挠新学。正在欧阳中鹄犹豫之际,而当时政局对变法也有利,清政府在五月十三日下发保举精于天文、地理、算法、格致、制造诸学者的上谕。湖南又以陈宝箴任巡抚,亦有心变法图强,且当时湖南学政江标也支持新学。这些条件均促使欧阳中鹄下定设立算学馆的决心。于是,欧阳中鹄认真考虑成立算学社一事,且为之行动起来了。
湖南学政江标于七月按临浏阳,各乡秀才集中在县城参加岁考。谭嗣同会同唐才常、刘善涵、涂儒翯、罗召甘等人十多名秀才,联名向其递交了由刘善涵起草的《上江标学院禀》,申请将南台书院永远改为算学馆,并会同公正明白的绅耆,细定章程,妥为办理。江标对倡立算学馆之事极为赞赏,批文道:“浏阳城乡五书院,旧皆专课时文,近拟将南台书院永远改为算学馆,与四书院文课相辅而行。”并札示浏阳知县唐步瀛立案。当此时,大多数以反对洋务、标榜正统的秀才一片哗声,对浏阳设立算学馆一事大不以为然,诋之为妖异,坚决与之划清界限,并且相互告诫抵制算学馆的余毒。后来,随着《兴算学议》、《书兴算学议后》的出版,士子们了解到变法的原因及目的后,纷纷表示理解或支持。
谭嗣同北游访学后,与老师欧阳中鹄在思想上开始出现分歧,师生关系已有所疏远。据欧阳中鹄所说:“及(谭)次年入京赴行,宗旨遂变。尝以书来,言誓发宏愿救四万万人,其语多释理最高明处,知已为异学所引。丁酉(1897)冬归,与语间不相洽,视弟文字不甚措意。”
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中旬,欧阳中鹄进入陈宝箴巡抚幕府,参与省中新政,师生再度共事。鉴于原先陈氏幕僚罗正钧、黄修原等人与维新派关系不佳,维新人士对欧阳中鹄进入陈氏抚幕,极表赞同,并大力促成之。欧阳中鹄进入抚幕后,自然而然成为陈氏父子联系维新人士,特别是谭、唐的中介人。
当省内外守旧派的压力滚滚而来时,陈宝箴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摇摆于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对湖南维新运动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一转变始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矛盾最初产生于谭嗣同和陈三立之间。三月三日,谭嗣同在《湘报》刊登康有为第五次上光绪皇帝书,并撰写按语加以赞美,引起陈三立的强烈不满,陈认为“嗣同等钻营康名士,自侪于门人之列”。欧阳中鹄也表示不快,认为谭嗣同并非康有为门人,为什么要自称门生?谭嗣同对陈三立也早有不满,认为他平日诋毁梁启超、诋毁唐才常,及力阻不许聘康有为来湖南。他转而指责陈三立对康有为自揣学问不如人,而又不胜其忌妒之私,于是诽谤他取笑他。
正因为遭到王先谦、叶德辉等守旧势力的攻击,又遭到陈三立、欧阳中鹄等维新人士的不理解,谭嗣同、唐才常变得更为激昂。谭嗣同在致欧阳中鹄书中写道:“才常横人也,志在铺其蛮力于四海,不胜则以命继之。嗣同纵人也,志在超出此地球,視地球如掌上,果视此躯曾虮虱千万分之一不若。一死生,齐修短,嗤伦常,笑圣哲,方欲弃此躯而游于鸿蒙之外,复何不敢勇不敢说之有!”
至三月八日,谭嗣同、唐才常在《湘报》刊登了易鼐《中国宜以弱为强》一文,顿时引起震动,陈宝箴、黄遵宪认为过于惊世骇俗。在黄遵宪看来,日本有渐进、顿进二党,现在即便求顿进,也难以快速取得效果,不如采用渐进法,报纸上刊登的文章不要太激烈。陈宝箴反应更为强烈,指责其“过于偏激,惊世骇俗,非处士所宜言”,并“命瓣姜师致书报馆以责之”。陈宝箴公开出面干预《湘报》言论,这还是第一次。接信后,唐才常与谭嗣同非常愤慨,立刻回信为之辩护,该信以《复欧阳节吾舍人论报书》为题刊登于三月十一日的《湘报》上。
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以“为乃翁五十祝寿”为由,于二月中旬离湘赴沪,本拟诸事完毕后仍然返湘,故并未辞去总教习一职。梁走后,守旧派蜂起攻击,扬言已在学堂读书札记中,发现粤人教习的激进批语,涉及批评君权及反满族意识,称之为“悖乱实据”,要求撤换学堂教习。维新人士认为此举证明陈宝箴对他们已有疑心,其心中的惶惑与愤慨可想而知。唐才常甚至认为,王先谦、叶德辉攻击学堂事出有因,欧阳中鹄因为谭嗣同及他赞美康有为而老大不高兴,就在陈宝箴面前说了坏话;早就听说陈宝箴想让王先谦代替熊希龄,以叶德辉担任总教习,看来陈宝箴已经和他们握手言欢了。
陈宝箴未必有以王、叶主掌学堂的计划,然而确有撤换粤人教习的打算,但因遭到黄遵宪、熊希龄的反对,一时难以实施。整顿学堂暂时未果。闰三月二日,时务学堂添聘教习,在增加唐才常、欧榘甲二人的同时,又增聘陈氏友人周大烈为教习,算是双方的一个妥协。从当年闰三月起,陈宝箴迫于守旧派压力,开始采取措施限制维新派,他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整顿学堂。闰三月中下旬,陈宝箴下令调阅时务学堂学生读书札记。到四月下旬,在陈宝箴的授意下,时务学堂决定改定课程,振兴实学,并正式宣布:“现在时务学堂学生于经学已通大义,拟将课程改为特科六门,由教习择各学生性之相近者分门教授,以备经济特科之选。”由此,改变了梁启超为时务学堂拟定的教学方针和课程。
经此事件,维新阵营的内部关系趋于紧张,气氛大为恶化。闰三月二十日,又发生了出时文题事件,在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掀起了轩然大波。是日,岳麓、求忠、城南三书院官课考试,由欧阳中鹄出题。时文本来是维新派极力反对、强烈要求废除的,欧阳中鹄自己早在甲午年间即主张废除,早几天陈宝箴在南学会演讲,也认为时文之弊病极大,宜废除。且事先皮锡瑞等一再要求不出时文题,而改出时务题,欧阳中鹄也勉强答应。临到考试时,发现出的仍是八股时文题,维新人士顿时哗然。皮锡瑞写道:“此等题出自何人?令守旧者鼓舞欢欣,维新者扼腕太息!如此办法,必无振起之望。”此时,维新人士对欧阳中鹄极为不满,视其为维新变法的阻碍。唐才常也说:“乃师办事本无决见,好听小话。浏阳开化,并非其功,到此专听污吏赖子佩之言,荧惑上听。”
事实上,陈宝箴、欧阳中鹄在对谭、唐等维新派采取行政措施的同时,也开始采取措施“厘正学术”,以便与维新派的“平等民权”学说划清界限,在思想上保持距离。而对于诸生试卷,欧阳中鹄进行了大量的批阅,特别在某些言论过激的试卷上,其批语多至千余字。何来保既是校经书院学生,又是《湘报》主要撰述者,他属于与谭嗣同、唐才常一类的维新激进派。其关于《墨子·尚同》篇的策论,明显主张民权思想,故遭到欧阳中鹄的批驳,且将其名次置后。至此,浏阳变法以来,欧、谭师生之间所潜伏的深刻思想差别终于凸现出来。
谭嗣同于闰三月十八日为组建团练事返回浏阳,逗留将近半个月。不料在此期间,风云突变,形势急转直下,而调阅札记及出时文题时他都不在长沙。四月五日,谭嗣同由浏阳回到长沙后,即和唐才常一起与欧阳中鹄通过书信进行交涉,据理力争,力图为学堂等事“雪清此谤”。谭氏在信中说明出时文题一事为何引起“群然愤怒”,谓维新人士对欧阳中鹄“所愤者初非区区一题,盖把持一切,新政不得展布耳”,并要求与欧阳中鹄作一次开诚布公的长谈,认为“凡事总以直说为好,若愈隐则愈误”,希望从源头讲明学术宗旨,“不然,则满腔热血不知洒向何地”。
出时文题还有一个原因是阅卷较易,但欧阳中鹄的解释,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实际上应当是湘省官方遏制维新激进派的措施之一,如同调阅时务学堂札记一样。随之,谭嗣同、唐才常在《湘报》馆主笔地位被黄膺、戴德诚代替,《湘报》不再刊登激进言论。为此,失去陈宝箴的支持,谭、唐等维新派在湖南已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曾经引人注目的南学会讲学也难以维持下去了。四月十三日,南学会发表《申订章程》,宣布讲学暂时休会。“天时渐热,人多气郁,难以宣讲,本学会议暂停止,俟有阴雨凉爽时,或所讲新理及所闻时事须集会友讲听时,当择期预行刊报布告”。
与此同时,陈宝箴密折保荐经济特科等人才六十人,其中以欧阳中鹄为首,在保送他为经济特科的考语中,称赞其“学术正大,持论平通,不为偏激”。而欧阳中鹄以为既为陈宝箴幕僚,陈氏如此推举保荐,自己还是避嫌为妙,故极力推辞。不过,当时因欧阳与维新激进派有隔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杨深秀诸人在京辅佐光绪帝变法,诸人也不会吸引欧阳中鹄进京。
维新派在湖南备受压抑的情况,至四月下旬出现转机。四日二十五日,侍读学士徐致靖上奏举荐著名维新人士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等人。光绪立即采纳其建议,发布上谕,准备召见康有为,并令黄遵宪、谭嗣同赴部引见。处于困境之中的谭嗣同得此消息后感叹:“此行真出人意料,绝处逢生,皆平日虔修之力,故得我佛慈悲也。”临行前数日,谭嗣同写了封信给欧阳中鹄,准备约唐才常一起去欧阳中鹄寓所作竟日之谈,专门讲明学问宗旨,并就此辞行。五月九日,谭嗣同赴欧阳中鹄处辞行,同时向其说明维新派关于救亡图存的计划。次日,欧阳中鹄致信谭氏,劝其勿锋芒太露,韬光养晦,暂时退隐,“平其心,养其气,敛其才,藏其智,以俟积厚流光,异日出而倡其学”。但他的劝谕未起半点作用,此时师生在思想政见方面已存有很深的隔阂,最后一次谈话不欢而散,欧阳中鹄唯有连连叹息。
在此,欧阳中鹄还强调指出双方学术的原则区别在于:“吾儒是礼,是文家兼质家;汝学是墨,是释,是耶,是纯乎质家。然流弊太多,不能自立。”此种分析很客观到位,欧阳中鹄是较纯粹儒者,奉行中庸之道,虽主张变法维新,但只准备以渐进的方式来实行。而谭嗣同由于其家庭生长环境的原因,形成其躁急偏执的个性。欧阳中鹄在与他相处的二十余年中,一直努力化解其戾气,可惜失败了。再加以自丙申北游,谭嗣同接触西方先进科技知识以及基督教、佛教,思想为之大变,主张激烈的变化方式,特别是力推民权平等的思想。这些是欧阳中鹄断断乎不能接受的,师生分道扬镳也就成为必然。直至谭嗣同喋血菜市口,欧阳中鹄还是认为“临刑谈笑自若,可谓壮,惜乎未闻道也”。
三
戊戌变法失败后,随着陈宝箴被革职交卸,湖南守旧士绅势力极大,叶德辉诸人在维新运动中及运动后大出风头,大力攻击维新人士。欧阳中鹄是谭嗣同最著名的老师,又是维新变法的倡导者、参与者,在当时那种风声鹤唳的形势下,受到的冲击就可想而知了。
谭嗣同被杀后,其灵柩由胞侄谭传赞与谭嗣同两个忠实仆人于九月十八日运达长沙。九月下旬,谭嗣同灵柩运抵浏阳,安置在城外茅坪。谭嗣同是被朝廷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杀害的,在当时看来极不光彩,故谭家不准备举行悼唁仪式。歐阳中鹄念师生之情,禁不住老泪纵横,遂由长沙返浏,忍痛亲自主持丧葬事宜。他遵从谭嗣同先前信佛的意愿,特地延请僧人诵经超度,做了七天道场,还烧了纸钱等。欧阳中鹄当时亦大受谭嗣同一事牵连,而他仍能出面为谭嗣同经办后事,其气节也令人钦佩,也非一般人可做到,真正尽了师生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