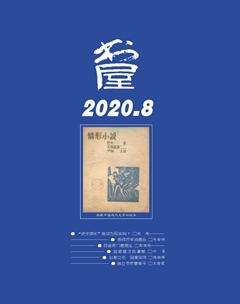思君雄才良凄楚
叶隽
滕固(1901—1941)先生英年早逝,有些像德国天才薄命的意味。确实,仔细盘点先生遗作,我们要承认,滕固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过早凋零的艺术精英,值得后世追怀。钱锺书眼高于顶,是出名的才子型人物,然与滕固却颇为投契,相互之间有诗词酬唱。滕固赠诗给钱称:“十九人中君最少,二三子外我谁亲。”以表达对小自己十岁的钱氏之格外欣赏。而初闻滕固死讯,钱锺书即作诗悼念,《哀若渠》四首哀婉动人,使人潸然欲泪。后《又将入滇怆念若渠》一诗云:“学仙未是归丁令,思旧先教痛子期。沉魄浮魂应此恋,坠心危涕许谁知。”1938年在昆明,钱锺书留英归国任教于西南联大;此时,滕固则在主持国立艺术专门学校,二人一见如故。1939年,滕固邀钱锺书为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撰讲稿,钱锺书写了《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
当然,追溯滕固的友人圈子,最需要提及的,自然还是留德时代的精英交谊。朱偰撰文《吊若渠》,反映出当时留德学人的状态:“余游莱茵归来,与若渠同寓于柏林西郊,风晨日夕,相与唱和,无间风雨。”不仅如此,他还记录下了滕固留德时代的赠诗,让人很是感慨:“我来柏林城,君涉莱茵浦。相送虾龙驿,挥手良凄楚。归来箧衍中,满贮新纪叙。旖旎若李温,悲凉似老杜……”这是滕固赠给朱偰的诗,遥想先生当年,在异邦萧条的风土之中,能得见同乡同道,相互酬唱,引为知己,真是乐也何如。而事隔多年之后,朱偰先生作长诗《秋夜述怀寄昆明姚教授从吾滕校长若渠冯教授至白沙蒋馆长慰堂北碚梁教授宗岱三十三韵》则给我们理解那代留德学人的交谊状况和精神风貌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诗史”记录,所谓“声名传海内,寥廓各殊方”,当年曾经意气风发,而今国难当头之际,却仍不禁要“忆昔西游日,文星聚上庠”,于是在朱氏的浓墨重彩之下,昔日留德的各位人物陆续登场:
姚公拾遗闻,荟蕞涉重洋。
作史准班马,结交尽贤良。
滕君瑚琏器,遁迹翰墨场。
偶然赋■鸟,郁郁焕文章。
冯公江海客,澹泊岂佯狂。
论诗追义山,作赋拟班扬。
蒋公柱下吏,秘册富珍藏。
东西罗史乘,图籍列琳琅。
有客远方来,言是南海梁。
冥搜真与美,秀句满遐荒。
徐公久不見,家世出潇湘。
脱略公卿思,跌宕文苑旁。
余随诸子后,风雨必相将。
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
这里的七位人物,都是日后在中国现代文化场域大展身手,各自留下了辉煌业绩的名人。即姚从吾、蒋复璁、滕固、梁宗岱、冯至、朱偰、徐梵澄。他们之间年龄相差或有在十年者,却都是留德一代的佼佼者,是当年聚集在德意志国土上的一代中国知识精英。姚从吾治蒙元史,是相当有成就的一代学人,亦曾获德国学者的充分肯定;而作为诗人的冯至,则代表了德诗在华的有力存在;梁宗岱兼通法、德,对欧洲南北文化有相当深刻之体认;至于徐梵澄,以其对梵学、西学的不凡造诣,而被誉为沟通中、西、印三大文化的一代通人;蒋复璁专治图书馆学,对中国图书馆等文化事业之开辟颇有贡献;滕固则不但曾是狮吼社的重要代表作家,日后更成为一代艺术史家;朱偰就更了不起,他所治为经济学,但其中国传统文化修养洵嘉,著述与文化保护事业都相当突出。
朱偰曾记录下和滕固的交谊过程:“余初识若渠,乃在1930年暮春,时余将远游莱茵,若渠则方亡命至柏林,送余于虾龙驿车站,客中送客,倍觉情深。后余归柏林,相交益厚,时常相过从者,有海宁蒋慰堂、襄城姚从吾、长沙李石岑、河北冯君培、长沙徐梵澄以及南海梁宗岱、山东刘衍淮等,皆一时知名之士。每逢星期假日,辄聚会于柏林西郊森林湖畔余之寓庐,上下古今、纵横六合,无所不谈。真有‘意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之感。而席间挥斥八极、才气纵横者,尤以若渠为最。后余以1932年夏归国,若渠亦不久东渡。其在欧游踪极广,尝西游巴黎,南访罗马,所至探求古迹,结交名士,尤以所学为艺术史,故对于文艺复兴时代之名城——如翡冷翠(Florence)、威尼斯(Venice)、梵罗娜(Verona)、米兰(Milan)——尤三致意焉。”文言诗的德国叙事,或许是个值得探究的话题。早在二十世纪初期(约在1909年),马君武即作诗《特里尔纪游》:“文化传初纪,遗碑尚纪功。比邻新酒绿,残堞古砖红。曲折莫差水,荒颓罗马宫。百年争战地,今暂息兵戎。”陈寅恪在1910年则作《庚戌柏林重九作·时闻日本合并朝鲜》,将其指点江山的学子激情外溢无疑,先是说“惊闻千载箕子地,十年两度遭屠剖”,对朝鲜之任人宰割命运深表关切,结语则为“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到滕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柏林感怀,这一脉络延绵未绝。白话诗的崛起自然有其内在逻辑可循,但其与旧体诗的关系是否便如文学革命所倡导的“非此即彼”乃至“势不两立”,今日看来其实大可商榷,旧体诗的过度压抑,对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形成恐怕未必就是好事。
滕固早年留日,进而转以留德,成就了自身的学养形成过程。这是符合那代留学精英人物的侨易轨迹的,即由日转德,如杨昌济、马君武、张君劢、梁希等,走的都是这样一条道路;彼时日本以德为师,留日学人身在樱花烂漫之地,向往的却是莱茵河的涛声,滕固的留德也符合这样一个大势。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名作家,滕固的作品也很有特色,其作品《壁画》、《银杏之果》、《死人之叹息》、《迷宫》、《外遇》等,值得关注。不过他的作品基本为留德之前所作,应当视作留日作家中的代表人物。当然,值得追问的自然是,为何滕固的诗情在留德之后反而化为“乌有”了。德国作为文艺之邦,究竟给滕固留下了怎样的印记?他在留日之际,生发出浓厚的文学趣味,因缘际会,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最早成员之一,其早期创作都自成风格。更有趣的在于,在有过归国经验后,他又毅然选择了去国行,在1931年留德,此后似乎迅速由文学转向学术,成为现代中国艺术史学的重要拓荒者之一。说起来,他与陈铨、冯至大致是一代人,留德时间亦差不多。作为狮吼社的核心人物,虽然生命短暂,但却才华横溢,故此滕固的文学史地位值得关注。
滕固的成就,固然有天才的一面,但也与后天的求学历程不可分割。其早年留日,后又留德,海外居留近十年,先后求读于日本京都东洋大学、德国柏林大学,获艺术史博士学位。他不但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中国艺术史家,还是一位艺术教育的管理者。他不但曾参加“文学研究会”、“民众剧社”等社团,而且与刘海粟等人发起成立“上海艺术研究会”,是艺术家中的佼佼者,更曾先后出任湖南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校长,是中国艺术教育的领袖之一。他在艺术史著述方面颇有硕果,如《中国美术小史》、《唐宋绘画史》等;译著则有《德国过去对于科学事业的维护》、《先史考古学方法论》等。当然,我更看重的,还是他作为艺术史家有否卓识。在滕固看来,“音乐为世界观的艺术”,而“音乐的本源在于人心,人心的活动因缘于事物,事物的根极是世界所由生的生命或实在……”这就超越了简单的艺术观的狭隘自闭,而在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人生和人心的范围内来讨论作为艺術的音乐了。
关于由日到德的转变,有论者认为在中国绘画史研究中,这意味着从“日本模式”到“德国模式”的转变,后者主要指理性思维模式和方法论模式。其实日本模式具有普遍性,而不仅是简单的一个过渡而已。不过,滕固的这种生命经历并不仅是个案。譬如青主(廖尚果),就也是一个可供印证的例子。而较此前科目相近的王光祈等人,则有年龄上的差距。这样一个人物,在柏林大学留学了四年,最后获得了艺术史博士学位,应该说是相当不易的。经由蔡元培先生开端的德国美学引进工作,经由杨丙辰、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努力,已经形成了相当的理论积淀;而如王光祈、萧友梅、青主等的专业化推进,则开辟了完全不同的学理空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相比较音乐学的“拔得头筹”,绘画学方面确实值得深究。而滕固的意义,就是在这样一种比较视野中显示出来。一般而言,论绘画,则容易联想到留法学人,如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等都是清一色的留法出身,而且也有不同程度的旅德经验。可若论及绘画史研究,也就是艺术史研究,则留德学人的地位就凸显出来了。而将滕固的遗著择出发表,既显示了宗白华作为美学家的慧眼,其实更主要的恐怕还是滕氏的思想符合宗氏文化建国理想的基本思路,这回强调的是艺术的重要。艺术境界,说到底还是人的生命境界的反映,这一思想与宗白华的美学视角其实息息相通。实际上,这批艺术史精英人物的认知,是受到德国学术思想影响,并且能出而化之,有很强的消化能力的。
对于现代留德学人群体而言,这所大学对中国人来说,一点也不陌生。从二十世纪初的蔡元培那代人,到二十年代的宗白华、王光祈一代,再到1930年代冯至、陈铨、徐梵澄、滕固等,都曾先后立雪柏林,攻读文学、哲学、美学和艺术史。滕固的学养相当不错,他兼及著译,且创作与研究并举,按道理来说,应是有可能得以大成的一位留德学人。可惜的是,他的政治兴趣似过于浓烈了些,所以最后竟然不能专心于本行,再加上天妒英才,竟然在如此绚丽年华夺其生命,使其终不能施展长才。否则以先生大才,当不至于仅仅停留在如此地步。
在柏林大学,宗白华直接受业于德国著名美学家和艺术史家德索(Dessoiz)、伯尔施曼(Bolschman)和哲学家里尔(Riehl),听他们讲授温克尔曼、莱辛、席勒、歌德、康德、黑格尔的美学和艺术哲学理论。这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德索教授对宗白华的影响。德索当时已在柏林大学任教二十五年,讲授美学和艺术哲学,其代表作《美学与艺术理论》亦出版了十五年。书中对美学与艺术理论的许多基本问题都做了系统、完整和丰富的阐述,尤其是有关艺术分类的理解和阐释,有对艺术的理性功能和社会功能、道德功能的把握等,都独具特色,在西方学术界影响颇大。德索主张,“如果审美只包括思维过程,那么谈审美对象就毫无意义了”;凡是研究美学的人,都应该多看艺术作品,用艺术的成就去印证美学理论。还呼吁建立一种普及艺术欣赏的理论,以丰富美学研究。这一思想,显然对宗白华影响非常大。宗不但亲身加以实践,十分重视对艺术作品的考察和研究,并将之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在撰写《美学》、《艺术学》等讲稿时贯穿了这一基本思路,强调“美学就是一种欣赏。美学,一方面讲创造,一方面讲欣赏。创造和欣赏是相通的”。这种专业训练,对于宗白华来说显然是得益匪浅。而这位德索(Dessoir,Max,1867—1947)就应当是滕固的主考官之一、柏林大学的哲学教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留德学人群体之间这种内在的学术、思想的关联性和德国学术的整体场域是有关系的。
滕固回国后出任过国立艺术专门学校(即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的校长,也属于民国大学校长中留德一代谱系中的人物,虽然不过短短两年,但也有其自身的教育观值得探寻。朱家骅说:“若渠有用世之才,也有用世之志,如果他不死,我相信他的前途一定是非常远大的。而且他对于文学和艺术的欣赏力极高,搜集材料作研究的本领也极大,我相信他在学术上的造诣,也会很高超的。”这样一个相当全面的天才型人物,就如此凋零于时代的风雨之中,思之实在让人感慨万千。民国时代“德系知识”谱系的一批人物,似乎都与德国模式结下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其中颇不乏一些天资卓越、深思力行、成就颇彰的人物,譬如宗白华、朱光潜、滕固、朱偰、陈铨、冯至、李长之等都是,当然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他们并没有造就中国历史上的“天才时代”,但重新考量,或许仍可将其称为一种“拟天才时代”,而且其或许还有进一步的世界史意义,这种文化现象是值得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