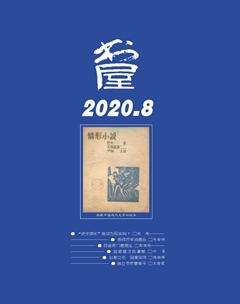什么样的“知识”改变命运?
魏冠宇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没有任何报纸、图书和期刊曾有过“知识改变命运”这一提法。直到1992年2月11日,《光明日报》在第二版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知识改变命运》大型公益广告片春节播出。”随后的几天,一组主题为《知识改变命运》的公益广告通过中央电视台的荧屏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其中的故事娓娓动听:草根如农村小姐妹抽签上大学、大腕儿如导演张艺谋谈自己的成就归因,都讲到了知识对人生的重要性。广告的结尾,对未来做了一个明确的判断:二十一世纪是知识的世纪。从此,“知识改变命运”的这一命题深入人心。
之后,它也一直饱受批评。2002年,“人民网”刊登了一篇网友对这组公益广告的评论,语词直指不同社会群体对教育机会获得的不公,认为广告中注入了“主流人群”具有优越感的潜意识,而对“底层”的人们,则是“把本可改变的命运当成一种难于更改的无奈”。彼时对广告中“精英”和“工人阶级”对立呈现的讨论已经不绝于耳;此后,社会上关于这句名言的讨论从来没有休止。
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到2014年,参考人数上涨了零点八一倍,录取人数上涨了二十九倍,录取率从百分之四点七上升为百分之七十九点五。如果说知识改变命运,那么大多数人的命运应该都被改写了,这在改革开放后物质空前积累的语境中无疑正确;然而人口内部的结构性差异仍在,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百分之三十二点二扩大到2016年的百分之三十八点六(世界银行估计)。人口分化更趋明显,阶层焦虑愈发显现。
对于“知识改变命运”,或许可以这样提问:知识是怎样改变人的命运的?什么样的“知识”改变命运?美国社会学家劳伦·A.里韦拉的《出身:不平等的选拔与精英的自我复制》给出了美国版本的答案:精英雇主凭借其精英阶层的稀缺文化资本,形成了一种定义和评估优点的方法,极大地偏向于具有社会经济特权的孩子。
宏大的叙事抱负终归需要一个落脚点。里韦拉找到了一个巧妙的点:招聘。招聘是就业的必由之路,是知识变现成财富、社会地位的命枢。从就业角度分析阶层分化,必然是不同回报的就业机会的分化。而产生云泥之判的就业机会,往往就是那些稀缺、高端的“顶级”工作。因此,里韦拉把注意力放在了精英行业的招聘过程中。
美国的“顶级”工作钟于精英专业服务(下称“EPS”)公司,包括投资银行、管理咨询公司和律师事务所。进入这些公司,意味着高收入和潜力无穷的向上发展前景。可以说,EPS公司是进入当代美国精英阶层的第一站。它们的招聘过程,或许就是解开美国精英阶层再生产之谜的钥匙。
此前,社会学学者对招聘的解释力度显然不够,他们往往只关注应聘人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人口学特征(性别、种族),把其他因素统统归入测量误差和歧视。这样似乎只能得出泛泛的结论(如“知识改变命运”)。在里韦拉看来,招聘主体(即雇主)被学者们忽视了,毕竟他们才是就业机会的守门人,他们守护的稳定的、不成文的决策机制值得研究,也应当被研究,哪怕里面存在违背主流叙事的“歧视”。
简历的初筛即是正确知识持有者的游戏。EPS公司的招聘虽然“公开”进行,但在收简历之前,招聘者就设立了很高的门槛,将绝大部分大学生排除在外:我们想要目标院校的优秀学生,官网上的“纯公开”招聘和非目标院校招聘会成了标榜公平的摆设和“刷存在”的企业营销。虽然招聘者认为这种排他性做法“并非”出于对非名校毕业生的主观歧视,更多是出于效率考量。但无论如何,EPS公司打开一扇“虚假的大门”,一进去就会被“透明的天花板”碰头。名校文凭象征着知识,它也是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制度性文化资本”,持有这种资本的学生简历才能被招聘者看到。一些研究已经探明,名校生更多出自近水楼台的精英家庭,而普通人家的孩子很难得到正确的信息资源和教育资源。
简历主要呈现教育声望、课外活动、学业绩点和工作经验四个方面内容,但招聘者對它们的重视程度显然不同,门槛已然保证了教育声望,教育声望的光环效应又为学生的学业打了包票,招聘人真正在意的只剩下课外活动和工作经验。在课外活动一项,招聘人渴望学生拥有一项需要长期金钱-精力-时间投入的爱好(最好是和招聘者玩一样的高端运动),这意味着应聘者不是书呆子,而是能够愉快相处的人;工作经验方面,他们期待学生曾经在知名企业实习过办公室工作,这会为学生的认知能力、社交能力、进取心和行业兴趣给出证明。
然而,这些要求并不简单。费时、费事、费钱的高端课外活动是一种家庭出身体现,标示着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高端实习工作也很难找,这种职场出生在反映求职者的个人成就的同时,也考验着他的资源链接能力。归根究底,它们都与应聘者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关。而当学生获得“正确”的课外活动和工作经验之后,他又获得了新的知识——一种内化于身心的综合素质,这被布迪厄称之为“具身性文化资本”。
没有的正确“制度性文化资本”,应聘者的简历很难进入初筛;没有正确的“具身性文化资本”,应聘者的简历很难通过初筛。至于何种知识是“正确”的,往往由招聘者决定。总体上,审议者是按自己情况界定、评估应聘者素质的(而非刻意歧视)。符合招聘者期待的参数是一种文化匹配的文化资本符号,它们一旦出现,招聘者就会眼前一亮:“他多像我呀!我就成功了,他一定会成功。”这是他们的潜在逻辑。
如果说简历初筛还有一定的客观标准,两轮面试的评价逻辑就更加主观优先。社会学的招聘研究常常推定面试是人力资源部门完成;而EPS公司的招聘却表明不是这样。没有经过系统性培训的业务部门是真正的面试官,人力资源部门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后者仅仅给前者的面试时间打了个环节框架,规定了破冰闲谈、自我叙事、技术性测试和自由问答的顺序,但具体如何评判仍是业务部门自己的事。
在破冰闲谈环节,招聘者寻找相处舒适的应聘人,他们认为新员工与自己契合,也就是与工作和客户契合,期待应聘人的人际互动和光鲜程度让自己“来电”。自我叙事环节的核心是了解应聘者的成长背景和人生观解释,社会经济地位优渥出身的候选人侃侃而谈,而底层出身者往往羞于启齿(他们可能会忽视:言谈光鲜,使双方放松,保持有克制的自信和兴奋,这些也属于“具身性文化资本”,即一种知识)。
技术问题的时机置于破冰和自我叙事之后,面试官的首因效应已经发生作用,出于已经形成的好感或恶感,技术性测试会相应变成过场或刁难。在这种机制下,很少有之前表现不好的应聘者成功翻盘;而对技术问题本身,招聘者认为只要新员工相处得来,参加工作后是可以培训的。自由问答是在结束语中的最终确认,主动进取的积极叙事更易引发面试官的积极情绪,他们期望应聘者的工作驱动力不在于报酬而在于个人价值和社会贡献,而这正是社会上层出身的符号。
两轮面试中,同样的四个流程环环相扣,不断强化面试官的主观认定。他们把认知能力和技术知识的重要性压低,或把它交由高校声望和另一场面试来界定(这是一种没有实际考察的幻觉),这样留给自己的任务就是轻松的和愉悦的:找到在谈话中具备与自己类似的经历、人生观、价值观,又从行止上谈得来的人。而这些“轻松”条件的背后,是对知识的严苛要求。说话看似简单,但想做到行云流水,却像学习乐器一样需要长期的操演,其中蘊含着大量的群体、阶层的社会符号。以精英阶层、白人、男性为主体的评审人规定了哪些知识是正确的,这为类似背景者创造了优势,而底层出身、少数族裔和女性群体在这个过程中处于劣势,机会不平等加剧。
招聘的最终决策常被解释为面试分数,但事实上是个不足为外人道的“黑箱”。EPS公司的招聘委员会通过“校准-表态”机制对那些模棱两可的候选人做出决策。所谓“校准”,是利用刻板印象弥合面试官的不同意见,取得一致性观点;所谓“表态”,是看评审人中有没有人愿意拉下脸面来为一个候选人强烈发声。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属于优势群体,并至少与一个面试官相契合的面试者,才会成功“复活”。最终的判定不是用客观性纠正主观性,而恰恰是主观评定登峰造极的时刻。
社会学家把就业选拔简化为两种解释框架。“竞争性流动”把工作机会作为完全通过个人努力获得的回报,而“荐举性流动”是通过当前业内精英的挑选确定候选人。人们往往假设一种以竞争性为主、荐举性少量补充的局面。里韦拉的研究揶揄着这样一个事实:竞争性的本质是经过包装的荐举。
精英的包装过程是这样的:上层出身的学生可以获得好的教育资源,帮助他获得知名高校的文凭和学习成绩;家庭给他的社交风格、课外活动资源和高质量实习机会,帮助他获得更好的社交能力、价值观和进取心。
在招聘中,同为精英的面试者按照自己的样子寻找和他社会经济地位相同的候选人,表现出了与他自己类似的(也是让他满意的)品质。简历筛选和面试考核,是一种竞争的形式公平,但招聘的人事工作性质注定逃不开人性,所以招聘者以自己的主观为客观在所难免。
获得青睐的学生具有正确的知识,这其中既包括“制度性文化资本”,也包括“具身性文化资本”,它们都是父辈社会经济地位的产物。具有正确知识的学生获得了EPS工作,这是否属于“知识改变命运”?应当说,是他的出身通过文化资本的投资,给了他易于获得正确知识的命运,而后正确知识又反过来帮助他延续了命运。招聘过程与其说是精英的重建,不如说是精英的再生产。能够“改变”命运的是由精英阶层定义的正确知识,而这种知识,不是同阶层出身的孩子就很难获得。
虽然美国主流社会强调个人奋斗,但书中的案例指出,EPS公司招聘本质还是一个“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游戏,这是作者发出的最重要的警告。当不公平的招聘通过结构化形成了一种制度,以“自由流动”、“个人奋斗”之名行社会分化、阶层固化之实(尽管不是出于主观故意),这种看不见的壁垒更加难以打破。
[(美)劳伦·A·里韦拉著,江涛,李敏译:《出身:不平等的选拔与精英的自我复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