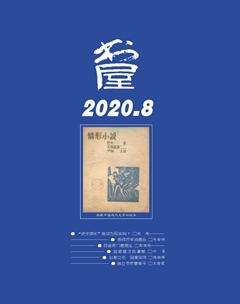醰醰多古情
朱航满
谷林原名劳祖德,大半生从事会计工作,晚年写作自娱,著述不多,但颇为识者所赏。有论者由谷林想到了曾做过会计的英国散文作家查尔斯·兰姆,对此,谷林倒是有一番特别的自嘲:“兰姆当了三十六年的小职员,他牢骚满腹地说,他生平的伟大著作,都已被锁藏进东印度公司的账桌抽屉里。世上以会计工作终其身,直至退休的男男女女,只恐怕不止成千上万,但像查尔斯那般发牢骚动人听闻的有几个呢?”谷林自认为“不敢去盲目与之攀比”,但诸如兰姆这样的会计人员,又能写一手好文章者,世上又有几人呢。谷林与一般的会计不同的是,他爱读书,是个真正的书迷,而他曾供职多年的新华书店总管理处和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也都还算是个与文化打交道的地方。后来,他又调至国家历史博物馆,以十多年的时间,校订一部二百余万字的《郑孝胥日记》,算是成为一个文化界的边缘人物。也正是因为这段经历,使得他因缘际会地与刚刚创刊的《读书》杂志结缘,有幸成为这份杂志的编外校对和作者,也是读书圈的一个小小佳话。
起初,谷林在《读书》杂志所写均为短章,借女儿之名作笔名,乃是有意于隐的。他给当时尚在《读书》杂志任职的编辑扬之水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只是想看看闲书消日,并非求学做学问,偶有会意,记以小文,自鸣其幸遇和欢悦,故读写皆属‘计划外项目,而读更先于写也。”这种无意为之的行为,却使他很快收获了一册小书《情趣·知识·襟怀》,收录于三联书店的“读书文丛”之中,与已颇有影响的王佐良、董鼎山、董乐山、流沙河等作家学人的作品同为一辑。数年后,他的另一册读书随笔集《书边杂写》,列入辽宁教育出版社的“书趣文丛”第一辑,且得以与施蛰存、金克木、唐振常、辛丰年等名流的作品同列。这两册小书,令谷林在爱书人中声名鹊起。《淡墨痕》是谷林生前出版的最后一册文集,收录在岳麓书社的“开卷文丛”第二辑之中。至此,谷林生前共出版文集三册,总计字数不到四十万字,可谓少矣。谷林去世后,由止庵编选其散落的文字,成为《上水船·甲集》和《上水船·乙集》,但就水准来说,远不及谷林生前出版的三册集子。
谷林虽晚来作文,但他起手极高;对于评价文章高下,则常常强调一个“回环咀嚼”,或者是否能够“咀嚼慢咽”,故而在文章的立意、布局、修辞和素材使用上,谷林都是颇为讲究的。在1995年给扬之水的一封信中,他谈及了对于写作读书随笔的理解:“写书话,是不是宜把视线收紧些,引例最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因为不是写导读,或曰学术性的评论,随笔小品拿一本书来做引子,这是借他人酒杯,触发自己的郁结,引例一多,放心难收,不免‘缺少景深。”在1998年给沈胜衣的一封信中亦有相似的论调:“前面说到的书话极好,是因为浓浓的感情皆淡淡着墨,不用长吁短叹,没有宏论傥议,切切实实写出一些细节,此等风格不仅仅能求之知堂翁集中也。”也正因此,收录在谷林生前出版的三册集子中的文章,几乎篇篇为佳,虽多是读书小品,但并不泛泛写来,也不长吁短叹,更无艰涩的学术话语,均是能够“切切实实写出一些细节”,用他的笔头尽可能把议论的“景深”拉得很远,故而很有一些可以“回环咀嚼”之处。
现代以来的作家,谷林自始至终都最服膺知堂笔下的文章,而他研读知堂文章也最为细心,有些甚至到了痴迷地步。《曾在我家》堪称谷林的代表之作,乃是谈他读周著、藏周著,以及因此而结缘的书人往事。这是一篇写读者与自己仰慕的作家交往的文章佳构,写他搜求周作人文集的往事,以及因此而两次登门拜访的经历。文章沉静而优雅,也留下了一份特别的文坛资料。《等闲变却故人心》亦可作为谷林谈知堂文章的代表之作,此文系其读周氏《知堂回想录》而作,但只谈其中的一节《元旦的刺客》,并就周氏回忆1939年元旦在八道湾遇刺一事进行议论。对于周氏的回忆,谷林写道:“叙事不过两百字,全景已描绘得清清楚楚,推想当时运作,无非三五分钟罢了。两客先后开腔,合并字数,寥寥九字,此之谓要言不烦。”这“寥寥九字”,乃是刺客问:“你是周先生么?”作为学生的访客沈启无则回答另三个字:“我是客。”对于这三个字,谷林认为“大堪咀嚼”。由此,谷林继而谈这一对师生后来的关系破裂,并认为此或已为两人交恶埋下了“伏笔”。
与《等闲变却故人心》一样令人“回环咀嚼”的,可推《绘画,写历史》一篇,亦是在字里行间读出了微意。此文谈冰心的散文集《记事珠》,但谷林专门挑出其中的一篇散文《我的故乡》来谈,乃亦是“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此文先从他在博物馆整理严复日记的往事谈起,颇有些白头闲话的寂寞,并不经意地提及日记中的一句“谢子修故,八十七岁”。他在读了冰心的散文《我的故乡》后,恰恰证明了谢子修不但是冰心的祖父,且与严复是朋友的这个佐证,这种读书,真有种他乡遇故知的“幸遇和欢欣”了。到此,谷林又写到了一个闲话,乃是他因此为“谢子修”所做的脚注上,特别加了“作家冰心的祖父”七个字,并希望由此“引逗某一些读者的闲览兴趣”。文章至此,本亦该结尾了,谷林却笔锋又是一转,写到冰心关于童年读书的记忆以及家庭出身的论述。但经过谷林的又一番考证,这两条记叙均值得推敲。待到此时,谷林才写到他作此文的意图:“人们所有的回忆,不由自主,总是要经过情感的筛选。冰心也是在她记忆的画本上绘画吧?”
谷林的这种在字里行间读出微妙之处,很能体现他作为爱书人的性情之处,想来也与他多年从事会计这一职业所养成的敏感细心很有些关联的。他还有一些文章,诸如《〈争座位帖〉与〈苦住贴〉》、《湘西一种凄馨意》、《牙签与暮齿》、《汗漫游》、《版本的选择》等,均是这样值得“回环咀嚼”的篇章。在文章《湘西一种凄馨意》中,谷林特别对照了《湘行散记》和《湘行集》两个不同版本中的内容,发现沈从文晚年对他这些早年的文字,曾做过大量“极为细微”的改动,“但也因之益见出作者的用心致密,着意推敲”,而这种“暮年经营”,在谷林看来,乃是“他始终没有忘情文学工作”。至于沈从文改行转业于文物研究,谷林在文章篇末亦有简短论述:“原也是寻常行径,然而由于外力的压迫,实逼处此,自不能不令人思之于邑。”文章《版本的选择》,对比两本不同版本的梁实秋散文集,其中均收录一篇《谈闻一多》,但其中一个版本在闻一多的出生日期上,直接采用了公元纪年,但生辰却没有换成阳历,故而闹出了笑话。
以上略举数例,不难看出谷林的书话文章,乃是“拿一本书来做引子,这是借他人酒杯,触发自己的郁结”。《一个长期的旅程》和《谔谔一士》两篇文章,均是令人刮目相看的短章。前者谈冯友兰的《三松堂自序》,后者谈梁漱溟的《忆往谈旧录》,谷林均拈出两位读书人在政治年代的一段特殊遭遇,细究其间的微妙心思,其中颇有些动人心弦之处,这或许正是触发了他这样一个亦曾遭遇政治坎坷的小人物的“郁结”之处。可贵的地方还在于,谷林能够在作文时做到“浓浓的感情皆淡淡着墨”,可谓“发潜德之幽光”矣。与此相类的,还有谷林在2002年8月致小友沈勝衣的一封书信中,写他在《读书》杂志上读到《江河万里》一文,由此想起与此文所谈的著名水利学家黄万里交往的一点逸事。1995年,谷林因胃癌在北京医院住院,邻床的病友枕侧放了一册《宋词三百首笺释》,而他也恰恰带了此书。结识后,他才得知此人正系黄炎培的公子黄万里。他继而写道,黄因反对某大型工程,“被戴上反苏反社受苦二十年之帽”,“一意孤军作战如马寅老”。
还有两篇文章,亦是令人会心的。《共命与长生》一文,乃是从六个读书人关于书的故事,来写他对于书的态度:“‘诚知此恨人人有,把深爱的分散给也能爱的人们,使所爱的及时得所,岂非便是长生?”谷林生性淡泊,藏书不多,但颇有些令人爱慕的旧物,这些他生前多分散给他欣赏的后辈,使他的爱物终得以“长生”。另外一篇,则是《煮豆撒微盐》,谈及他极为喜爱的周作人文章《结缘豆》。周氏论及京师僧人在佛诞之日,“煮豆微撒以盐”,“邀人于路请食之以为结缘”,并说他不必去“念佛拈豆”,“姑且以小文章代之耳”。谷林在文章中还引用周氏:“煮豆微撒以盐而给人吃之,岂必要索厚偿,来生以百豆报我,但只愿有此微末情分,相见时好生看待,不至伥伥来去耳。古人往矣,身后名亦复何足道,唯留存二三佳作,使今人读之欣然有同感,斯已足矣,今人之所留赠后人者亦止此,此均是豆也。”无论怎样评价周氏做此文的用意,但这又何尝不应是所有做文章者的夫子自道。谷林于此处感慨:“宿业前缘,真令人无可排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