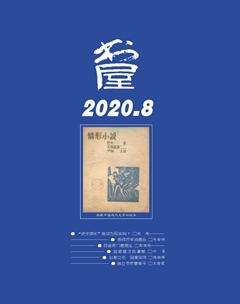独立苍茫意难平
王澄霞
沈亦云女士六十万字的皇皇巨著《亦云回忆》,为之作序者皆声名赫赫,如蒋介石、胡适、张群和张公权等,无一不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局中人和见证者,有的甚至主演和导演,这也足见这部《亦云回忆》的分量和影响。
亦云何许人?作者简介一栏这样介绍:沈亦云(1894—1971),黄郛之妻,祖籍浙江湖州,生于嘉兴。原名性真,后改署景英,字亦云。1906年,考入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后到苏州景海女学读英文。辛亥革命时,在上海组织女子军事团。抗战期间,在沪创办南屏女子中学。1950年后定居美国,1971年逝世于美国纽约。
值得一提的是,“亦云”一名,系中国最早的女子师范学校、北洋女师首任监督兼主持傅增湘先生所取,“他用景慕沈云英之意,给我取‘亦云二字。抗战时起,我以字行不再用名了”。这里的沈云英(1624—1660)系随父征战的明朝女将,浙江萧山人,其文武全才的巾帼英雄,同乡晚辈秋瑾女杰曾以“执掌乾坤女土司,将军才调绝尘姿”相歌颂。由沈性真而沈亦云,这也可见作者本人的志向和抱负。
沈亦云堪称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共同孕育下的卓绝女性,二十世纪罕有其匹。她的身上既有女性的溫良贤淑,又有男性的侠肝义胆;既是深受欧风美雨洗礼的时代女性,又以“天理良心”、“心安理得”为修身尺度;既能搦管救国,功成弗居,偕隐山林而自足,又能任劳怨历艰险,与丈夫荣辱与共,生死相随;既淡泊名利,仗义疏财,义无反顾地捐献其“唯一的住宅,并其中所有值钱之物”,以示抗战决心;又珍视名节,倾尽毕生所能,誓将亡夫生前“心迹之苦、行事之难,而不为世人所共谅”赍志而殁的屈辱悲辛,向后人向时代和盘托出。她有决断有识见更兼史才,历十年践行诺言完成《黄膺白先生家传》,逾廿年又写就上、下两卷的《亦云回忆》。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为之惊叹“少年喜得忘年友,续史才惊读史人”。亦云女士几乎汇集男、女两性全部的优秀品质于一身,历史上任何一个淑女、才女、烈女,抑或任何一个君子、才子、侠士,几乎难可比拼。在国家积贫积弱的甲午战争年间出生的亦云女士,即使用当代女性的标准来评价,依然是那么光彩照人,难以望其项背。中国妇联所倡导的女性“自尊自爱自立自强”,早在沈亦云身上就已得到充分体现,而今日之当代女性,不少人对于这样的目标却还有很大的差距。
一
沈姓为嘉兴故家。亦云之父沈秉钧1902年中举,以教读为业,后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曾独立校印《资治通鉴》,乃《辞源》初版的编辑之一。父亲教育子女首重“勿说谎”,故为她取名“性真”,释其意为“真之反面为妄,妄则无所不为,是个坏人”,常提醒她待人处世要责己重、责人轻,否则为人太刻薄,于恕道有亏。母亲葛氏亦系当地望族出身,平时极力助人,“尽量为人”,屡次受挫而能热情如故,“对儿女小气与小看人,她责之最严”。父母鼓励子女读新书做新人,对女儿之事为辛亥奔走募捐毫不阻拦,只是建议审慎行事,郑重嘱告勿经手款项。亦云自陈对其一生影响最大的良师益友,首推自己的父母。
亦云曾“诵‘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之歌词而奋发”,为辛亥伟业竭尽绵薄。当时上海出现了各种女子军事团体,如林宗雪组建的女子国民军,陈婉衍统领的女子北伐光复军,唐群英筹建的女子北伐队和沈佩贞组织的女子尚武会等。亦云发起组织的“女子军事团”乃其中之一:“我们组织了一个‘女子军事团,借西门方板桥一家停课的女校校舍为集合处,分四项工作:战斗,看护,募饷,缝纫,各以能力志愿参加。……团成立后,呈报护军都督府,请指导。后来南、北军事至南京而止,军事团工作仅以做制服和募捐略有成就。……在南京时,克强先生部下有人教装炸弹,亦曾练习使用,住在铁汤池丁宅,只极短时间。”
她后来之所以主动解散“女子军事团”,成员各自回归教、学本位,既有时局已趋明朗这一外因,更觉自身尚待提高充实,方能尽公民建设之责;另外,她深受传统文化之影响,认定政治圈乃名利场,属结党营私、藏污纳垢之地,绝非读书人尤其是知识女性栖身之所:“我们一班人热血有余,贡献极少,自这次经验,同人都不再参加群众运动。有一点相同处,觉冲动时期已经过去,国家需要建设,个人需要学问。有人提倡女子参政,我们几个人因受旧书影响,看得从政不是清高的事,又以如果参政,须先具备足以参政的条件,故均无意于此。民国元年(1912)暑假以前,我们已各归本位,教者归教,读者归读。”
无独有偶。同为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出身的许广平,在1925年4月6日给鲁迅先生的信中谈及唐群英、沈佩贞等女界先驱时,口气颇为不屑:“那些不纯粹不彻底的团体,我们绝不能有所希望于他们。即看女性所组织的什么‘参政、‘国民促进、‘女权运动等等的人才的行径,我也实在不敢加入以为她们的团体之一。团体上根本的事业没有一点建设,而结果多半成了‘英雄与美人的养成所;说起来真叫人倒咽一口冷气。其差强人意的,只有一位秋瑾,其余的什么唐□□,沈□□,石□□,万□……哟,都是应当用蚊烟熏出去的。”许氏持论失之偏颇,倒也充分表明了中国文化传统熏育下的知识女性,大多对政治有着本能的抵触和拒斥。
二
《黄膺白先生家传》中说“先生初娶于吴,继娶亦云”。她与黄郛(1880—1936,字膺白)相识于沪军都督府,因对家事国事天下事的看法颇为同调,遂相互激赏,并于1912年10月结为连理。此后亦云夫妇始终“志同道合,其坚如金”。这种坚牢的感情基础,与亦云的人品学问和过人能力密切相关。
沈亦云极有才干,家庭贤内助自不必说,“那时全家衬衣都我自做,有时亦做鞋袜。……我开始做手工,以做手工为定心养性之初步,渐成习惯。……在得不偿失和不虞之誉中,我得到的益处是耐得住闲,不怕寂寞”。她与丈夫志同道合、互相砥砺,堪称黄郛事业上的得力助手。在黄郛建议下,亦云曾以黄率真的笔名翻译了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的《南洋与日本》一书,1914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印行。黄郛因二次革命失败被袁政府通缉,亦云新婚不久就随夫流亡日本两年半,为生计只得将所有饰物包括结婚纪念品在内都一并变卖,其间危苦艰辛自不待言,她却自嘲这是一种心理解放。为安全计,亦云还得屡屡代夫独自“跑街”打前站,“跑马路、跑码头、跑银行、跑电报局等”。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1916年前后,单身女性抛头露面接洽一些为当局彻禁的人和事,需要胆量,更需要智慧。为分丈夫案牍之劳,又事涉机密,因此看速记、拟函稿等都由她负责:“他参与很重要之点,则我屡为其最机密的下手,有时为唯一的下手。我以读历史的兴趣,对国家的同心,而共同参与,事后我即退出。”
例如,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黄郛参与其间,但“成密电本归我保管,来往电均我亲译,膺白复电大概都由我起稿,彼此例行报告之外,偶然有一二机锋暗示,措辞十分小心”。这一细节对方始终不知,因为“我极力避免参与他们的事,即以前膺白与之通电是我起草之事,亦未说出”。在黄郛的日常政务中,亦云于他更是良师益友,谓予不信,请看下文:“我劝膺白写中国的《人民读本》……为写《人民读本》,引起了许多心事,他说何从下笔。我建议一面写‘常,一面写‘变,即照理中国应该如何,而此时则实际如何,把一篇烂污账请国民过目判断。”“膺白写第二本书《战后之世界》要吃力得多。……他写一章,我誊一章,我们在同一书房,我的书桌只是一张半桌。他要我誊,为让我做他第一个顾问,我见到须添须改之处,立刻告诉他,得他同意,立刻修改。我愿充誊录,以先睹为快,并且二人在同做一件事情,其他俗事不会因影响到我而亦分他的心。抄稿以外,我亦替他看参考材料,世界有许多未决的问题,疆界亦时常更改。……报上预告汪精卫作《巴黎和会与中国》,我函托在上海的吾弟君怡,该书出版,用最快的方法寄我一本。收到时膺白正在北京,我一口气看完,次日上午膺白已接我快信,报告他汪书已看过,不足以夺彩,无事参考。”
更为难得的是,亦云恪守公私內外之别,夫妻知己而又诤友,和而不同,“我在膺白面前,对国事和其他看法,要保持独立的见解,虽然我们的看法大都是相同的”。至于后来亦云夫妇隐居莫干山,筹办小学和战时临时中学,致力于义务教育和庾村经济合作社建设,尤其是丈夫病逝又狼烟四起的抗战时期,还在沪创办南屏女中十年,勉力撑持奋斗不辍,以贯彻亡夫遗志,“以真正学问道德报国”,亦云之笃行坚忍、“中通外直”、“亭亭净植”之独立个性可见一斑。
三
逢人必劝写自传的胡适先生在其序言中说:“亦云夫人这部《回忆》的第一贡献在于显示保存史料的重要,第二贡献在于建立一种有勇气发表真实的现代史料的精神。”适之先生此说大体不错,但尚未切中肯綮。作者沈亦云弟弟沈君怡的“沈跋”才可谓一语道破:“姊写此书的真正用意,我以为尚另有所在;而最能道出姊这点心事的,莫过于蒋公在卅四年(1945年)11月28日为《黄膺白先生家传》所作序文中间的几句话:‘亦云夫人撰此《家传》,其于逝者心事,实能推见至隐。这几句话同样可以适用于《回忆》,‘于逝者心事能推见至隐一语,实道出作者与逝者无限辛酸惊险的经历。今姊于悠长的岁月中,以坚忍的精神卒成此书,可告慰姊丈在天之灵者,无过于此。某日我曾对姊说:‘姊丈对得起国家,阿姊对得起姊丈,意思即在此。”
至此,必须介绍《亦云回忆》的真正主人公、亦云丈夫黄膺白。在民国云谲波诡的政坛上,黄郛可谓举足轻重。他在短短五十七年的生涯里,参与了民国肇兴、军阀纷争到“七七事变”前中日交涉的诸多重大事件,是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史、中日关系史无法绕开的关键人物。黄郛华北任上经手的几起谈判和签约,都是在中方极端不利的前提下进行,也令他至死陷入“亲日”、“媚日”的舆论漩涡:“膺白在世时,直接当济南惨案及塘沽停战之冲:为这两个问题,前后受大谤,为国家故,他愿过则独受。在当时折冲之苦,与事后隐忍不言,真是‘打落门牙带血吞、‘万箭穿心、‘腹背受敌各种成语的滋味都尝到。为国家,我不敢怨,然‘国家今如此,我岂能忘!”
1933年8月,黄郛在接受天津《大公报》记者王芸生采访时说:“这一年来的经过,一般人以为我黄某天生贱骨头,甘心做卖国贼,尽做矮人,我并非不知道伸腰!只是伸伸腰之后有什么善后办法?为国家设想,不能那样冒险……但国家既需要我唱这出戏,只得牺牲个人以为之。”1934年,黄郛的高级顾问何亚农就曾对黄郛此后的内外困境有所阐释:“盖有三误焉。从前日本以为黄有办法,所以捧之,近以其诸凡听南京,因之颇不满,此一误也。黄之来也,以为蒋必事事听之,孰料不然,此又一误也。蒋之约黄出来,本利用其做二重外交,……孰料黄亦系求国民叫好者,岂非亦一误耶。”
一如沈母曾经慨叹“取得经来是唐僧,惹出事来归孙行者”。亦云在回忆录中以巨量篇幅和大量史实,包括当年执政各方的书信、电报以及众多当事人口述回忆,从多个角度凸显亡夫“宅心仁厚,为国家民族鞠躬尽瘁……生平言行一贯,不依流俗浮沉”特立独行的性格特点,尤其一一呈现黄郛当年的艰难处境,“国家大难当头,犹意气用事,视当冲之人存心卖国,又责以万能。中国政治场中,为公谊而指臂之助者,甚为罕有”。亦云自称撰写回忆录之动机,一则“承他(黄郛)拿我放在他自己与朋友之间,使我义不容辞而写这些”。二则源自老师傅增湘先生的策励:“膺公为历史上之人物,记载要以翔实为主。凡官撰之书多有失实,不若私家著述之尚存真相,自古已然。共和以后,史职不修,若不自行整理,恐他时必至混淆是非,任情毁誉,非细故也。……斯意谓此事宜夫人自任之。”因此以《亦云回忆录》告慰黄郛在天之灵,同时“向现代史家交卷,拥护研究现代史的风气”。
如今,随着当代史学界“黄郛替蒋介石跳火坑”、“无以为继:黄郛与1935年华北危局”等研究成果的相继出现,人们对黄郛功过成败的评价日益客观公允,亦云夫人的弘毅笃行和她这部巨著,自然功不可没。
亦云夫妇同心一德、情比金坚,但全书毫无夫妻间风花雪月、情意缠绵的描写,甚至连恋爱细节都付之阙如。从一般意义上讲,男女的相处一开始有激情有爱意,维系与吸引彼此的就是这些。而像亦云夫妇,彼此又兼知己、同道和战友,在甘苦与共的岁月中激情潜沉,凝成声气相求血脉相连生死与共的亲情,可谓升华了的爱情,爱意早已弥漫于拟稿译电、谈心商讨、读写誊校、吃饭散步、端汤奉药等日常事务中了。正因情同一人,《亦云回忆》大旨为亡夫鸣不平以浇心中之块垒,故春秋笔法随处可见;而写到黄郛积劳成疾忧愤而逝的章节,字字句句泣血锥心。全书毫无女性为文的婉约柔美,风格沉郁苍凉。撰写长篇回忆录,不能仅靠毅力,还得具备相当专业修养:“我属稿时,排比而解说,常恐记忆有误。每择一题,先回想其时环境和有关人物,结成局面,然后置身其间,以所知多少略定轮廓,故虽信口述来,不敢以意为之。历史是中国最早而极郑重的一门学问,述而不作,古贤以之代舆论。我未曾学,而慕此理,执笔战兢,仍不免阿私溢美之处,读者斟酌,并请宽恕之。”亦云夫人当年是北洋女师简易科出身,她安排材料结构全篇包括回到具体历史场景中去构思回想,其艺术功力实令后辈来者追仰之至。
黄郛当年为求婚而长函恳告沈父:“后半世学问事业,视长者一诺。”回顾他们的非凡一生,与其说表明了膺白先生眼力之精准,毋宁说更证明了亦云夫人的才干能力卓绝超拔。
《亦云回忆》只有一处提及对两性平等的看法,有人“请我到妇女会演讲,我不知应该说什么,而且我有偏见,男女同隶于四民,没有男子会何以要有妇女会,故亦逊谢了”。在潮流面前不偏不倚,在权力者面前不卑不亢,在弱势者面前不矜不伐,在强权面前不屈不挠,二十世纪初的女性解放先行者,沈亦云先生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沈亦云:《亦云回忆》上、下册,岳麓书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