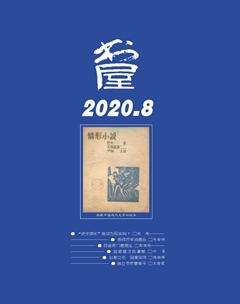美津子的彷徨
陈司琪 刘剑梅
远藤周作的《深河》成书于他人生的最后几年,他与疾病痛苦纠缠,生命到达油尽灯枯之时,仍然执笔与死神搏斗,留下这一部“总决算之作”。尽管他自己对《深河》并不满意,认为其“不像《沉默》让人沉醉,也不如《武士》那么浑厚”,但是这部作品在思想内容上包含了他这一生对宗教信仰的思考,读者依旧能从中挖掘出许多精神宝藏。
从乡下来到东京上大学的美津子,因着这种源自出身的自卑感,通过挥霍金钱来融入当时的同学圈子。但美津子并不认为这样的圈子就是自己所向往和憧憬的,她被同伴们簇拥着,“内心深处却又瞧不起他们”,甚至在他们说她能喝酒能开车时,“心底升起一股分不清是愤怒还是寂寞的强烈情绪”。美津子在这其中感受到的空虚,来自对自己生活现状的不满,也来自对自己所追求的未来的未知。很难猜测如果美津子没有遇到大津,她的生活会往什么方向去发展,但无论如何,她在当时正好遇上了与她的圈子格格不入,甚至还显得滑稽可笑的大津。
起初,美津子对捉弄大津并不感兴趣,认为这只是学弟们无聊的校园生活中的无聊消遣。但当她从大津口中得知他的信仰,又从同伴那边得知他每日虔诚地祈祷,对这个表面上老实巴交的男生产生了兴趣——并不是什么善意的兴趣,而是“觉得这种男子常会有伪善的地方”。她想撕开大津的面具,想证明这个看起来与众不同的男生,在骨子里不是同朋友们一样世俗,就是和自己一样空洞;从一个无神论者的角度来说,她也想证明大津的信仰只是一种家庭的习惯,随时都可以被轻易放弃。可是大津却对美津子说,“即使我想放弃神……神也不会放弃我”。这样的话,对美津子内心的震撼太大了。或许她从未相信过大津的祈祷可以得到他的神的回音,认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只不过是浮于表面的形式,而此刻她却发觉大津的坚持并非一厢情愿,两相对比下更加重了她内心的空白虚无。她的引诱行动变本加厉了,这样的羁绊让她更有破坏的冲动,她对大津的信仰下战书:“神啊,我要从你那儿把他抢过来!”在大津遵守约定不再去库尔特尔屋时,她对着耶稣的塑像耀武扬威:“他不会来了,你被他抛弃了。”她似乎变成了莫伊拉的化身,享受着这种“从一个男子那里夺去他相信的东西的喜悦,让一个男子的人生歪斜地快乐”。但很快,美津子大获全胜之后就厌倦了这种乐趣,也抛弃了大津。
我们无法得知美津子在抛弃大津之后,以及在与矢野相亲结婚之前,是怎么过日子的,只有一点片段告诉我们,她在毕业之前曾有过一段努力读书的时间,并且意识到“学生时代在体内涌动的那种想弄脏自己的冲动是多么愚蠢”。她放弃了之前游戏人生的行为,也放弃了自我破坏的行为,转而尝试成为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平淡地过完一生,因此选择了矢野作为结婚对象。
当她得知大津跑去念神学院要当神甫后,她内心也不过认为,“神不过是贪婪地把我抛弃了的男人重新捡起来罢了”,“瘦削男子捡起她扔掉的东西,如小孩子抱起掉落在沟中满身泥泞、不停吠叫的小狗”,一种作为胜利者的心态依旧根植在她心中,也正因如此,当她在新婚旅行中厌倦了自己的丈夫,无数次将自己与苔蕾丝对应起来时,她更加质疑自己的选择,这似乎不是一个胜利者应该落入的境地。她没有办法掩盖好自己爱已枯竭的秘密,同许多改邪归正的人一样,做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于是她从这令人窒息的新婚旅行中逃离出来,作为自己最后的任性,前往了苔蕾丝的兰德,也前往了大津所在的里昂。很难说美津子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去见大津的——作为胜利者去同情这位失败者,还是需要这位失败者的凄惨模样来抚平自己内心的不平稳,又或者只是单纯好奇为什么他又去了神学院。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她从大津口中得到的答案都不是她所想要的,甚至这答案还粉碎了她一直以来自以为的胜利者地位。
之后,美津子离了婚,脱离了苔蕾丝的角色,开了一家服饰店,周末的时候还会去参加医院的义工工作。这并不是由于她富有同情心之类的原因,而是“爱已枯竭的她日渐形成尝试爱欲行为的自虐性情绪”,这是对爱的一种模仿、一种演技。她的内心依旧如沙地般干涸,潜藏着的黑暗因子时不时冒头:“当美津子注视着无任何抵抗能力的老太婆睡着的姿态时,会突然产生某种冲动,故意不替她换尿片,不给患者该吃的药。那时,她的心里有另一种声音在说:反正她吃药也好不了,不只对别人无益,对家人还造成很重的负担。这个老女人不如早点解脱”。她不再做毁灭自己的尝试,但也无法从内心深处生起对别人的关怀与爱。她还对即将去世却极度眷恋自己丈夫的矶边太太否定了转世的可能性:“要认定,死了就什么都消失了,这样会比背负着过去种种到来世生活要来得快乐。”美津子见不得矶边太太这样的深刻的爱,这样的爱与大津的信仰都会刺痛她空虚的内心。
美津子在这一阶段努力让自己融入平凡的生活之中,却徒劳无功。她依旧不知道自己在追寻的是什么,但总归踏上了追寻之路。
在行前说明会中,美津子就看到了印度查姆达女神的图像,之后旅途中又在导游江波的带领下在洞窟中看到查姆达女神的雕像;这是一尊矛盾的女神像,疾病与疼痛压榨着这女神的生命,她却依旧从萎缩的乳房中硬挤出乳汁喂养小孩。这尊扭曲的女神像可怕却又充满着大爱。这显然与美津子之前所认知的以及大津所信仰着的完美的神的模样有着巨大的不同,但也正因为这女神混合了善与恶、残酷与慈爱,呈现一种混沌的姿态,才给美津子的追寻之路提供了新的可能。一如美津子自己所说,她来到印度,感兴趣的是这个世界“清净与污秽、神圣与猥亵、慈悲与残酷混合共存”。美津子洗刷不掉自己身上的黑暗与罪恶,但如果能如女神查姆达一样,背负着一身罪恶也能坚持自己所求,也不失为一种好的生存方式。
在印度与大津的碰面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让美津子失落,她失望的是大津的生活处境,被教会驱逐,在这脏兮兮的地方干着脏兮兮的活计。尽管内心对女神查姆达有很大的震动,但当她真正见识到大津的模样,她完全无法接受,一度埋怨大津,为何要这样愚昧地相信着他的神导致这样的境地。大津内心反而十分安定,他在印度找到了自己的容身之所,物质条件不好但精神上有人能容納自己,拥有相同的信仰,跟美津子说话的时候头一次开起了玩笑。两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似乎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美津子不懂得宗教信仰,不懂得大津的神,她一直以来只是有种隐隐约约的直觉,“她模糊感觉到自己也希望拥有X,一个可以让自己觉得充实的X,可是她无法理解X究竟是什么”,在大津身上或许能找到自己所寻找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大津的信仰就是她的信仰。
还有一个细节,是美津子与沼田在码头附近看到贫穷残疾的人们乞讨,沼田生发出了“大家同样是人,这些人也同样是人”的同情,但美津子却读懂了沼田的同情中所带有的“我们观光客可以做些什么呢”的意味,这些廉价的同情让她不安。美津子之前一直说自己是个“爱已枯竭”的人,故而她必然是渴望唤醒自己心中的爱的,可她又对这种浮于表面的廉价的同情嗤之以鼻,“她不需要‘装出来的爱,只希望真正的爱”。这里就暗示了美津子追求的不只是那种寻常的爱,这种爱令人无力又显得泛滥而廉价,她渴求的是能令她心里安定的那个神秘的X。
美津子换上纱丽,迈入了恒河沐浴。她不知道对谁祈祷。或许是对大津追随的洋葱,不,不一定只限定洋葱,或许是对某种巨大永恒的东西。
比起之前美津子在做义工工作时对爱的模仿,她这一次模仿的祈祷对她而言,意义更为重大。之前满怀恶意,却也不觉得自己这么做有任何错处;这一次却连这样的模仿都能让她感到不好意思,她明白自己仍未达到足够虔心祈祷的状态,却也愿意尝试真心去做,于她而言,是一次大的改变。这一条恒河包容了各色各样的人,同时也包容了美津子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在恒河之中,美津子察觉到自己的一切都有了安放之所,也稍微摸索到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作为小说来说,美津子的自我救赎与觉醒之路似乎在这条恒河中就迎来了一个终点,后面的故事本应该对美津子的觉悟不再产生大的影响。可事实并非如此。以往的美津子尽管内心有无数想法,面上都是矜持自控的。在大津为平息逝者家属对三条拍照的愤怒而被打受重伤时,她在小说中终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发泄自己的情绪:“你真是愚蠢啊!真的太蠢了。”美津子目送被抬走的担架叫喊着:“真的太蠢了!你为了‘洋葱虚度一生,虽说你模仿‘洋葱,然而只有憎恨和自私的世界,不是什么都没改变吗?你到处被驱逐,最后连脖子也断了,被人用抬死人的担架抬走。你终究是无力的,不是吗?”她蹲下来,用拳头敲打石阶。
美津子为大津感到不值。虽然上一刻她的明悟才表明她将来或许会走上和大津类似的道路,但此时此刻的她毕竟还没有真正踏上这条路。她刚刚结束了自己内心中挣扎,决定好了未来的方向,都还没有来得及巩固这个想法,就迎来现实的当头棒喝:“只有憎恨和自私的世界,不是什么都没改变吗?”个人的力量在这庞大的世界里算得了什么呢?由此可见,美津子尽管解决了内心的矛盾,但个人与世界之间的矛盾,仍待她长时间地去经历、去思考才能解决。
在小说的结尾,美津子遇到了与大津做着相同事情的修女们,又有了新的体会:“洋葱老早就死了,但是,他转生到他人内部。将近两千年之后,转世到眼前的修女之间,转生到大津体内。像他被担架抬到医院那样,这些修女也会消失在人间之河。”
我们不好下结论说美津子只通过修女简单的几句话,就能完全理解这种信仰力量的源源不断与生生不息,这股力量是否足够强大,是否能与整個世界的憎恨与自私对抗;但无疑,她对个人与世界之间的矛盾有了一丝丝的开解。结尾并没有明确说明大津是生是死,但无论他活着还是死去,他的信仰大概会用另一种方式存在于美津子的身上……